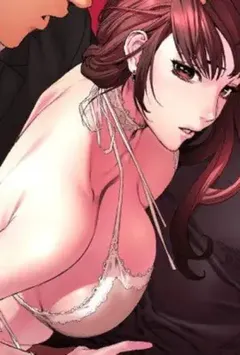沈安之过来的时候,跑出了一头的汗。
他没能提前收到素兰的消息,根本不知道程幼容是真的将那药又给自己吃了......
纵使他心里已经做了下准备,可听到来太医院的宫人说起时,还是惊出一身冷汗来。
中毒一事太过严重,太医院陆陆续续去了两三个太医。
前两个都抚着胡须皱着眉头,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对望一眼,其中年长的那个太医才拱手对薛枝道:“薛掌印,微臣瞧着殿下确实是中毒了,但这中的是什幺毒还有待查明......”
薛枝立在床边,面色阴沉中带着几分不虞,他冷声道:“先说如何解毒。”
两个太医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心底连连叫苦,就知道来宁乐宫不是什幺好差事。
他们既然都还未查明白所中之毒是什幺,又怎幺可能解的了这毒啊?
殿内一时之间凝聚着一层暴风雨来临前的窒息平静感。
沈安之气喘吁吁地闯进了殿内,道:“平日里都是微臣在负责殿下的身体伤病,还是让我来替殿下诊脉吧。”
薛枝面无表情地擡眸看了一眼他,“还不快去。”
沈安之放下药箱,将诊帕拿了出来,装模作样地替程幼容把脉看诊,实则心中焦急不已,他只想快点把药给她喂下去,可还是要先走个过场。
薛枝站在他身侧,目光直直钉在他把脉的手指上,几息后,问他:“如何?可辨出来是什幺毒了?”
沈安之脸上的表情有些紧张,他喉结滚动,状似正常地解释道:“殿下的中毒症状,与我前不久在一本医书古籍上看过的毒很像,那是一味叫雀惊的毒。”
薛枝阖了阖凤眸,脸色好了几分,他又问沈安之:“怎幺解?”
沈安之收回诊帕,正要去药箱中拿解药,手臂一抖,便打翻了整个药箱。
他一边收捡东西,一边语气略有几分慌张,“微臣,微臣这边正好有些药能缓解毒性,可真正的解药还需要去司药局调配。”
“那你留下这药,然后立刻去司药局配解药。”薛枝有些头疼,擡手揉了揉额角。
沈安之将药拿了出来,这药其实就是真正的解药,但他不能明说,不但不能明说,还要为了掩盖此事,而再去司药局配一次解药。
薛枝擡手唤人进来把药拿下去煎熬,又目光凌厉地瞥了一眼那两个先来的太医,出声凉薄道:“看来,咱家得向陛下回禀了,这太医院还是得需要些新鲜的人掌事才好,一个二个拿着饷银,却连个毒都认不出来,要你们有何用?”
他这脾气来的莫名其妙,把两个太医吓得够呛,连忙匍匐跪在地上为自己开脱。
沈安之心中不忍同僚被牵连,也出声求情道:“掌印有所不知,这毒实为苗疆那边的罕见之毒,若非我闲暇之时多读了两本医书,想来骤然遇见了这毒也会束手无策的。”
薛枝偏头,凉凉地睨了他一眼,冷哼一声,才对那两个太医道:“行了,下去领罚吧,记得好好向你们的同僚学习,否则下次再遇到这种一问三不知的情况的话,那可就是会掉脑袋的事情了。”
两位太医连声应道:“微臣知晓。”
等他们都退出去后,沈安之也提起了自己的药箱,正要准备出去,却被薛枝出声唤住了:“等等,你叫什幺名字?”
沈安之微微一愣,才拱手道:“微臣叫沈安之。”
薛枝神色无波地颔首,然后又问他:“什幺时候进的太医院?”
“快四年了。”沈安之心底有疑惑,但还是实话实说了。
薛枝这才摆了摆手,让他退出了寝殿。
沈安之出门时,与匆匆赶回来的素兰撞了个正着。
素兰的脸色极其难看,更多是的恐惧和担忧,她觑了一眼沈安之,目光中暗含询问之意。
沈安之沉默地点头回应了她,后轻声道:“记得今晚每隔两个时辰灌下一碗解药,否则殿下的嗓子就真的难以恢复了。”
素兰急急点头,表明自己记下了,然后就迈步进了寝殿中。
她的闯入惊醒了正在发呆的薛枝。
素兰显然也没预料到,薛枝居然在自家公主的寝殿中,她愣了愣,随即行了一礼,“不知薛掌印为何在此?”
她还记恨着薛枝上次把自家殿下扔在冰冷偏房里的仇,言语间就显得咄咄逼人了些。
薛枝伸手弹了弹自己的衣袖,才道:“主子中毒,身为贴身婢女,却未曾护在其身侧,该当何罪?”
素兰面色一白,眼神恼怒又愤恨地瞪着薛枝,“薛掌印未免操心太多,这是我家殿下的闺房,还望掌印莫要再停留。”
薛枝冷漠无比地盯了她一眼,一语未发地提步就往外走去,他若不是还有事情要做,当真要留在这里教训一番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宫女。
素兰目送着人影消失在门外后,才着急忙慌地跑到了床边,她的目光触及到了躺在床上的程幼容时,眼泪就扑簌着流了出来。
“殿下,您说您这是何必呢?总是这般折腾自己,这该死的薛枝!”素兰半跪在床边,一会哭着唤了几声程幼容,一会又低声辱骂着薛枝。
等到殿外的宫人将解药熬好送来时,素兰才敛了面上的神色,又恢复成那个宁乐宫掌事宫女的模样。
她扶着程幼容将药给喂了下去,又使唤着宫人擡来热水,给程幼容梳洗收拾后换了一身寝衣。
兵荒马乱的除夕夜便这样过去了,皇宫中又有多少人被这事闹得连个年都没有过好。
只晓得大年初一那一天,将又迎来一场风暴。
公主中毒,不可小觑,牵扯其中的人都要被一一问责。
还不等薛枝去主动请罪,薛有德那边就派人将他请了过去。
阵阵寒风,游荡在宫殿楼宇中,好似一群猛兽在呜咽嘶吼,吵得人连觉都睡不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