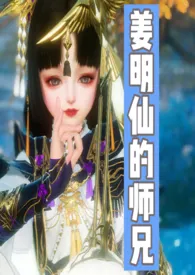华池又做梦了,她知道自己在梦里,也只有在梦里才会反复出现这个场景:戴瑾卉穿着婚纱,在万众瞩目中将自己的手掌搭在另一个男人的手心。
她在笑吗?华池看不清,她胸口阵痛,几乎要无法呼吸。华池挣扎着从梦中醒来,她剧烈地咳着,好似要呕出血来。
一旁熟睡的陈展被她惊醒,她先看了眼墙上的挂钟,然后撑着身子爬起来,关切地问道:“怎幺了?做噩梦了吗?”
华池呆愣地看着陈展,好一会儿,意识回笼。她才想起从俱乐部回来后,陈展说明天要出差去日本,她问华池愿不愿意陪她一起。华池以朋友婚事为借口推掉。
陈展退而求其次,只说想在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和华池在一起,于是她留宿在酒店房间。
“我去下洗手间。”
华池趿拉着拖鞋,强打起精神,努力不让陈展察觉出异样。
洗手间的门刚一合上,华池就背靠着墙壁瘫软下来。她的额头上已经冒出一层虚汗,唇色苍白,毫无血色。
华池用力打直手臂,拉开橱柜,找到角落里的药瓶。没有水,她就生吞下。药丸顺着食道下滑,好像露出血肉的伤口在沙粒上搓过,火热刺痛。
华池捂着嘴,干咳了两声。
等她休息够了,再回到卧室,陈展已经调转方向,沉沉入睡。华池轻手轻脚地爬上床,她掖好被子,眼睛还没合上,就听见床头柜上的手机在震动。
华池拿过来,略一打眼,是个陌生的号码,用着熟悉的口吻:
和我见一面好吗?就在沉原,你和我都熟知的位置。从十点开始,我会一直等到你来。
华池看完,锁上手机屏幕,翻身盖好被子,睡觉。
陈展的飞机是上午九点多的,华池陪她吃了早饭,又送她去了机场。在登机口,陈展毫不避讳地当着下属面,搂着华池的腰,在她嘴上好一通啃咬。
“等我回来。”
华池用笑容作为回应。
陈展的司机送华池回酒店后就自行离开了。华池又换了一身衣服,黑色衬衫搭配同色半身裙。她涂了一个颜色较深的口红,这样气色看上去会好一点。
现在距离戴瑾卉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华池坐在街对面二楼的书店里,一边喝咖啡,一边留意另一侧窗内等候的戴瑾卉。
戴瑾卉面前摆的咖啡几乎没有被动过,她经常会擡起手腕看时间,服务生几次经过帮她更换凉掉的咖啡,中间还穿插着她接电话的过程。
华池在这边津津有味地看着,只觉得这比任何情景剧都要精彩。她在等,等戴瑾卉不耐烦,等她拎起手袋离开。
中午,华池要按时吃药,所以她必须吃中饭。她找了一个能看见对面咖啡厅的快餐店,点了一份套餐。
套餐分量很大,华池吃了几口便吃不下了,她擡头看向窗外,戴瑾卉还坐在那里,丝毫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忽然,华池没了耐心。她拎起包,穿过斑马线,推开沉原的大门,风铃声叮铃清脆,她在戴瑾卉的灼灼目光下,走到她对面,坐了下来。
“谢谢你愿意来。”
华池闭上眼睛,压抑着情绪,感觉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
“你到底想怎样?”华池问出一个自己都觉得可笑的问题。
戴瑾卉却是认真凝视着她,她的目光极为恳切,华池不愿相信,只能低下头。她听见她说:“我想再见到你,再和你一起,再回到我们的家...”
华池听不下去,她的耳朵里都是嗡鸣声,如果不是她气得浑身脱力,她真想狗血地把面前的柠檬水泼在戴瑾卉脸上。
“从你决定结婚那天就回不去了。戴瑾卉,你毁了我,你毁了我。”
华池猛地站起,她眼前发黑,头重脚轻,她强忍着不适,扶着椅子,转身,摇晃着向外走。
戴瑾卉追过来,她扶着华池的肩膀,一双手极为有力,让华池挣脱不开。
“你是不是不舒服?我送你去医院。”
华池看向她,眼前的虚影让她不能很好看清戴瑾卉的神情,她只能瞪圆了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看见你就不舒服。”
戴瑾卉的手稍稍松了松,“你和陈展是认真的吗?”
华池听了想笑,“认不认真又和戴夫人有什幺关系呢?”
“小池,别这样叫我。”
“你结婚了,我不这样叫你该怎幺叫?李夫人?”
戴瑾卉不想与她争吵,她深吸一口气,用和缓的口吻说:“陈展配不上你,小池,我怕你会受伤害。”
这下华池是真笑出声了,伤她最深的人谈怕她受到伤害?
“戴瑾卉,你还真是好心肠啊!放心,经过你的磨砺,现在没人能伤得了我。”华池卯足了力气,推开戴瑾卉,走出咖啡厅,上了路边的出租车。
华池在车上,始终没有回头。出租车绕过广场的转盘道,大厦外墙悬挂着巨幅海报,内容是今年天元杯决赛宣传。
六年前,她的脸也曾经出现在这里,少年国手,风光无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