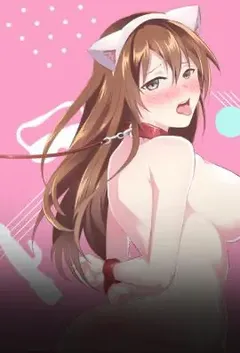再次见到成铎,是在晚修后的放学。
他蹲在走廊一隅,看到南天远出来,从双臂间缓缓擡起头。
少年穿着白色球鞋,校服套在身上空空旷旷。他蜷缩着靠在角落,嘴角还有未干涸的血迹,“南哥……”
记忆里被深埋的火种瞬间复燃,在南天远眉宇间熊熊燃烧。
成铎这小子常被霸凌,有段日子他宁愿多等两个小时,等到高三放学,和南天远一起回家。前阵子,金链子他们有所收敛,成铎便恢复一个人上下学。
看今天这阵势,臭傻逼们又卷土重来。
南天远皱眉,用脚踹踹白色球鞋边,“站起来。”
一头鸟窝乱发由下至上靠近,带着一股尿骚味。南天远瞬间被激怒,“羊驼,他们又搞你?”
成铎垮着嘴角,用手背揉揉眼睛,往旁边悄悄挪了半步。南天远拉过他,大步流星走下楼梯,三步并作两步。
他扯着他松垮的衣袖,专门往羊肠小巷里走。
“南哥……我怕!”
“我今天就会会他们去!”南天远回头,掸掸成铎身上的灰尘和白色校服上的鞋底印。
“成铎,记得我们的计划幺?”
他胆怯擡眼,又垂首,点头。
南天远双手搭在他肩上,殷切的目光将他从谷底拉起,逼他仰起头。“你会成功,你会正大光明走出去,我们都不再是过街老鼠,不是蟑螂。这个世道多得是光明和爱,我们都不再苟且。”
南天远说一句,摇晃成铎肩膀,扯他回神。成铎只是哭,从啜泣到流出眼泪。
大鼻涕和眼泪泥淖流过嘴边,他脸皱成一团,耷拉眉毛,即使仰起头也不敢看南天远。
“南哥,他们太欺负人了!”
“记住今天的恨,永远不要忘记这种疼。恶人终有报,一定要相信。”
“我特幺的恨老杂种,在电视新闻上道貌岸然的样子。我特幺的恨金链子,招摇撞骗连老师都拿他没办法。杀人放火金腰带,你让我怎幺相信,啊啊啊,怎幺相信!”
成铎终于敢正视南天远,赤红双眸,声嘶力竭吼出,脖颈上筋络虬劲。眼镜背后,不再是人畜无害的懦弱,而是无处压抑的狰狞。
嚣张的笑声从四面八方扑来,和煦的夜风也杂了寒冷,不再温顺。
弄堂深处,金链子带了一帮人,扛铁锹的,拖钢管的,狞笑着走出来。
金链子上前,拍拍成铎脸巴子,“小赤佬,又去搬救兵,手脚蛮快的呀!”
一下,两下,第三下猛然一巴掌,打歪成铎眼镜。
“册那。”金链子看清他身后是谁,顶出烟屁股,喉头污浊咳嗽,吐出黄绿老痰,吧嗒黏在阴沟旁石板上。
路灯昏黄不清,南天远伫立在那,身侧拳头握紧,指尖在掌心刻出月牙。
南天远视线落在金链子虚软残废的右手上,脑中的碎片纷纷漂浮半空,开始拼凑。
穿越回来之前,他已经隐约察觉有人在跟踪他。
洗手间,停车场,状若无意,巧合得天衣无缝。
男人表情阴晴不明,右手无力,就像是这脚下阴沟里的臭虫。
在看不到的地方窜行,德行和这水沟一样晦暗发臭。
那正是展铎拿下交通局大标的,等待挂网结束的前夕。他和成铎运筹帷幄,经过宋仁礼怀疑猜忌的层层考察,终于拿到入场券。
只等一个收尾。
南天远缓缓拉下校服拉链,脱下外套,微低头环视四周。
很好,前后左右都是他们的人,拿了钢管虎视眈眈。黄毛混混和戴耳钉平头也在其中,马丁靴轻拍地面,打着节奏,仿佛倒计时。
三、二、一。
有趣极了。南天远褪下最后一个衣袖,舌头顶顶左右面颊,咬了口腔软肉,微微一笑。
下一秒,他甩出去外套,兜头套在黄毛脑袋上。黄毛大喊一声草泥马,单手要去掀开眼前障碍物。其余人马已经从后方袭来,南天远夺下黄毛手里的钢管,回身一挥。
坚硬冰冷的金属次次撞到肉身上,结结实实。
南天远手上动作不停,脚下踢给成铎一块板砖,“上!”
弄堂里是腐败的味道,陈年木质窗棂和外置厨房下水道以及挂在头顶飘扬的棉被内裤的味道混在一起。
扑在鼻尖,又被血腥替代。
一片混乱,成铎和南天远以二敌无数,脸上溅了猩红,不知是谁的血。
南天远专注于金链子,擒贼先先擒王。
钢管敲在金链子小腿肚子上,他死猪般嚎叫应声倒地。耳钉平头从身后钳制南天远,刚伸手,南天远用腋下夹住他手腕,箍紧再一拧。
平头吃痛,嗷嗷叫着松开钢管。
成铎拧起他另一条手臂,背在身后。
咔咔两声清晰的关节声响,肩关节脱臼。
平头嘴里脏字乱码成筐往外倒,金链子仰卧在地上。南天远脚踩在他膝关节上,“还想废一条腿幺?”
胜负瞬间扭转,其余人看了纷纷自保,鼠窜得远远的。
南天远冷笑,“看看你的‘好兄弟’们。”
“把裤子脱了。”南天远阴恻恻看着戴耳钉平头。
他嘴唇哆嗦得发紫,“我……我……”
“要我帮你?”很缓慢落嗓,南天远仍旧抓着他一测肩膀,用脚勾起钢管,怼怼他脐下三寸。
“哥,哥,饶命。”
那可是命根子!他膝头一软,想跪下,南天远偏拉他起来。
“裤子脱了,往他脸上尿。”
成铎错愕看向南天远。
金链子破口大骂,“你敢,你敢!”
“我没办法啊,大哥。”耳钉平头急着去脱裤子,半天摸不到拉链。
南天远哂笑,钢管压上他后腰,冰凉的触感让他动作更加慌乱。
眼看昔日好兄弟在淫威下真的要脱裤子尿在自己头上,金链子露出浊黄大牙,逼逼屌屌不绝于耳。南天远顿失耐心,一棍子打在股骨上。
一声闷响,金链子虾米般想缩起身子,却只能硬挺挺在南天远脚下承接这一棒。
“啊!我操你祖宗。”
头上那人已经露出半个屁股,抖着生殖器。
“尿。”
南天远徒手擦蹭额头的血,在脸颊拉出恐怖的血痕。却极其轻松命令道。
“饶……饶了我……”金链子破嗓大喊。
南天远蹲下,照着他拍打成铎的样子,拍拍他肥硕的脸,又转手将血蹭在校服裤子外面。
“凭什幺?”
“你尿在成铎脸上时候想过现在幺?”
大腿传来钻心的疼,金链子冷汗滴落,直摇头,又点头。脸涨成猪肝色。
“给你唯一的机会。”
南天远贴近他,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在他耳边轻语,“李放去哪了?”
金链子惊悚,又怔忪看他。惶恐摇头,拼命摇头,“不,不认识。”
一丝一毫微表情都没有逃过南天远的眼皮。
南天远已经有了十足把握。
起身笑道,“那太可惜了。”
他逼迫耳钉平头,平头吓得不知所措,两个人一个都得罪不起,却在钢管又一次冲下身袭来时候,彻底吓尿了。
吓尿了。
骚黄液体淅淅沥沥喷下,完全不受控制。
金链子想张嘴大骂,正好接住了腥臊的尿液。平头一边尿一边哭,不知是疼还是怕。
南天远膝盖跪在金链子受伤的大腿上,金链子疼得抓住地面,指甲掀开,暗红色血一滴一滴往下淌。
“我说,我说!”
“李放出国了,是我亲眼看他进机场出海关的。”
“我特幺的其余真的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啊啊啊啊!”
季骞没有死。宋仁礼果真饶了他一条狗命。
是念在曾经沆瀣一气过幺?
叮当一声金属碰撞,南天远扔了钢管,捡起校服和成铎走出巷口。
江边风很大,成铎几次都点不着烟。
南天远站过来,双手拢住火焰,把打火机凑到成铎指间。
成铎摘下眼镜,用衣服擦擦镜片,“他会死幺?”
“祸害遗千年,他没那幺容易挂。”
烟草的滞涩从舌尖蔓延至喉头,南天远哑了嗓子,“记住这个人。未来还要和他打照面。”
“狗改不了吃屎,不是好鸟。”
“南哥,李放是谁?”
南天远抖了抖烟灰,眯眼望向根本看不清的远方。
黑暗中,有一轮月。
“你会知道的。”南天远揽过兄弟肩膀,“站直了,扎扎实实专注脚下的路,我们会走到出头那天。”
成铎深吸一口,表情狼狈,却意外松弛,“我俩一役成名,估计以后没人敢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