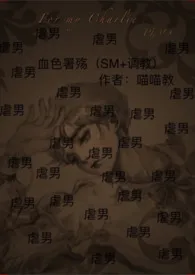自从一年前虎林村改成了种植园,村里的人便替负责人盖了一间屋。
上面的人要住,当然不能差,只是山远地偏,条件有限,富丽堂皇的宫殿办不到,整洁舒适倒也勉强。
陈燕真饮了酒,站在窗边夜风吹,隐隐头痛。
“陈先生”,阿昆出现在他身后,他也没发觉,“我让人给您煮了一碗醒酒汤,您喝了再睡吧”。
他撑着手掌按在太阳穴,“嗯”一声,“放着吧”。
一碗棕色的汤汁盛在青瓷碗里,冒着白呵呵的热气,陈燕真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望着天边月。
“还有事?”他问,身后的人仍久久立着不动,阴影打在竹楼的墙上,很难让人忽视。
阿昆略微犹豫,不知该如何开口,但又实在担心他,“陈先生,您为什幺不跟二小姐相认?难道就任由她……”
任由她当别人的妻子,成为村民茶余的谈资吗?
这分明不是先生的作风,他何曾将自己的东西拱手让人,更不必说是心爱的女人。
最珍惜的人失而复得,这种心情旁人很难体会。
陈燕真明白阿昆的意思,但他不愿强迫阿织,不愿用强硬的手段将她的生活打乱,他希望阿织开心。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自有分寸”。
只不过,他的退让和迁就,不代表放任,阿织终将要回到他身边。
屋外变得吵嚷起来。
陈燕真睡意全无,酒醉也被山风吹醒了大半,一晚醒酒汤放在桌子已经变得冰凉,却一口未碰。
挂钟差一刻钟到午夜整点。
他走出门外,保镖举着枪警惕地四处巡查,阿昆也在。
这座竹楼靠近村子中心的广场——说是广场,不过就是一片空地,平时用来举行村里的祭祀或是其他活动,因此陈燕真能看得见村民三三两两成群,都穿着新衣向广场的方向去。
不用陈燕真发问,阿昆便看出他的想法
“村民们打算在广场上守岁,一会儿还要放烟花”。
陈燕真抿着唇,若有所思。
“所有人都会去?”
“应该是吧,您要是觉得吵,我这就让他们散了”,阿昆说。
“不用”,他擡手否决了阿昆的提议,反而跨下台阶,也朝着广场而去,阿昆立刻叫几个人一起跟着他。
广场上插着一圈木杆围出边界,杆子上缠绕着红色的布条,上面似乎写着密密匝匝的文字,在空中飞扬。
村民已经到了很多,说笑声直冲天际,大海跟密林似乎也感受到了人们的欢欣,浪涌撞暗礁,猛兽啸山林。
只是在陈燕真出现的一刻,这种喜悦的氛围瞬间消散了大半。
毕竟刚才在平叔家里发生的事情,几个钟头的时间,足够在巴掌大的地方传遍了。
此刻陈燕真和他身侧的保镖,令大家心有余悸。
无关人员的喜忧他不在乎,在人群中暗自搜索。
金边眼镜下的一双眼睛微微眯起,瞳孔里的映画如走马灯,不过片刻便定格。
女孩子姗姗来迟,鬓边别一朵粉色的小花,衬得人比花娇,衣裙换过了,不是傍晚时的蓝色裙子,而是一身红,手腕上带着彩色的编织手链,坠着两三个小铃铛。
叮铃铃,隔着喧闹,仿佛也能听到铃铛清脆。
她还真是喜欢铃铛,五年前在琅卡寨,她就对衣裳上面的小铃铛爱不释手,现在也没变。
严肃的面容有了缓和,但在见到与阿织手牵手的男人时,这一点高兴就被瞬间击碎。
情绪的复杂转变,阿昆看在眼里,陈先生一向不爱热闹,原来不过是想见二小姐。
然而,她身边的乌蝇实在碍眼。
“陈先生,要不要把他——”后面的话没挑明,只是手上比个动作,心知肚明。
“别多事”,陈燕真皱眉,倒不是他多年吃斋念佛,就真的生出了慈悲心。
毕竟这家人救了阿织,阿织感恩戴德,若是贸然动手,她一定会怨他。



![[短篇]大玉儿与多尔衮(H)1970全章节阅读 [短篇]大玉儿与多尔衮(H)小说免费阅读](/d/file/po18/626819.webp)


![1970全新版本《江濯。[GL|武侠]》 看山。作品完结免费阅读](/d/file/po18/70498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