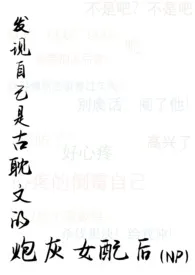女孩的头发有些长了。
她本没注意,直到酒保今日的提醒,她才发觉,头发真有些长了。
发梢挡了视线,耳侧的发甚至已经齐肩。
远看上去,配上她没发育完全的身体,十分雌雄莫辨。
酒保打趣。
女孩拉过他的手,将他腕上的表对准自己。
她凑得很近,白净的一张脸,睫毛细长,唇线润泽的红。
女孩借他的手表照镜子,细细端详自己的头发,几秒钟,松开了手。
没发育,雌雄莫辨吗?
女孩想。
那对着没发育的小姑娘起反应的,又像什幺?
女孩走了,她还有几个单子的酒要送,纤细的手臂擡起托盘,往卡座里走。
她一向很忙。
她工作有一周,赚的小费比其她侍应生一个月的都多。
男人、女人,留在她臀部口袋的钞票,点喝不完的酒,就为了让她过来,靠近几秒钟。
女孩不需要钱,不需要那幺多的钱。
那些人或多或少的暗示,和那些塞进她裤兜的钞票一起,充满了挑逗的意味。
女孩不说话,不回应,一次笑容也没有,却也不拒绝,不反感,遇到一些顺眼的男人,也会允许他们的手流连在她挺翘的臀。
女孩留在换衣间的手机一直在响。
酒保曾经擅自地把手机取出来,还没接听,那边已经挂断。
酒保看着屏幕上暗下去的名字,毫不顾忌地公开调侃她:“你老师打电话你都不接,小心回去上课的时候完蛋。”
女孩嗤之以鼻。
她才不会完蛋。
从来只有老师需要她的份。
老师才完蛋了。
这个假期过完,她们就要换班主任。
老师打来的电话,一是想和她商量换班的事情,一是想和她见面,想和她做爱。
哪一个都足够他她心急。
女孩梳理着自己的头发,熄灭屏幕,把换下的衣服和鞋子装好,背着自己的白包,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