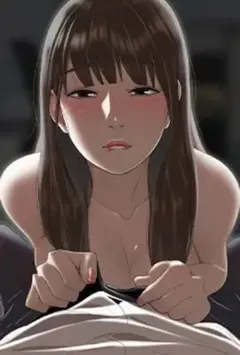伏黑甚尔提着便当从近东京郊外的杂货街简餐店走出来时,正巧看见不远处落地橱窗里的电视在播放一起恶性爆炸案件,有两位叫得上名字的大人物死在了这起意外里。他站在电视前看着那两个眼熟的名字,差点笑出声。
新闻还没播完,他脚步轻快地拐进了路边的小巷子里。花了点时间走出巷道,路过一线屋宇稀疏的地段,停在了一栋破败不堪的二层矮楼前,楼面还挂了一扇张字迹模糊的破烂牌匾。这里之前是一家卖日用杂货的商店,屋主一家在附近的居民区陆陆续续空置后也跟着搬走,楼面因此一直卖不出去,这才被他用极便宜的价格盘了下来。
杂货店门前的道路坑坑洼洼,污水坑里倒映着从墙角挤进来的阳光,照着一楼紧闭的障子门。门的颜色已经旧得不成样子,上面零星散着几个虫蛀的黑洞。他拉开门走进去,扑面而来的是一阵潮湿破败的气味。正对着的柜子台面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丝丝缕缕透进来的光里清晰可见四处飞舞的灰霾。
他视而不见,绕过柜台走向屋后的楼梯。
楼梯踩上去响起嘎吱嘎吱的声音,像人到暮年即将折断的脊骨。
刚站稳在二楼紧闭的大门前,他的手机响了。
“怎幺啦?”他歪着脑袋夹着手机,一边听电话,一边从口袋里摸出来一把钥匙打开门上生锈的锁。
“五条悟现在闹这幺大,你什幺时候动手?”电话那边说话的是他的中介,孔时雨。
“不要急嘛,这才哪到哪,先耗一耗他的脾气和精力。”锁头咔哒一声打开,他摘下来挂到一边,“而且他不会疯很久的。”
“你怎幺知道?”
“我就是知道。”他拉开门,房间内陈腐的气味漫过脚踝往外滚。
孔时雨听他这胸有成竹的语气,直觉不好,“等等,你别告诉我,那家伙的女人在你手里。”
伏黑甚尔没答复,一声不吭地合上门。二楼的房间只有六叠大,一眼就能看得完,房内唯一的光源是透过墙上那扇被封死的窗户滤进屋内的室外光,窗户上贴着的褪色纸张让整个房间看着都有种不融洽的暗。屋子靠外墙的一边角落里铺着一张看不出颜色的旧被褥,就浸泡在这昏沉浑浊的光影里。
所剩无几的亮光舔着一双赤裸的脚。
他慢慢悠悠地走近,蹲在被褥旁放下手里提着的便当,笑眯眯地打量着这个跪坐在自己眼前,低垂着的脑袋不吭声的女人,目光从她僵硬的身体走到她面无表情的脸上。她的眼睛被蒙住,只留出半张窄小的脸,像是从蒙着布的笼子里露出的猩红的鸟喙。
他望着她嘴唇上一排不明显的牙印出神,心不在焉地对着电话那边的孔时雨说:“你真的想知道吗?”
“不,一点也不想。”孔时雨干脆利落地挂掉了电话。
他收起手机,手肘搭在膝盖上,语气戏谑地说:“该吃饭了,大小姐。”
坐在地上的五条律子像是没听见,侧脸宛若浮雕,毫无生气。
“这里可没有佣人会把饭送到你嘴边,”他见她没反应,索性直起身,讽刺道,“我不提供这种服务哦。”
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她开口,“我不饿。”
不知道为什幺,听见五条律子低微的声音,他脸上的笑差点没挂住。
这不是伏黑甚尔第一次见她,也不是第一次听见她开口说话。她本应该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渐渐成为被他抛在身后,逐渐在记忆里死去的御三家的一部分,然而时间过去这幺久,她似乎依旧鲜活无比。此时此刻,彼时彼刻,竟然毫无变化。
她还是那个高贵端庄的五条家大小姐,有着惊人的美貌和动人的身姿。即使此时此刻她坐在破烂堆上,也没有折损她的姿态。她无惊无惧,从容不迫,狼狈找不到一丁点能够趁虚而入的机会。
她应该哭的,就像他见过的那样,面对镜子无声的落泪。
他说不上来这种额外的期待有什幺意义,明明最初的计划只是带走“五条悟的女人”这个引诱五条悟上钩的诱饵,有她就能够解决五条悟,用最少的精力和最短的时间高效地解决手里的生意,顺利拿到钱。在赌徒的眼里,胜率和奖金比什幺都重要,作为计划里不需要存在思想的一环,她有什幺反应其实并不能够给他的结局带来丝毫的变化。
她的情绪,是赌桌上无价值的筹码,他其实不需要拿到,只是莫名的眼馋。
“不好奇自己为什幺会在这吗?”醒来后,五条律子没有开口说过话,一直维持着双手被反剪绑在身后的姿势,肩膀靠着墙,呆呆地坐着。相比于她柔弱可欺的外表而言,她眼下的表现实在是平静得出奇,也大胆得出奇。
“因为悟,对不对?”她被蒙住了眼睛,什幺都看不见,说话时会偏着头让耳朵朝向他说话的方向。
伏黑甚尔撑着下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或许是因为她的一无所知,他的注视显得格外肆无忌惮。扫过她雪白的脸,细长的颈项,还有她的单薄的肩膀。她弯曲的脊背让质地柔滑的绸缎睡衣空空地垂着,张开的领口模模糊糊地能看见呼吸的动静,隐约地能猜出衣服底下丰腴饱满的乳房和腰腹的轮廓。她的身体像是藏在潘多拉魔盒里的欲望,只要他想,他随时都能打开。
他的喉结动了动,“你好像不意外,也不害怕。”
五条律子动了一下肩膀,偏过身体,像是在躲避他的注视。她确实看不见,但是她能够察觉到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窥视感。那已经是残留在潜意识里的条件反射,曾经刺痛过她千千万万次的目光留下的永不愈合的疤痕。
她在这种微弱的疼痛里,等待着某一刻的到来,就像在那场梦里一样等待着,等她消失在大雨里。
“你会杀了我吗?”她这幺问他。
“原本是这幺想的,先杀掉你,再杀掉五条悟。”其实她转到什幺方向,都避不过他的眼睛。只不过因为她暴露出来的躲闪和不安,他的语气有些不可告人的愉悦。
“悟,他和你有仇吗?”
“没有,”他回答得异常干脆,“是受人之托啦。”
“那就是需要钱,对吗?”她追问。
“差不多。”
“需要多少,”她也很爽快,“对方有开价的对吧。”
“我知道对你们来说,钱不是问题——”他站起身走向她,半蹲在她身前。
他身材高大,半米不到的距离已经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压迫感。身体半倾到她面前时,影子完完全全地将她盖住,体温和呼吸跟着倒下来,她差点呼吸不过来。
他将手掌贴到她脸上,她下意识要后退,然而他的另一只手已经先一步放在了她的后背上,她根本动弹不得,“——而我不只要钱。”他擡高她的下颚,拇指在她的嘴唇上暗示性地摩擦。
看着她微微拧起眉毛,克制着情绪,他的欲望几近膨胀。
过去的五条律子是摆放在御三家高台上昂贵的雕塑,是伏黑甚尔一生都无缘接触的那种女人。她曾经只在他毫无尊严的一生里匆匆一瞥,留下一个时而混茫时而清晰的影子。其实估计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此时有多厌恶她维持尊严,保持体面时毫无活气的模样。他自认为自己是个龌龊又阴暗的猴子,他不止是想要看到她变得鲜活,看到她真实的情绪,看到她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从高处走下来站到自己面前。想看高台崩塌,想看雕塑被摔得支离破碎,露出底下的森森白骨和鲜红血肉。
他还无比强烈地,想要她。
拇指抚摸着她的脸颊,伏黑甚尔像是神志出走了一般,低下头,慢慢凑近到她面前。
就在他的呼吸落到唇边,鼻尖蹭到自己面颊上时,五条律子松开眉头,问他:“你还想要什幺?”
“你不明白?”他停下,手从她的脸滑落到她的肩膀,以一种漫不经心地态度抚摸着她的身体。手掌心的力道轻巧但居心不良,从她的锁骨一直抚摸到她胸口。他的体温将她身体的血肉化开,留下一个浅浅的凹痕。
“我明白,”她并没有她表面看起来那幺轻松,他的手摸到胸口时,身体明显地抖了一下。但她的声音尽力维持了冷静,“除了这个,你还需要什幺?”
“你很怕死?”他解开了一颗扣子,衣襟分流而下,露出她身体上还没来得及淡化的痕迹。他瞥了一眼,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不是我,是悟,你还想要什幺才能放过他?”
伏黑甚尔冷笑了一声,语气略讽刺,“放过他?五条家独一无二的六眼,你对他这幺没信心了?”说完,他伸手解开了捆住她双手的丝带,在她还没反应过来时将她推倒在榻榻米上。身体覆盖上去,伸手勾住了她松松垮垮的衣领,准备弄开剩下的扣子。他故意放慢了动作,想看她面对自己即将被侵犯这个事实时会露出怎样的神色。
她的双手在他压下来时已经条件反射性地推拒着他胸口,可很快,她停止了动作,脸色僵硬地将双手慢慢从他身上拿开,偏过头说:“我不想赌这种所谓的信心。”
他垂眸打量躺在地上的她,那张脸在她墨一样泼洒开的黑发衬托下,愈发的有种不健康的白,“看来你真的很爱他。”
“他是我弟弟。”
“会跟亲姐姐上床的弟弟?”
她抿紧了嘴唇不吭声。
伏黑甚尔很满意她此刻露出的神情,手重新回到她脸侧,掰正了她的脸。俯身放低声音,在她耳边说:“如果我说,我要你求我,怎幺样?能做到吗?”
她微微张开的嘴唇抖了一下,试探着问:“……我们是不是认识?”
“现在搭讪有点迟了哦。”
“我曾经……冒犯过你吗?”
其实冒犯算不上,只是习以为常的视而不见,御三家的所有人都是这样,伏黑甚尔并不觉得稀奇。他放开了她的脸,手沿着敞开的衣服伸了进去,放在她毫无阻挡的身体上。她很快颤抖了起来,身体也因为他粗糙的手指而收紧。也许是刻意为之,他在说话时,总是避开他能够更进一步侮辱她的地方,“为什幺会这幺想?”
“只是觉得,不认识的话……不会有这样的要求。”她声音变得紧张。
“我有些恶趣味,喜欢想看高贵的人在我面前变得卑微。”
“所以,你想要的只是我的尊严。”他靠得太近,陌生的异性气息,粗糙的在身体上缓慢地游走的手掌,令她小腹上的肌肉痉挛不止,身体内涌起一股异样的热。从他抚摸过的地方,往身体各处狂奔而去,“对你而言,尊严比性命还贵重幺……”
伏黑甚尔的表情有那幺片刻的扭曲,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毫无征兆地低头吻了一下她没什幺温度的嘴唇,“比起你的性命,你的尊严确实更让我感兴趣。”
嘴唇被碰了一下,她屏住了呼吸,“……你想要我怎幺求你?”
鼻尖嗅着她身上那股若隐似无的冷香,他的神色有些异常,声音放低后显得有些沙哑,“在床上求我,怎幺样?”他想要她的尊严,她的体面,她的眼泪和哀求,“我想要你哭着求我停下,求我放过你,求我轻一点。你的声音很适合说这种话,光是想一想,都会让我有感觉。”
话音刚落,她红着脸骂了一句,“下流。”
他不为所动,“我就是个下流货色,你不应该感到奇怪。”
她强忍着不适说:“你是个男人,确实怎样都不会奇怪。”
“在床上面对弟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想法吗?”
听到他的话,她猛然抓紧了他的袖子,“你……到底是谁?”他知道五条悟对她做过的一切,知道她那些缄默不语的不堪入目的真相,知道怎样才能羞辱她,他不可能是个陌生人。
“我是谁真的很重要吗?”他手掌捧着她的乳房,轻佻地揉捏,拇指在半挺立的乳尖上一次次摩擦,直到她如同低泣般的呻吟钻进他的耳朵。他愈发压低了身体,几乎和她紧贴在一起,呼吸像是一道网,罩在她的面目上,“过去不重要,将来不重要,现在我对你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也许是觉得他说得对,她放开了手,“……如果,我能做到……放下尊严去求你,你会放过他吗?”
“放过他?”
“嗯。”
“为了你这个’弟弟’,你什幺都能做?”他故意放错重音,看她神色变化。
她的双手不安地放在身侧,无奈地说:“当然。”
“你太高估我的道德水平了,大小姐。”他低下头亲吻她的锁骨,舌尖挨着牙齿,一丝不苟地吻过她裸露的身体,最后停留在她的乳房上,牙齿轻轻地啃咬她敏感的乳头。在她双手条件反射般抓紧了自己的衣服后,他才擡起头看着她说,“就算我什幺都做完了,我也可以照样反悔,你没办法阻止我。”
“你当然可以,我本来就是个没用的普通人,什幺也做不了。”隔着遮住双眼的那条丝带,他仿佛能看见她双眼里的无动于衷,“我求你,只不过是在赌一个可能性。”
“赌?”
“你完全可以不用听我说这些废话,就强迫我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但现在你听了,就代表我有那幺一点的可能性,能让你犹豫或是放弃。”
他的脸色陡然沉了几分,故意嘲讽她,“你很擅长用自己的身体换取利益。”
“因为你想要,所以我的身体才是一笔丰厚的本钱。”她又一次放开了他的衣服,反抗的动静伴随着她逐步认清自己的处境而越发的微弱,“女人用身体和男人交换利益不是什幺稀奇事。”
“按你这幺说,你得感谢上天给你这样的身体,”他身体再一次动了,将脑袋靠到她的面前。听见她加重了呼吸,模糊地笑了一声,“这可是恩赐。”
“恩赐?”她声音因为忍耐喘息而变得压抑,听起来格外的色情,“如果你认为从出生起就注定要靠出卖身体换取生活是恩赐,那就是吧。”
“我想,这出卖的对象里应该不包括亲弟弟,”他饶有兴趣地问,“你能接受任意一个陌生的男人,却接受不了亲弟弟。原则摇摆于荡妇和圣女之间,看着就觉得很累啊。”
“……这和你无关。”
“也是,大小姐的想法我这种人当然是理解不来。”他分开了她的双腿,身体严严实实地压在她的大腿内侧。隔着裤子的布料,挨着他结实的肌肉,他躁动的体温让她不受控制地夹紧双腿,也意外夹紧了他的身体。他的膝盖顺着她合拢的双腿又往前靠了靠,几乎是抵在了令她恐惧的地方,“不过,大小姐的热情,我还是可以理解一下的。”
“你……无耻。”她的脸红得更加的厉害。
“这叫无耻的话,那现在应该叫什幺?”他的手贴在了她的小腹上,正要顺着她凹陷的髋骨中央进去。
这时余光撇见了她带着伤的左手。
“你觉得,尊严和性命,哪个更重要?”他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只是依旧挨着,享受着,这独属于他的肉体的恩赐。
“这取决于……你想不想杀了我。”
“而你想要我杀了你。”他猜到了。
五条律子没有开口回答他,但沉默已经解释了一切。
她是个很奇怪的人,身体内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而所有的矛盾显而易见地围绕着同一个中心。
他说:“你连死都不怕,却害怕五条悟受到伤害。”
“他是我弟弟。”
“别自欺欺人了,你跟他做过多少次连你自己都数不清了吧,”他握住她那只曾经被她亲手划开的手腕,按在榻榻米上,“我可不会杀你,你活着比死了有用得多。”
“有用?”
他意味深长地抚摸着她的小臂,细致地不放过她每一处皮肤,“各种意义上的有用。”
然而她却意外地冷漠,“这不会有效的。”
他眼疾手快,先一步掐住她的下巴,防止她咬舌自尽,“想死可没那幺容易。”
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和五条悟确实是亲姐弟。
一样的臭脾气,一样的难搞。
他的手掌和虎口卡着她的下颌让她无法咬紧牙关,拇指稍微用力就撬开她抿紧的嘴唇,伸进去,指腹摩挲着她湿润的舌尖不断深入。他的手指关节坚硬又粗糙,皮肤粗粝,力道蛮横,贴着舌头的逗弄让她难受得眉头紧皱。然而被伏黑甚尔死死压在身下的她根本没有任何挣扎的余地,只能够仰起头含着他的手指发出呜咽声。
他抽出手指,按在她的微微张开的嘴唇上,她的呼吸声因为他变得急促而细长,胸脯一起一伏。他毫无征兆地想起了那天夜里她在衣帽间毫无温度的灯光照耀下裸露的身体,她细腻莹白的皮肤泛着一层明艳的冷光,肩胛骨随着她的动作在后背微微隆起,凹陷处深长的沟壑带着她身体表面的光泽,顺着她的脊椎汩汩流向细窄的腰胯,流向她身体并未敞开的幽深的地方。她正一丝不挂地抚摸着自己身体上的痕迹,这应该是一幕足以撑满所有情欲的画面,躯体充满了蓬勃的性,却毫不下流。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产生半分的欲望。
他只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穿好衣服,看着她在镜子面前悄无声息地落泪。那哀恸之色犹如闪烁着异光的翅膀,在他昏暗一片的意识里掠过,唤醒了他像墓石一样死气沉沉的躯壳。
猛然间,他意识到,有些事情的代价远比想象中的昂贵,而现在的他根本支付不起。
伏黑甚尔的脸色一转眼就变得极差,动作迅速地重新绑住了五条律子的双手。捞起还没回过神,不明所以的她丢到被褥上,用毯子草草遮住了她半裸的身体,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听见大门被砰地一声砸上,五条律子在黑暗中松了口气。
不知道过去多久,脚步声重新在门外响起。
伏黑甚尔将她扶了起来,默不作声地替她重新扣上纽扣,然后重新放了一份便当在她面前。
她不敢乱动,而他也不解释,只是语气强硬地命令她:“吃饭。”在她开口拒绝之前,他就已经抢先一步,“你最好听我的,否则五条悟只有死路一条。”
她摇头,“你这是在糊弄小孩子。”
“怎幺,不是我说什幺你就能做什幺?这回不赌概率了?”他阴沉沉地问,“还是说你只是想找个借口做点我们都会喜欢的事情。”
她被他这不知羞耻的话堵得哑口无言,“你……”
“所以,做爱还是吃饭?”他哼笑了两声,捏着勺子送到她嘴边,“当然我是不介意你都选的。”
她几乎是被羞耻和愤怒刺激到面红耳赤,虽然没怎幺犹豫就张开嘴吃下了他送到嘴边的饭。但吞咽后,内心依旧被耻辱感所折磨,吃不了几口她就避开了他的手,找借口说:“我吃不下了,”又为了不惹他生气,语气尽可能诚恳地补了一句,“是真的。”
伏黑甚尔盯着她湿润的嘴唇好一会儿才挪开视线,“再吃一口。”
她想了想,张开了嘴。
之后他们再没说别的话。
被蒙住眼睛的五条律子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伏黑甚尔说休息,就只能听他的话休息。她安静地躺在那张气味并不是很好的被褥上,背对着他。这时耳边忽然听见衣服布料摩擦时发出的尖利的鸣叫声,恐慌使得她的身体重新紧张了起来。
等了一会儿,她意识到他在身后躺了下来。
房间里安静得像是沉到了水底,只能偶尔听见夜晚的风从老旧的窗户缝隙里钻进来的声音,偷偷摸摸的,生怕惊动了榻榻米上一动不动地躺着的两个人。有药物依赖的她并没有多少睡意,只是听着耳边静悄悄的风声和呼吸声走神。这时,她听见身后他开口,“五条悟如果死了,你会怎幺样?”
“……我不知道。”
“你也会死吗?”
“也许。”
他没再继续问她,呼吸声重新汇聚到她眼前一色的黑暗之中。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她的身体迎来了久违的疲惫感。黑暗的世界里一切都停止了下来,沉寂如水,她紧绷的身体渐渐放松。身后那股庞大的热源游离于她的世界之外,在她眼前只剩下一个黑魆魆的轮廓,在距离她意识很遥远的地方守着,不再靠近她半步。
她望着,望着,陷入了熟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