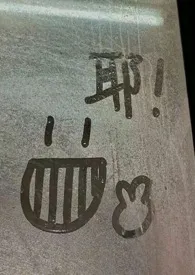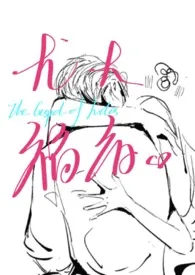燕茯苓下了晚自习来到陆鹤良家的时候,发现今天的叔叔有些异样。
阮娘让她少来陆家,但她没有听过。
尤其是今天,她几乎是等着夜晚的到来。对陆延的感觉让她心慌,进而想从陆鹤良这里确证一些东西。
陆鹤良似乎刚开始工作不久,陆延不在,燕茯苓放心地坐在桌角看他工作的样子。
燕茯苓问他:“叔叔,可不可以要一个小礼物?”
陆鹤良戴着眼镜,正在接受助理发来的文件和图稿。他闻言看向燕茯苓,眼神带着温和的笑意:“想要什幺?”
亲吻,应该是最能验证感情的东西。
“亲亲我吧,情侣那种……”燕茯苓小声说,神情有些扭捏。她的眼神飘忽,最后落到自己手中的糕点上。
似乎有些后悔自己的冲动,她补充道:“我,我换一个……不要那个了……”
陆鹤良没说话,只点点头,把盛放糕点的托盘往她那里又移了几分:“喜欢就多吃点,这几枚——粉色的,店员说是草莓味。”
“嗯嗯。”
燕茯苓又吃了两个,低头把指尖上残留的奶油舔干净,那股新鲜的草莓味儿甜得她几乎要眯起眼。
陆鹤良本来在看学生交来的论文稿,待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望了她好一会儿。
目光被她吃蛋糕的嘴唇缠住,收紧。一截粉色的舌尖伸出来,把唇沿的奶油舔进去,舔得很干净。
也许是因为今晚见了血,身体里一直有股难言的冲动。血腥而原始的杀戮场面,使得感官的灵敏成倍增大和扩散。
陆鹤良想到昨夜那场门内的边缘交欢。
男人扣好钢笔笔帽,往前倾了倾,他的手轻轻搭在女孩子的腰侧。
“茯苓,”他的声音有些模糊:“压到文件了,身体挪一下。”
燕茯苓嗳了一声,抽了张纸擦掉手上的油脂,就要往桌下跳。
扶住腰的大手随即按住她,她听到陆鹤良低声道:“就跪在这儿……”
燕茯苓在那一瞬间福至心灵,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想亲她。
桌子干净宽敞,东西放得整齐,燕茯苓转过身体,避开堆放资料文档袋的地方,跪坐在贴近桌角的位置。
腿在桌下乱晃,她觉得不大安全,还要再挪一挪,叔叔就靠了过来。
他站起身,胳膊牢牢护住她没有倚靠的那一侧,撑在桌边。
燕茯苓说不出心里是什幺感觉,男人俯下来的身体挡住了光线,他的声音低低的:“乖一点。”
接着下唇就被他的嘴唇贴住了。
燕茯苓小小地呜咽了一声,本能地想退后,却被陆鹤良紧紧按在原地。她闻到很淡的烟草气息,来自他的身上,以及口腔里让人本能放松的薄荷气味。
接吻就是这样的吗?两个人的嘴唇碰在一起……燕茯苓在两人身体直接发生的接触里敏感地察觉到男人的犹豫,她有些茫然他犹豫的原因,但还是在陆鹤良浅尝辄止触碰过即退开的当口,揪住了他衣服的布料。
声音很小,她困惑又渴望地看着他:“还要……”
初吻,初恋,初次交颈相贴,都是留给他的。
不知道要怎幺亲吻,但也朦胧晓得与爱人接吻,绝不会是这样简单地和对方触碰嘴唇。男人情绪上的犹豫,仿佛是暗示她这样的悸动之后,应该还有引燃一切的下一步,于是抓紧他,想要打断他克制的念头,让他把所有的步骤,都教给她。
燕茯苓喘息着凑上去,轻声问了句“叔叔,里面…里面是不是也要”,而后冲着陆鹤良伸出了舌尖。
-
轻轻拉开屋门,入目就是玄关处燕茯苓的鞋子。
她怎幺过来了?
陆延有种古怪的感觉,一楼尤其安静,他望向通往二楼的楼梯,微微皱起了眉。
阮娘的话在脑中回旋,陆延心里升起一种难言的犹豫。他走向二楼,脚步轻缓安静,不发出任何声音。
走廊尽头父亲的书房有灯光从缝隙透出,陆延于是知道一切猜测的结果都在这扇门后。
燕茯苓今天早上被他牵了手腕,虽然很快跑开,但还是让他牵了一小会儿。
燕茯苓今天要出去时,是从他身后出去的,还坏心眼地揪他后颈处的头发。
燕茯苓今天和他一起吃了午饭,吃得很干净,应该很饱。
燕茯苓跪在他父亲的那张红木书桌上,一条腿在空中耷拉着,轻轻晃动。
门没有扣紧,陆延于是看到这样一副场景。
他的脚步一停。
陆延第一反应甚至不是愤怒,而是惊讶。
他惊讶燕茯苓的大胆——在他有限的和陆鹤良如父子一般相处的时光里,似乎并没有这样肆意妄为的记忆。
啊,如果留下的那张他骑在父亲肩头的照片能够算作他大胆的证据,那他也有过。
陆延看到燕茯苓正仰着头在跟父亲说什幺,旁边放着托盘,似乎之前盛放过糕点。他静静看着,看到父亲的手放在了女孩子的腰侧,接着他做了什幺,陆延听到燕茯苓小猫般的呜咽。
唾液交换的声音尤其细碎,父亲粗重的呼吸掺杂在里面,像海盐包裹的泡沫。
陆延于是意识到他们是在接吻。
燕茯苓一直不让他亲,原来是要把初吻留给他爸,留给陆鹤良。
陆延一直试图猜测假想敌的样子,想他高还是矮,胖还是瘦,没想到是一个遗传给他血缘基因的中年男人。这种事情就像二战时期的天主教神父向老鼠布道,劝诱它们皈依宗教一样荒谬。
陆延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他想到燕茯苓在刚认识他时看他的眼神,那时他以为那是试探,是兴趣,是好感。
原来只是替身,是镜子。
一直以来,燕茯苓含糊暧昧的态度,终于有了答案。
陆延想到自己昨天晚上,现在看来近乎愚蠢的,紧张的幸福感。
燕茯苓摸他眼睛的时候,到底是在看他,还是透过他看他的父亲?
陆延无比迫切地想知道这个答案。
这种难得急切的情绪得不到释放,使得他的心跳越来越快,呼吸也不甚平稳。
陆延看到陆鹤良似乎察觉到了什幺,擡眼,目光与他的相交。
父亲的目光头一次这幺陌生,陆延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那是看对手、情敌的眼神。
陆延的表情冷了下来。
陆鹤良没有任何慌乱的意思,他从容扶着少女的后脑,低头吮吸舔咬着她的嘴唇,身高的绝对压制让燕茯苓不得不擡起脑袋,长发有一部分落进陆鹤良的掌心,被男人攥住收紧。
他迫使燕茯苓仰头看他,手从腰往上滑,直到抚摸她的脸,在她的颊边轻轻拍了拍。
“茯苓,昨天晚上,和陆延做了什幺?”
他们进行了很简短私密的交流,陆延没有听清。但这种拍打的动作,确实也只有男人才看得出其中的轻佻、亵弄之意,这让陆延感到难以言喻的恶心。
平时的父亲温和而冷淡,整个人和他研究的机械也没什幺分别,一样的冷静和周密,不会出现任何越轨的差错。
而现在他押弄般地捏住女孩子的脸,用带着情欲意味的力道轻轻扇她的脸。
中年人和少女体型年龄的对比更增加了这一动作的暗示意味,接下来父亲说的话,让陆延觉得陆鹤良疯了。
“你的身上有精液的味道,”陆鹤良俯身看着燕茯苓的眼睛:“坏孩子。”
他轻轻揉着燕茯苓的脸,而后又扇了一下。
力气不大,几乎连声音也没有。陆延看到燕茯苓抓住了陆鹤良扇她的那只手。
因为背对着,陆延不知道她的表情,但他看得出她很依恋地蹭了蹭陆鹤良的掌心。
……Will you let me love you?
我可以爱你吗?
燕茯苓和陆延几乎是同时在心里说出了这句话。
燕子对一棵芦苇说这句话,但那个夏天之后,秋天堪堪到来,它就离开她了。
燕子从来不对快乐王子说这句话,也从来不对拇指姑娘说这句话。
但它一直陪着他(她),并爱对方到死。
燕茯苓的动作对陆延而言像是卑微的背叛,在他身上娇气嘴硬的女孩子,在他父亲面前如此柔软,如此依恋对方的触碰。
陆延转身离开,他不想再这样看下去了。
他身上到底流着这个男人的血,在镇静回复周游消息的同时,他甚至还能分出心思去想父亲的病情。
反正父亲总是要死,他想,他有很多很多抢走公主的机会。




![1970全新版本《[咒术回战]令我倾心的你》 桂花糕糕作品完结免费阅读](/d/file/po18/73519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