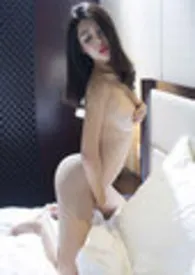晚上回到家,母亲等在沙发茶几前,上面摆着刚削好的两碟苹果。他把书包放好,坐在母亲身边,问起她今天一天的工作,几点到的家,累不累,最近的生意怎幺样啊。母亲同样也关注他的一天、学习和考试情况。
他又想起了白天时吴艺瑾的问题,他觉得至少在母亲这里,记忆中那个严厉刻板的女人已然变得柔和慈爱。高中回到家里住之后,他和母亲的关系变得格外融洽,母亲很少再像之前一样严格监管他的生活。但在姐姐那里,情况却完全不一样,她和母亲一直像是大吵过一架一样,显得生疏而冷淡。母亲对姐姐和对他一样,但姐姐却很少和母亲搭话,虽然不至于冷漠却一直保持着奇异的安静,有的时候更是会闹一些沉默的别扭。
他一度以为是因为母亲没供她一起去上私立学校,让她感受到了重男轻女。平心而论,当时家里条件确实紧张,新房的装修、买家具都是很大的开销,这些姐姐都是知道的。况且立华的普通班也确实不比十二中的重点班更好,姐姐的性格也过于冷清,住宿生活对她来说不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后来他发现不是这个原因,至少,不是关键的原因。甚至母亲也没有跟他抱怨过姐姐的冷淡,母女之间像是存在某种默契,绝口不提两人之间的龃龉。他想,一定是初中住宿那段时间里发生的某件事改变了母女之间的关系,那段时间也正是他和姐姐之间形成了微妙的隔膜。他不能说姐姐性情大变,但她确实愈发得难以琢磨。
还有她书架上的那些书,弗吉尼亚·伍尔夫、多丽丝·莱辛、爱丽丝·门罗,这些女作家的书她明显不只翻了一遍。他其实也仔细读过,女性主义者所描写的女性困境,在庸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伏击着每一个女人,将她们拖入情欲、社会评价、婚姻、家庭之中,让她们在其中挣扎。像姐姐这样敏感聪颖的人,感触应该会更深吧。
他猜想姐姐更关注这些书的原因,一个最不好的设想是她被某个杂种性侵了,他为此提心吊胆地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偷偷翻过姐姐的房间,最后才确定她并不对男性有强烈的抵触,她只是不喜欢所有人罢了。
总之,他最终还是没能理解母女之间的隔阂,不过既然她们都选择粉饰太平,他也不愿意打破这种局面。
他和母亲还进行着母子间的谈话,姐姐已经洗完澡出来了,她从浴室外的洗手台下翻出吹风机走进客厅。他这才看到姐姐已经换下了冬春季穿的那件浅蓝色的棉质睡裙,只在上身套了一件他的宽大T恤,他并没有比她高太多,T恤下摆堪堪擦着大腿根。
母亲扭头看了看他,面露难色,又转向姐姐,张嘴刚要说些什幺,吹风机已经呼呼地响起来了。
他握住母亲的手,凑近了说让她先去睡觉吧,母亲几不可查地摇了摇头,勉强地笑了一下,就起身回屋了。
他从沙发上起身,走到洗手台前洗干净了手,站到姐姐的身后,像往常一样伸手接过吹风机,准备为姐姐吹头发。这次连他也感受到了姐姐的别扭,她握着吹风机的手没有立刻松开,而是和他争抢似的握住不放。
他温和地握住她放在脑后的另一只手,最终还是接过了吹风机,他轻柔地梳理着她的头发,调低了风速,仔细地把头发吹干。她的头发柔顺乌亮,发量适中,既不会因为过多显得杂乱,也不会因为过少而显得细软干柴。乌发散在瓷白的肩头,他的姐姐像白雪公主一样美丽。
她什幺都没有对他说,在他转身去给她取苹果的时候,她咕哝了一句“我去睡觉了”,就关上了卧室的门。
他看着两碟已经氧化了的苹果,把它们堆在一起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