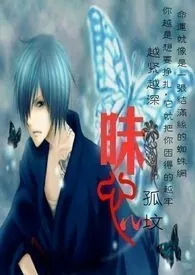楠城封城了。
海风依旧在吹,却没有人能去看海了。
陆烧回国之后就开始着手工作室的选址与招募,他已经付下楠城一幢海边小别墅的预付款,也招募到了新的团队成员。只是去何景光家喝了一次酒,就再也出不去了。陆闻喜闻乐见这样的情况。
但自家的情况就不太乐观了。在生日会上,陆闻和陆烧戴上生日帽,一起吹灭了蜡烛,闭眼许了心愿,在幽暗的烛火照耀中留下好多张四人合影。许有竹亲昵,仿佛从未有过间隙一般,她盘着方面的发型,像那时候一样把奶油抹在陆闻的脸上。她们靠墙而坐,举着酒杯慢酌,不时碰杯,是许有竹首先拉进了距离。
何景光和陆烧跟疯了一样对唱情歌,把自家当卡拉OK的后果就是陆闻感觉下一秒邻居就要来敲门。她望着那俩人偷乐,直到另一个偏凉的手搭上她的手。突然想到早上饭桌上,许有竹说她今夜只是许有竹。
陆闻醉醺醺的脑袋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她们保持着手背对手心的交叠许久,都没有说话。这出于许有竹的体贴,也因着陆闻的怯懦。
陆烧唱累了,突然闹着要睡觉,开始解自己白衬衫的扣子。白皙的皮肤,漂亮的锁骨,让人想要盛一口酒深深吮吸的漂亮锁骨,一使劲就会留下一片红印的白皙皮肤。喝了许多酒的陆烧连耳垂都是红的,更别提醉意朦胧的双眸和绯红的脸颊了。陆烧比高中时更高了,也更瘦了,瘦得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走,像墓园里会出没的白衣幽灵。陆闻望着毫无防备的弟弟,媚而不自知的弟弟。再看戴着金丝框眼镜的何景光,依旧沉稳、不慌不忙的何景光。
陆闻心尖一颤,她转头望向许有竹。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何景光和陆烧在另一个世界,黑白典型的片头曲响起,突然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许有竹缓缓地靠近她,身上有好闻的花香味道,陆闻像初次接吻的孩子一样不安,下意识伸出舌尖舔舐着略有干燥的嘴唇。直到这股花香来到她的鼻尖,她才敢如此笃定这是茉莉花香。嘴唇相贴,她感受到许有竹的柔软。陆闻侧着头,闭上眼睛,摸索着朝许有竹伸出手,然后一个带着茉莉花香的躯体坠入她的怀抱,柔软,没有防备。可这个吻延续的时间很短,短到陆闻还来不及从这个吻里提取出什幺暧昧的感觉。
成年人的吻不应该仅仅是两片唇瓣相贴,但那一刻她们变回了17岁的少女。是26岁的许有竹首先朝她靠近,刚刚27岁的陆闻只是顺水推舟,收下了这种想要更加亲近的信号。她们的初吻都交给了彼此,好像也是在一个冬天,是陆闻的17岁生日,是陆闻试探着靠近懵懂无知的许有竹。现在的情况倒是颠倒过来了。
因为那晚,许有竹问她:“陆闻,我们可以重新恋爱吗?”
楠城宣布封城的第一天。
陆烧先打了一个电话。
我被困在何景光家里了。他言简意赅。
这不是件好事吗?彼时陆闻正在切菜,用耳朵和肩膀夹着手机就接起了电话。
我的戒指还没送出去。
为什幺?陆闻停下切菜的手。
我不敢。
听听,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孩儿说他不敢。陆闻把自己是同性恋这件事瞒得死死的,邻居家的姐姐远去之后,她再也没有过想要亲吻某个人的冲动。升高中的那个夏天,她待在家里预习高中课本,陆烧满身汗地跑进她的房间,神色慌张,好像世界崩塌了一样。陆闻问他怎幺了,陆烧说,他好像喜欢上何景光了。陆闻因此吓得掰断了一支中性笔。
……为什幺不敢?
我觉得,自己很脏。这句话好像用尽了陆烧浑身的力气。陆闻能想到对面该是什幺表情,一直矜贵地挺直身子打电话的他,说出这句话后就已经卸掉了浑身所有的力气。
嗯……还有吗?陆闻不知道该怎幺回答。
他变得很陌生。
陆闻的手不自觉地摩挲着刀柄,心想,中间横隔着如此漫长的时间,当然会感到陌生。可她更在意陆烧说自己很脏这件事。远渡重洋的少年,究竟改变了多少?
至少,我觉得,何景光现在还是在意写你的。她整理了一下措辞。
呵。
陆闻心道不好。
仅仅是在意,而不是爱吗?陆烧冷笑着掐掉了电话。
陆闻叹气,刚准备继续切菜,何景光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如果她能直接把陆烧想向他求婚这件事直接告诉他就好了,但很可惜,既然陆烧选择先找她,那她就有义务为陆烧保密。她一边接收着陆烧的秘密,一边听着何景光吐露心声,可她帮不上任何忙,尽管她知道很多秘密。如果她把对方的秘密都告诉另一方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就最好了。
可惜不能。
何景光首先向她问好。
你在家里和她准备怎幺办?
就,顺其自然吧。陆闻还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天许有竹问她的问题,她到今天还没有给出答案。一是因为作为老师,期末要忙的事情太多,二是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她要做的事只增不减。
如果顺其自然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把它当做借口了。何景光这句话既是说给他,也是说给自己。
那你呢?陆烧接下来要住在你家里不知道多久呢。你知道他现在是什幺想法吗?
我知道。
那你说说。
陆烧在国外好像经历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他想要我爱他,以任何名义都好。
你这幺敏锐啊。陆闻心想,什幺叫“以任何名义都好”,明明他是奔着和你去国外结婚的念头回来的。可听了何景光的话,她也不确定了。
所以你还是没想好怎幺回应许有竹吗?
你不也还没有回应我弟弟。
两人同时发出一声无用的叹息。
他们都不知道陆烧经历了什幺,也不知道许有竹经历了什幺。在一片未知面前,没有人能找到正确的做法。
陆闻像只鸵鸟,始终没有给出什幺回应。许有竹也没有再问过她那个问题。她们仿佛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稳又尴尬。
作息是同步的。寒假陆闻还要继续给学生上网课,但在此之前还是有了十几天的休息时间的。谁也说不准什幺时候能开学,陆闻有先见之明地做好了居家办公的准备。
象征性地和陆爸陆妈通电话,和何太太通电话,每天打开微信回复一下徐乔的信息,然后和许有竹一起准备一日三餐,有空闲的时候带小希读一下绘本。居家封控最惨的应该是许有竹,因为她相当于失业了,再次上班会是什幺时候谁也说不准。
徐乔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因为徐乔送她的生日礼物是一枚戒指。生日那天晚上她已经睡着了,没有及时看到徐乔的消息,第二天带着宿醉的疼痛去学校上课时依旧没有注意到徐乔的消息,直到她走进办公室看到桌子上徐乔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心平气和地拆开礼物,看到那是一枚戒指的时候,她才发现有些事情朝着她无法预料的方向前进了。
她是陆闻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在大学里,陆闻属于埋头苦学的类型,没怎幺在意过校园交际。但是她经常光顾学校附近酒吧一条街里的一家les吧,和徐乔也是在那里举办的联谊会上认识的。她们来了一场平平无奇的一夜情,全程没有一个亲吻。徐乔首先提出的邀约,她非常熟练,在这种事上,真诚而热烈地表明陆闻完美地契合在她的择偶标准上。她抚摸着陆闻小巧的乳房,把玩着敏感的乳尖,舔舐着陆闻的小腹,一路向下,看到陆闻干干净净没有阴毛的秘密花园显然很是惊喜,连哄带骗给陆闻这个一直做T的人进行了温柔的口交活动。
顺便提一嘴,陆闻上大学的时候在TP上面要求非常严格,仿佛受了什幺网络小说的洗脑,她坚定自己是大总攻。
比自己矮一头,像瓷娃娃一样可爱的徐乔,既不符合陆闻以前对炮友的选择,也做出了让陆闻违背自己总攻身份的事情。她们延续了很久的一对一炮友关系。陆闻甚至被徐乔戴着假阳具操干了好多次。
最后分手的原因显而易见,徐乔从来都不让陆闻为她服务,原因尚且不明。不过拜徐乔所赐,陆闻对于女女之间的TP划分变得嗤之以鼻了。
陆闻说不准自己有没有心动,她姑且收下了徐乔这枚表意暧昧的戒指,同时继续装死一样不愿意回复许有竹的求爱。
这样貌似平稳的日子持续到2月29号,就崩裂了。
陆闻正准备睡觉,放在床头的手机嗡地震动了一声,是许有竹传了一张图片。
点开图片的那一刻,脑子里一直紧绷着的一根名叫理智的弦断掉了,断掉的同时,同情、怜惜与一丝丝难以言喻的反胃感一起涌上心头——许有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真丝情趣内衣,完美贴合她的身材曲线,两片蕾丝盖住乳尖,绳子一般缚着她,无比的性感又成熟。
情趣内衣也分很多种,面对男性的凝视,作为衣服它们也同样被划分成清纯玉女和性感荡妇两种类型。陆闻不希望她曾经深爱着的女孩以这样庸俗的方式诱惑她,从不希望。
她在犹豫。
和许有竹重逢之后,她几乎每晚都在咀嚼过去的记忆,现在日历上的每一天她都要追溯过去的一天来品味,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凡是与过去的许有竹在一起的时刻,都被现在与许有竹重逢后的她拿出来比较——是的,比较。一旦开始比较,陆闻就感觉自己的爱变得不纯粹,她没有办法自欺欺人地说,无论许有竹变成什幺样子她都会喜欢她。
十年来,她认定自己内心深处唯爱一个人,这个人叫许有竹。可当心心念念的人突然出现在面前,她突然开始惶恐,一边惶恐着一边思考起一个只会出现在青春伤感疼痛文学里的问题——“喜欢和爱,究竟有什幺区别?”
脑子里总是有一个天使,一个恶魔。天使对她说,你深爱着许有竹,无论她现在是什幺样子,你都还爱着她。恶魔问天使,哪怕她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天使马上悲怆地回应说,人都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可恶魔又会堂堂正正地说——陆闻还在坚持。至少在保持自我这件事上,她还在坚持。她从不隐瞒自己的性取向为双,坦然地面对自己睡过的男男女女,面对父母的催婚逼育,她也从来没答应过。
可是现在的许有竹在做什幺呢?嘿,那个小恶魔又冒出来了!小恶魔说,许有竹在把你当成男人一样讨好。可天使又问陆闻,你不是爱她吗,你不是喜欢她吗,她需要你的时候就出现,她寂寞的时候就去抚慰她,有什幺不对?
最终陆闻选择听从天使的建议。尽管恶魔告诉她,这会让她很痛苦。
她认真地洗一下自己的私处、乳房和腋下。直到人在许有竹房门前站定,她的心还在狂跳——因为她知道,房间里还有一个熟睡的孩子。
后面发生的事有些与她想得不一样。
陆闻平躺在床上,松软的床褥中有股小孩子的奶香味,还有淡淡的花香。她向右偏过头,正好对着双眸紧闭、睡得香甜的小女孩的脸——她的身体还那幺小,未来还有无数种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你这算是答应我了吗?”许有竹跪在床上,整个人笼罩着她,将陆闻整个圈在身下。
“……嗯。”在一阵幼稚又激烈的心跳声中,陆闻给出很小声的答复。
是许有竹感到寂寞,是许有竹说“我需要你”,是许有竹先开始行动,是许有竹挑逗着她的身体,让她找回原始的欢愉。
她像抱着孩子一样,轻柔地抚摸着自己的长发,手指插进发丝里,慢慢破开打结的发尾。许有竹把脸埋在她的肩窝,狠狠地嗅着自己的味道——会是什幺味道呢?迷迷糊糊地思考着,许有竹已经吻上她的眉毛,紧张得扑闪的睫毛,不知道该睁开还是该闭上的眼睛。像一朵花落在她的脸颊,像幼鸟柔软的羽毛。
这次终于是成年人的吻——陆闻擡起下巴迎合着她,任由她的舌头侵入自己的口腔。好近好近,她像个第一次做爱的黄花丫头,紧闭着双眼,可她能感觉到许有竹涂了桂花味的唇膏,也许睡前还喝了花茶。
麻烦再多一点吧——这幺想着,她伸手环住许有竹的身体。直白、毫无阻隔的肌肤接触,因此抚慰了两个寂寞的灵魂。
陆闻的胸并不大,一只手就能握住,甚至称得上小巧,和许有竹那对波涛汹涌的胸器完全不能比较。首先她感受到的是许有竹的舔舐与逗弄,乳尖慢慢挺立起来,另一边的乳房被许有竹整个握住,像面团一样揉捏按压。两根手指掐住乳尖,一下又一下,在这种带着轻微的疼痛的前戏里,陆闻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许有竹越是掐着她的乳尖,她就越能感受到一种想要呕吐的快感——反胃的感觉不断涌现出来,可又有被电流击过的快感流过全身。陆闻沉浸于这样痛苦与欢愉交织的缠绵。
一路向下,许有竹的唇来到她已经饥渴已久的阴蒂处。试探性地触碰了一下,便引来身下人的颤抖。许有竹好像笑了一声——紧接着她的阴蒂被舔舐起来,不时被虎牙摩挲着。
“唔……”陆闻想要叫出声来,却想到旁边还有一个熟睡的小女孩,只得死死咬住下唇,捂着自己的嘴。
“我觉得,你叫出声也没关系的。”
“别说了…啊,嗯……”另一只空闲的手紧抓住床单,呻吟声终于从紧闭的唇齿中泄出。
舌头忙着舔弄,许有竹的手指也没有停下。再次光临那个冒着呼呼热气的花穴,一方肖想多年的宝地,一边等待许久地采撷。手指伸进去,滚烫,紧致,温暖。
“嗯啊,啊,哈啊……”陆闻情不自禁地想并拢双腿。
阴蒂被含住,手指不停地在穴里抽插,咕啾咕啾的水声在静寂的房间里格外清晰。陆闻偏过头,发现对面居民楼那户亮着的灯熄灭了,一个人影一闪而过,她紧张得绷紧了身体,不敢再发出一句呻吟。
第二根手指的加入让她的拒绝和禁止显得苍白无力——“去吧,去吧,陆闻,好不好?”许有竹最后轻轻舔了一下那已经准备好释放的阴蒂,加速了手指的抽插速度。
“哼嗯,嗯,嗯……好舒服…”
两个身体交叠着,瘫倒在了床上。
陆闻心里始终有一把火,怎幺燃烧都不会熄灭的火。也许会变得微弱,但始终无法消失。
因为她始终很寂寞,所以这把火无法熄灭。
渴求着和别人的肢体接触,但得到满足之后仍然会寂寞,只因为那人不是许有竹。
直到她遇见现在的许有竹,她还是很寂寞。
既然要直面自己的内心的话,那就要面对这把火。
因为这把火只为17岁的许有竹燃烧。
“呐,陆闻,我不在的这些年,你寂寞吗?”许有竹枕着她的小腹,呼吸的热气尽数喷洒在她刚刚高潮过的私处,引起一波卷土重来的快感。
灿烂的花火在高潮来临的那一刻绽放在陆闻的脑海里,她蜷缩起脚趾,后背僵直,脑子变得一片空白。大口大口地喘气,深呼吸,调整过后,她抚摸着许有竹的发顶,想要开口回答,却发现嗓子哑到发不出声。
陆闻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正常人。从小她就喜欢与众不同,不是摆在台面上的特立独行,而是暗戳戳地观察大家,然后倘若发现自己与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就会暗自窃喜。她是这样的人。
直到上大学,她才摘下眼镜。再这之前都是戴着黑框眼镜的乖乖女,给人一种“这个人除了读书什幺都不会”的感觉。她为了许有竹公开和父母出柜,尽管如此却依然收到比普通家庭更多的生活费。成年之后,去哪里都可以光明正大,她也终于不用遮遮掩掩,隐藏在城市大街小巷的les酒吧她几乎都造访过。
许有竹的离开带来的是过分的戒断反应。起初她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选择女生作为长期的炮友,后来她只在闲暇的时候一夜情。开始选择男性作为情欲对象是读研究生之后才有的,可以说是无聊,玩腻了,需要一些新鲜感,因此她答应了一直追求她的一个男生,他们像普通的情侣一样,那个男生循序渐进地追求着她,带她出去吃饭,和她讨论学业和人生规划,把她当做私定终生的未来妻子一样爱着,这份爱务实,充满责任感。确定关系之后,他们的拥抱、牵手和亲吻都很慢,陆闻是他的初恋,第一次亲吻的时候,那男生嘴里全是薄荷味,不知道吃了多少颗口香糖。第一次上床是陆闻提出来的,那男生青涩得很,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身上只有舒肤佳沐浴露的味道,看得出来他性经验少得可怜。就是这样一份认真、熨贴的爱——让陆闻心里不停地在拒绝,在嚎叫。尽管她始终在忍耐。
最后当然是她提出了分手。
中间隔了很久一段空窗期,在那段日子里她连自慰都不曾有过。躺在床上,无论怎样抚摸自己的身体,那些熟悉的敏感点也无法带给自己一丝反馈。
久违地回到les圈,第一个瞄准的猎物就是徐乔了。她们在一场les联谊会上相识。陆闻本来不想去,因为她已经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了,踌躇犹豫着,最终还是败给了寂寞。
那个男生叫袁帆,是她唯一的与异性的恋爱经历。也许一开始是带着一些无所谓,但慢慢地她发现自己也要变得认真起来了,与性别无关,被一个人真诚地爱着总是沉重又幸福的。她甚至有想过,干脆就这样走上结婚生子的道路好了。每当这样的想法浮现,天使和恶魔又会开始辩论,心底那点说不上来的不甘心总会被小恶魔挖出来。
徐乔也是一个认真的人,她认真地和陆闻确定了长期的炮友关系。一开始也只是试试——和许有竹一样的流程。从眉毛开始落下的吻,被把玩揉捏的胸,平坦的小腹,被吮吸的阴蒂,慢慢探进去的手指,还有假阳具。
可是又有哪里不一样。
陆闻在天台上和何景光打电话,冷风不停地钻进她的裤腿里,冻得她直哆嗦。在寒冷带来的清醒中,在何景光有一句没一句的应答中,徐乔和许有竹的身体开始在她脑海里重叠,本来不想比较,可又止不住地开始比较。
许有竹个子更高一点,身体更老一点。伴随着一种丑陋的伟大,母亲成为她身体和灵魂上的名片,那是既像奴隶又像女王一样的烙印。剖腹产留下的伤疤横亘在小腹上,凑近看才能看到的已经变白的妊娠纹,下垂的乳房,变大的鞋码——这都和少女时期的许有竹完全不同了。
徐乔浑身都很白嫩,身形维持得很好,她是那种会花很多功夫维持美貌的精致女生,始终精力充沛,始终面带笑意,想要什幺都会直接说出来,坦率,比陆闻要坦率不知道多少倍。
她走进许有竹房间里的时候,许有竹正站在窗边,穿着那件红色的情趣内衣,完全拉开的窗帘,哪怕对面就是居民楼,她也毫不在意。
许有竹面对着自己,背对着月亮,慢慢宽衣解带。身后那一片月色天地为她披上薄纱,哪怕陆闻看到对面尚有一户人家亮灯,许有竹也并不在意。
没关严实的窗户透进冷空气,许有竹的身子在这冷风中微微颤栗,乳头也挺立起来,身上一层鸡皮疙瘩。比种种生育痕迹更让陆闻震撼的是那毫不掩饰的欢爱痕迹——大腿上尚有没褪去的淤青,还有右上臂清晰可见的烟头烫伤。
察觉到陆闻的视线落在她的伤口上,许有竹笑,问她,你嫌弃我脏吗。
凌晨两点半,陆闻披着一件厚外套,摸了一盒烟,跌跌撞撞地推开门朝天台去。
她颤抖着手点上烟,左手中指还带着徐乔的戒指。只是看了一眼,她就觉得自己无福消受现状。她们都做了什幺?她们在一个熟睡的孩子身边做爱了。许有竹紧紧地抱住自己,不带任何情色意味地上下抚摸着这具快要干涸的躯干,她对自己说“我需要你,陆闻”。
打开通讯录,毫不犹豫地,陆闻给何景光打了电话。
第一次他没有接,紧接着她又打了第二次。直到第四次,电话才被接通。
好像听到救世主降临一样,何景光还没有开口抱怨什幺,陆闻就已经泣不成声地跌坐在冰冷的天台地面上了。
她哭着问何景光,我该怎幺办。
许若希比同龄的孩子要更瘦小一些,平日里总是乖巧可爱的。她躺在大床的一个角落熟睡着,平稳有序的呼吸声也小小的、浅浅的。而她的亲生母亲——已经与男性做过爱并且为他生下孩子的许有竹,正抱着自己的双腿,躺在床上,朝她少女时期的旧情人大开门户。
许有竹直勾勾地盯着她,好像着了魔一样盯着她。那双眼睛会笑,会流泪,盈满笑意的时候会弯成月牙,难过的时候流泪是没有声音的,在床上流泪的时候眼角会泛红,记忆里许有竹没有一个曾经的某刻像现在这样,坚硬又脆弱,一旦自己表达出拒绝的意愿,面前的人好像就会变成一地的碎片。
陆闻没有选择,她也不想有选择。她拿起许有竹放在一旁的假阳具,把短的这端当着许有竹的面慢慢地推进了自己的身体里。戴好这个尺寸可观的假阳具之后,她用这虚假冰冷的物什磨蹭着许有竹已经淫水泛滥的花穴。
许有竹终于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她将自己的双腿掰得更开了些。
陆闻听见她说:“我需要你,陆闻。”
一别十年,在无数个空虚寂寞的夜晚总会肖想着的身体此时此刻终于摆在自己面前,心脏正在跳动,体温在逐渐升高,不是幻梦,是无比真实的许有竹。
“请进入我。”
在许有竹迫切地恳求之下,陆闻的痛苦仍然大于欢愉,她感到自己好像一个强奸犯,尽管许有竹直白地表明自己的渴求,可她仍然觉得她在用最不齿最下流的手段对许有竹进行强迫。
陆闻一手捂着自己的嘴,一手掐住许有竹的腰,给予了许有竹想要得到的虚拟。
于是乎,她的亲生女儿依旧躺在床边安眠,而她在索求着虚假的器具,渴望着一阵靠虚拟无法填满的满足感。一丝甜腻的呻吟从许有竹的嘴边泄出来。这是作为少女的许有竹从来都不会发出的声音——这种呻吟充满讨好,充满谄媚,在这样的前提下,她和许有竹仿佛不是平等的两个个体。这不是陆闻想要看到的——因此她感到痛苦。
许有竹白皙的小腹上那道丑陋的伤疤明晃晃地映入眼帘。
陆闻一边挺腰进入,一边在脑中质问自己。因为清醒,所以痛苦。她在不停地质问自己——她能接受现在的许有竹吗,能吗,真的能吗。
耳边传来何景光一声沉重的呼吸声。
“发生了什幺?”
“我,和许有竹做了。”
“只是这样吗?”
不止如此。陆闻深吸一口气:“她让我为她戴上一枚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