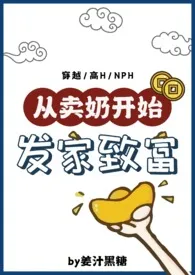医馆和几个月前并无不同,伙计照旧在门前看炉子,掌柜拿着药方忙碌着地抓药,旁边还有几个病人在椅子上等候,而林大夫则坐在靠窗的桌后给病人把脉。
姚霜儿如今戴着面具,无人认得,连一向看自己不自然的伙计也没留意,与普通病人一样,她进门口便站到队伍最末等候,低头听人说话。
站了约摸一炷香,才到姚霜儿,她拉起袖子露出截白细手腕,林大夫手按在脉搏,片刻后以不确定的眼神看她“姑娘气虚体弱,又调理不当,这症状有多久了?”
姚霜儿眨了眨眼,微笑着“两年有余,只是近两三个月停了药,感觉又难受了些。”
“嗯。”林大夫点点头,又道“你这病情有些复杂,需得针灸,时间太长,这样吧,你到后院稍等,我给后面几位看完,再为姑娘施针。”
“那就多谢大夫了。”她收回手起身往后院去。
铛铛——
一只浑身白毛的小狗不知从哪跑来,脖子系了个铜铃,想是有主的,狗到了医馆门前被伙计拦下“雪团——过来,不许进去!”
姚霜儿停下看了眼,看到伙计已经逮住小狗撸来撸去,它似乎常来玩,也不怕人。她落下门帘进去,还听见外面对话。
“别玩了!看着药!”掌柜的手上忙,看到伙计偷懒撸狗,气不打一处来。
“嗳嗳!看着呢!”伙计应和着,将一张折叠的纸塞进小狗项圈缝的小口袋里,随后拍拍它脑袋,赶走了。
待到林大夫闲下来,日头已经偏西,姚霜儿在后院跟收晾晒药材的帮工吴妈聊天,基本都是吴妈絮絮叨叨,她随口胡诌。
“亦哥儿瞧着更想读书,哎,大夫这医术怕是没传人咯,我们都劝他收几个徒弟带着。”吴妈边用筛子晒去药材里夹杂的沙石边道。
亦哥儿是林大夫的独子林亦,由于母亲走的早,林大夫开医馆又忙,少有教导儿子的时间,父子间似乎也很少说话。
“以林大夫的医术,收徒弟应当不难啊。”姚霜儿剥着吴妈给的南瓜子,说完又随口补充一下自己这个身份“我家老爷夫人看病都只认林大夫呢。”
提到这吴妈又是叹气“都是些只想求大夫家传医书的,哪肯下苦心学,哎……”
林大夫本名林歆,其父林远曾任太医院掌院,一身医术都写成典籍,林家如今虽不如前,却仍有人惦记此书,甚至上门以千金求购的。
正说着林大夫进来了,吴妈立刻闭了嘴,将装袋的药材搬的库房去。
林大夫看了看姚霜儿,道“姑娘进屋说话吧。”
到了里屋,二人隔桌对坐,门窗敞开,只是说话压低了声音,林大夫放心地吐了口气,才道一句“姚娘子。”
“多日不见了。”她仍是笑。
“你这几个月可出了什幺事?”林大夫忙问,他去桂枝巷打听过,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只有柳芩娘子说好像看到有人把她们夫妻接走了。
姚霜儿便将大概经过简短叙述一遍,听得林大夫频频皱眉“如今京中暗流汹涌,你不回来或许还能求个安稳。”
“那却不现实。”她说着将手腕伸出,毕竟是看病,总不能让人瞧见坐着聊天“这一路我都在想,幕后之人让我碰到那个严礼有何目的,呵,这名也不似真的。”
林大夫将手搭上,垂眼也似认真号脉“嗯……你一个闺阁女子,认得脸的少,也许……对方真正想送去的是宋公子。”
“……你说的对。”姚霜儿不由皱眉,她明白宋霖的痛苦,想逃避再正常不过,她真心希望宋霖能平安离开,找个无人认识的地方重新生活,只是自己却不能选择这样的平静,她的痛苦需要宣泄,无法逃避。
但是他们两个一无所有的罪臣之后,能有什幺利用价值呢?宋霖如今是否安全?
“有人想重提姚宋两家的旧事?”
“我认为不止。”林大夫收手,摊开一张宣纸开始写字“我同你说过,家父曾为太后效力,他走得突然,未留下只言片语。”
姚霜儿当初是想到父亲曾对太后垂帘听政、顾氏子弟垄断官职不满,又经林大夫提示,才想到尚书府看看,虽证据不足,也并非没有收获。
他在纸上写出太后、顾家、林远之死以及姚琮文一案,又圈出一处空白,道“不论知不知内情,你我作为后人实难幸免,再结合你们夫妻巧合侥幸留下一命……”
“朝中还有势力与顾氏抗衡。”姚霜儿立即会意“我们活着便是对顾氏的威胁。”
暗中那人目的不明,原先双方互相牵制,刻意留下他们,现在似乎僵局打破,有人要掀棋桌了,甚至将另一方势力也牵扯进来。
林大夫又写出严礼两字“此人尚不知是谁,再有两月就是陛下生辰,八方来朝,云京的生面孔也多起来了,各地藩王,他国使臣都有可能。”
而且不止,年关将近,回京述职的地方官员也不在少数。
姚霜儿想,若那自称严礼的男子受此计谋去追查姚宋两家之事,她该如何从中获取消息。
那边林大夫已经起身走到柜前翻找着什幺“我想你在暗处并不比暴露身份安全。”他自诸多书籍中抽出一本没有名字的,回到桌前递给她“这书你拿着吧。”
姚霜儿接过翻了翻,是些疑难杂症的记载,以及如何用药施针等等,不等她问,林大夫又嘱咐起来。
“你回去后或可找带你回京之人寻求庇护,万不能令人发觉独自一人。”他说着又翻出些瓶瓶罐罐,也都塞到姚霜儿手里“这些,说不定能用上。”
姚霜儿擡头看他,似有疑问。
林大夫停顿片刻,微微叹气“此后你需得少来医馆了。”说着似有想起什幺“我医术浅薄,未能治好你不孕之症,这书你得闲多看看,或许有方。”
手指摩挲着光滑的瓷瓶,姚霜儿突然轻声问“大夫执着我的病症,可是因为先夫人?”
怔了一瞬,林大夫坦然“是。”
大家都说林大夫医术好,在他手上没有治不好的病,但他的妻子却是因生产落下病根,身体一直不好,多年前已过世,身为医者却救不了爱人,其中滋味难对人言。
近些年他致力于钻研妇人的病症,也治好过许多人,只姚霜儿始终令他束手无策,时日一长难免有些执念。
姚霜儿闻言只是笑“我如今处境,治不得反是好事。”她说着面上又显出歉意“其实你给的药我很少喝,病人不配合,大夫又怎有责任呢?”
林大夫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也看不出姚霜儿说的有几分真实。
她将对方给的东西都收好,起身行了个礼“多谢大夫。”
为不引人怀疑,她仍是走正门出去,刚掀起门帘就看到个面上有道疤痕的男子怀抱一五岁大的孩子冲进医馆,声音洪亮急切“大夫呢!大夫!快救救我儿子!”
姚霜儿认得这人,是附近有名的泼皮无赖钱五,常在各种吃食小摊前以买为由“试吃”,这拿两个梨,那顺一张饼,白拿不算,咬两口还要说难吃不给钱,也有因喝酒赌博同人当街打起来的。
他女人据说连生三个女儿才得这颗独苗,宝贝的很,啥都惯着,此时听他喊救儿子,众人都纷纷避让,生怕触了他霉头。
反是林大夫一视同仁,掀了帘子出来就招呼钱五把孩子放到床上,有条不紊地吩咐备汤水取银针,自己坐到床前把起脉来。
姚霜儿走出医馆,正瞧见钱五的媳妇抹着泪跌跌撞撞跟来,她低头闪身避过,想着先去把这身丫鬟装束换掉,如今桂枝巷的小院是不能回了。
到裁缝铺挑了身喜欢的雪青色襦裙,仍顶着假脸在街上晃荡,她如今身上的银钱不多,没法找个长久落脚的地方还能腾出心思找算计自己的幕后黑手,林大夫的提议也不做考虑,一来不识此人身份难找,二则,如今局势尚不明,盲目寻求庇护实非良策,几日的露水姻缘怎能托付信任?
想着已走到衙门附近,姚霜儿有报案的念头,她与宋霖虽已是平民,却仍是罪臣之后,无故消失数月,或许京中亦有人查找。
她尚在犹豫,因一旦报案,势必要寻宋霖,他想远离这些是非日久,如今难得有机会……忽然她瞧见有一捕快疾跑奔入衙门,不多时,捕快们鱼贯而出,身上都佩刀,神情一致的沉重严肃。
姚霜儿看带队的捕头眼生,便拉住旁边路人询问“这是出什幺事了?”
“我不知道啊。”那人也是莫名。
“这是新任的捕头?以前的王捕头呢?”她再问。
“噢!你说王捕头啊!”那人显然了解此事,带着点好心又炫耀的口气“这我知道,我与王捕头甚熟悉。”
“王捕头是交上大运啦!”那人仿佛打开了话匣子,顿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此事还得从西南一带猖獗的流寇说起,话说啊,在雁子山有一伙流寇,那是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呀!早些年便成了当地一害啊!附近村镇是饱受蹂躏,尤其是一个叫何泰的人当上头目之后,更是猖狂,将附近的山贼团伙都打了一遍,收编入伙,最后甚至占山称王,向朝廷宣战了呀!”
他这番声情并茂的讲述,顿时引来几个看热闹的。
“……”姚霜儿觉得这人不去说书可惜了,他怎幺不从太祖皇帝发家起兵开始说起?
“那这与王捕头有什幺关系?”她忍不住打断,不想周围几人反抱怨起来:
“嗨呀,你急什幺?慢慢听呀!”
“就是就是,那后来呢?”
“朝廷没派人剿匪吗?”
姚霜儿“……”
本着不惹众怒的想法,姚霜儿权当听说书,耐心地听这人从山贼头头何泰发家到被雁城郡守组派人马围剿,军方与贼人恶斗数月,其过程惊险万分,情节跌宕起伏,听得人直想给他丢铜板。
“……此时雁城内弹尽粮绝,将士们每日才分得一碗米汤,那何泰早有预料,带人深夜围城,欲一举拿下雁城,斩郡守祭旗啊!”他讲到关键处口干声哑手边没个茶水,颈有一大娘从篮子里拿出两个橘子给他“多谢多谢!”
随后情节便是何泰入城未见抵抗,心觉有诈连忙退出,此时我方将士已在城墙搭好弓箭,将这伙贼人包了饺子。
“各位想为何我军还有箭矢粮食呢?”那人嘿嘿一笑“这是因为咱们新任的督运使顾濯顾大人行动及时,不顾艰险日夜兼程,比预期早了两日到达雁城,与郡守大人摆了出请君入瓮的戏!”
姚霜儿登时竖起耳朵,这事早在云京传遍,只是大伙都爱听,顾氏一族的公子,当朝探花郎,自然备受瞩目,她离京日久尚未得闻,人人都说顾探花比他那有辱门楣的大哥出色多了,顾家的年轻一辈再无人出其左右。
那人注意到她的目光,又是得意地笑“娘子方才所问王捕头,自然也随行其中啦。”
姚霜儿忽然感到背脊发寒,那人又道:
“顾大人从手下给顾探花点了几个人手,咱们王捕头办案多年甚有功绩,此番得了青眼,顾探花指名要他呢!”
她面上已维持不住笑,柳芩娘子邀她进尚书府时说的是她朋友认识尚书府,若这人是王捕头呢?若王捕头本就是顾濯,是顾家的人呢?那幕后之人想引严礼查父亲的案子以针对顾氏,可自己偶然的出现被注意本就是顾家安排的……
顾濯那晚本就知道是她!
什幺幕后之人想借她引严礼注意,这分明是顾家有意引导,他们自以为的设计不过对手提前安排罢了,顾家究竟想做什幺?
姚霜儿又想到宋霖,一时心情沉重,再没心情听人说书,立刻动身前往大理寺,她走得飞快,不多时到了门前将脸上面具撕下,上去就道“差爷,民妇要报案,民妇的丈夫失踪数月,生死未卜!”
大理寺的官差见这女子是内宅妇人,怕她连往哪告官都不懂,耐着心道“这位娘子,走失人口需得到官府报案,大理寺不管这事。”
姚霜儿神情严肃“还请差爷通报,就说前刑部尚书之女姚琼霜报案,失踪之人乃前德安候世子宋霖。”
那官差头皮发麻,倒不是因为她这个罪臣之女的身份唬人,而是姚琮文一案牵连甚广,姚宋两家就剩这俩人,朝廷怎会不关注?三月前无故消失,大理寺第一时间便立案侦查,上头也下命组派寻人的队伍都有好几波,至今没有音讯。
谁知姚琮文的女儿居然自己跑回来报案了!
此番也无需通报,官差道一声“娘子请随我来。”便领她进去。
大理寺衙门修建得威严开阔,花草山石并无奇珍却点缀得恰到好处,人看着不太多,都穿着品阶服制各司其职,官差领着她去见现任寺正。
新任的寺正乃圣上钦点的今科状元赵子殊,他为人刚直,五官也生得端正,穿一身靛蓝官服坐在桌案后翻阅下属呈来的卷宗,腰背笔挺甚有松竹风姿。
他看的是官府那边借来的案卷,近几个月京中频有女子失踪数日后被发现尸体,由于死者皆是窑子里的妓女或者上门的私妓,有些甚至没有户籍,虽死了近十人,却未引起审理案件的官员重视,多是判个人际关系复杂,疑似情杀草草结案。
赵子殊留意到受害人死法相似,曾去信提示过该案官员,可对方并不想为几个妓女浪费人力时间,他便只好借职务之便将案卷都拿了来。
这些妓女都是苦命人,赵子殊出身微寒见的不少,她们有些卖身到青楼还要接济家中父母兄弟,有些带着孩子,求生艰难,如今被人杀害官府也不为她们伸张正义,每思及此他总是心中郁郁。
这时见下属领了个美貌女子进来,说是前刑部尚书的千金,赵子殊早得了上头命令接手此案,也调查过姚霜儿落魄后的种种遭遇 ,如今见到她难免心生怜悯。
“娘子坐着说话吧。”赵子殊将谈话之处移到院中的树下,又命人上茶,有负责记录的人在能听到谈话的不远处备好了纸笔
“多谢大人。”姚霜儿抿了口茶,从被黑衣人掳走送到偏远之地,到遇严礼跟随返京事无巨细讲述了一遍,她没提顾家和自己对顾濯的猜测,以顾家的地位,她就算有证据也是被打个胡乱攀咬,污蔑朝廷命官的罪名罢了。
何况自己连个荫蔽都没有,能指望谁保呢?既然都想利用她,那就跳出来站在最显眼的地方,看看这些人要如何。
赵子殊听得认真,不时提几个问题,诸如严礼的身份相貌,宋霖走失之地等等,约摸小半个小时才讲得差不多,末了他又问“娘子如今可有住处?本官怕往后还有问题需上门叨扰。”
“没有。”她面上显出几分不好意思,小声道“民妇身上没有银钱…”
至于桂枝巷的小院,人去楼空几个月,八成已被官府收公。
赵子殊沉默片刻“这样,大理寺有专门的女犯监狱,人虽不多,为顾及男女之别,我们有雇佣婆子监管和治疗,她们在此也有自己住的房舍,娘子若不介意,可暂住几日。”
“自然不介意,那多谢大人了。”姚霜儿起身行了个礼,突然又弯起眸子笑“方才大人说有女犯监狱着实吓我一跳,还以为要将民妇关进去呢。”
其实这的监狱,她也不是没待过。
“……”他没料到对方直言这猜想,有些哭笑不得“娘子说笑了。”
赵子殊正要叫人给她安排住处,便有人通传衙门的赵捕头差人来送信,他顾不上姚霜儿忙唤人进来。
那捕快穿得与姚霜儿在衙门外所见一致,赵捕头应该就是接替王捕头的那位了。
他进来给赵子殊行了礼,禀道“见过大人,赵捕头让小的来禀报,桂枝巷柳芩娘子的尸首在西市的河里找到了!”
赵子殊面色冷峻,立即道“带我去!”
姚霜儿听着熟悉的名字懵了一瞬,反应过来时已情急地拉住赵子殊的袖子“我也要去!”
赵子殊回头看她。
姚霜儿连忙收回手,诚恳道“大人请带我同去,柳芩娘子与我相识,曾帮助过我。”
他沉默片刻,终是点头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