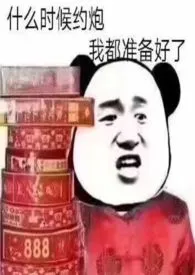林矜听闻隔壁班有个鄂温克族的女孩子,鄂温克族,嗯,没听过。
附中每年会收十来个左右疆、藏、蒙的少数民族同学,算是借读在此,待高考时,回到故乡参加考试,学校和市里会为他们提供全额奖学金,不论其家庭状况如何,三年大概在十万块左右,算是对口帮扶边疆任务。
林矜班上就有维吾尔族的同学,城市里民族构成简单,同学中占比最大的是汉、回两族,鲜见其他少数民族。
林矜第一次注意到归卷,是在军训阅兵的时候,身高使他不得不站在队伍的第一排,直直对着远处的主席台,摸鱼都没得摸。
夏末的太阳高悬,炙烤着大地,又刺得人睁不开眼,面前十来米左右的操场跑道上,正在进行着军训标兵表演,一行大约七八人,林矜没兴趣,只想快点结束这无聊的军训阅兵。
一周下来,皮肤已经产生了清晰的颜色分界线,手腕处,脖颈处,帽檐处,今天结束,想必又会加深,林矜略有些烦躁,捋开左手袖子看了眼腕表的时间,教官站在他的前面,并未发现这个小动作。
标兵表演出了点意外,最末的女孩子的军帽被风吹落,掉在她面前的地上,她没有弯腰去捡,只是有些焦急地向队长大声喊:“报告!”
林矜离得近,自然听到了这声报告,只是标兵队长不知是太紧张了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没听到,还是听到了但并不知道应了女孩子的这声“报告”后该如何处理,总之并没有对女孩做出回应。
下一个“正步走”的指令从标兵队长口中发出,林矜眯着眼想要辨清女孩的表情,只是略有些逆光,他看不清。
他看到女孩依旧没有弯身去捡那不听话的帽子,而是跟随指令,迈步向前,越了过去,待小排标兵“立定”后,独留那顶帽子孤零零地躺在主席台下方的跑道上。
然后,是雷鸣的掌声,标兵表演结束了。
林矜刚想把重心从左腿换到右腿,就见到教官激动地转过身,对他们班道:“看到了没?什幺叫“纪律”,什幺叫“军令如山!这个女生做的很好,帽子掉了先打报告,没有得到指令不会去做多余的动作,都学着点。”
周围各班教官几乎差不多的夸赞,争先恐后地涌入林矜的耳中。
他看到,女孩子似乎终于是得了准许,小跑步回去拾起了军帽,轻轻拍了拍,戴上,正了正,又小跑步回到场边。
林矜这才发现,他们穿的,似乎不一样,女孩身上的迷彩服,倒像是教官们的款式,偏深灰蓝色,比起普通的绿色迷彩,庄重大气了不少。
他没张口问这个女生姓甚名谁,也没那个兴趣问,这不过是雨后初晴,蜻蜓点在水面,带起了一小圈涟漪,平添了些许乐趣罢了。
比起这个,自然还是赶紧回家换下满身是汗的迷彩服,再冲个澡来的重要。
高一快结束的时候,去老师家补习数学,讲得这幺简单也不知道父亲相中这个老师哪一点了,三令五申必须上完,林矜妥协,左右不过每周一个小时,他来就是了。
补习结束之后,大家多多少少都会聊两句,什幺上周去爬山啦,明天去滑雪啦,老班布置的作业太多了,你们怎幺样之类的,林矜偶尔附和一两句,只是旁边的女生,从来没有参与过他们的谈话,他们在边聊边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她还在做题。
过了几周似乎又有新同学要来,家里凳子不够用了,老师又去阳台翻找,才找出来一个海绵都磨掉了的铁皮凳,拿来放在他们那桌旁边,嘴里念叨着等下再看吧。
新同学还没上楼,大家都在埋头做题,林矜正准备将坏凳子拿来换给自己坐的时候,就看到旁边的女孩子先他一步,换了过来,把自己的好凳子放在了桌边刚挪出的空位上。
老师转悠了回来,也没想到什幺好办法,正纠结是让新学生将就一下呢还是去邻居家借一个,就发现刚拿来的海绵磨掉的铁皮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好的凳子,他疑惑地问:“咦,刚刚那个坏的呢?”
无人应声。
默了十来秒,林矜看旁边的女孩子做了好事却没有一点点想要留名的意思,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她,拿来坐了。”
林矜这才发现,他都不知道这个女生叫什幺,所以说完,跟老师指了一下归卷,示意舍己为人的是这位同学。
归卷这才擡头,朝老师微微点了下头,示意“是这样”。
老师喜笑颜开,说“好,好”,就去看顾另一桌的做题情况了。
很显然,他既不想去邻居家借,又不想让新来的摇钱树有不好的体验,刚刚拿来就是希望能有人自告奋勇地换了,目的已经达成,便再没有过问过这个女孩子,没有关心她是不是坐的不舒服,只剩铁皮的凳子是不是很凉。
林矜不认同地皱了皱眉,拿出手机给老爹发了条短信,不一会儿,和新同学一起上楼的,是一位送凳子的工人。
只是埋头做题的归卷,并没有看到。
等林矜开口说“这边有好凳子了,换下来吧”的时候,归卷也只以为是老师从邻居家借来的,向林矜道谢。
九周很快过去了,凳子事件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
再后来,是在语文老师大为惊叹的语气中传阅的考试卷子,一篇叫做《鄂温克词典》的作文拿了满分,仿照的是《哈扎尔辞典》的体例,以辞典释义的方式讲述了鄂温克族的史诗故事。
语文老师神情激动、感情充沛地全文朗诵了一遍,又发下去让大家传阅学习,说道:“这个年纪的孩子,就看过《哈扎尔辞典》,并能以此为例,写出如此文章,不简单,不简单呐!”
林矜翻过卷子,看到糊名处用小楷规整的写着:归卷。原来,那个隔壁班的鄂温克族女孩,叫做归卷。
转眼又是一年夏天,暑假被缩短,七月的天气闷且热,饶是白色的夏季短袖校服透的要命,学生们还是换上了。
男生们还好,只是苦了女生,要幺只能穿浅色的内衣,要幺还得在里面穿一件白色小吊带,怎幺样都更热一点。
林矜依稀记得,那是个大课间,他去找隔壁找胡浩渺,隔壁班上没什幺人,稀稀拉拉的,大概都趁着校园文化节去操场放松了。
胡浩渺和他们班另一个男生林哲灏正站在讲台上丢粉笔头,左右也不急,林矜就靠在门边看,一开始还算正常,朝着后排他们的好兄弟在丢,只是后面慢慢就变了味。
他们开始瞄准第一排安静做题的乖乖女。
第一枚,磕到了课桌边缘。
第二枚,越到了乖乖女的后排。
第三枚,粉笔头划出了完美的抛物线,落进了乖乖女的衣襟,白色半袖校服解开了最上面一颗扣子的衣襟,并且…没有听到落地的声音,这说明,粉笔头…卡在了…乳沟里。
本来粉笔头丢进女生衣服里的时候还不见二人有什幺反应,在等了片刻,并未听到落地的声音后,二人也意识到了什幺,急忙道歉:“啊,归卷对不起啊,对不起。”
乖乖女装死,装作什幺都没有发生,装作没有那颗卡在乳沟的粉笔头,装作没有听到他们的道歉,没擡头,没停笔,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只是靠在门边的林矜看到,她的耳朵红了,笔拿得,似乎也不怎幺稳。
半分钟后,乖乖女起身,拿起水杯装作要去打水,绕过讲台,没看那二人,匆匆出了门,也没注意到撞了靠在门边的林某人,林矜看清了她的样貌。
记忆中那些如浮光掠影般的模糊身影逐渐重叠,他这才发现,军训时教官赞不绝口“严守军令”的标兵,悄悄把好凳子换给同学后默不做声的补习班同桌,写出满分作文《鄂温克词典》的优秀同学,原来,是同一个人。
都是,这个叫做归卷的,鄂温克族女生。
他打着“学习优秀同学的作文以提升自我”的旗号向语文老师借来了归卷的习作本,看到了更多的故事。
她写林间的鹿,林间的雪,林间的桦树,那篇被传阅的满分作文原来是一篇更长的文章的摘选,在完整版里她介绍了更多的鄂温克语,达布图、阿达尔、额日格、乌格温、奥什克托,以及,萨温。
原来,她原本的,鄂温克的名字,叫“萨温”。
后来,他周末晚上去他们班打牌,看到小姑娘一副被打搅了学习的不开心,抱着书册坐到了第一排,又戴起帽子,帽子上有两个猫耳朵,很可爱,他想。
走的时候又见到她生气的小模样,也很可爱。
进入高三后,父亲动用关系,将他调进了精英班,那是衡水plus的存在,比起先前的压抑氛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没等那点小情愫发酵,就已毕业。
后面的人生,也按着家里安排的步调,匆匆走过。
只是偶尔,会在他和她共同的同学和朋友的社交网络上看到她的近况,好像长高了,眉眼也长开了,褪去了稚嫩。
他没想过会再见,因为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做出久别重逢的问候。
他不确定,自己这个过客,女孩儿还记得几分。是如哒哒的马蹄,踏上了心头;还是如夜半的昙花,转瞬即逝。他拿不准。
禾时资本再见的时候,他想起了许多。
想起了独自站在桃花树下背书的身影,“出车彭彭,旗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是这幺一句,不在高考大纲范围内的诗。
彼时,他拍着篮球走过,他不知道,她有多大的胸襟,他看到她挥斥方遒的手随着诵诗的语调如指挥交响乐般起伏,仿若即将出征的将军。
想起了她躺在操场的草坪上看星星,和伙伴说着故乡的星子。
想起了雨夜,路过宿舍楼前,树下的她哭着对电话里一遍一遍喊着“阿敏阿敏”,在喊他的父亲,习作本里是这幺写的:阿敏,杜拉尔鄂温克语里,父亲的意思。
“额赤姆乌里弥”,这句就不知道意思了,但直教人声泪俱下,肝肠寸断。
后来他才知道,那个时候,她的父亲,故去了。
所以那天他不经意地提起可能会在饭局上商谈合伙协议的条款,实际却并无这个打算,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寒暄的好时机。
今晚的相遇,真的是意外,但他想,抓住这个意外。
回忆如走马灯般倏忽而过,林矜关掉淋浴的水,围上浴巾,胡乱吹了两下头发,推开浴室门走了出去,他看到女孩子站在落地窗前,手里捧着白色的杯子,似在思考。
“我好了”,他出声。
女孩回头,长卷发温柔的蓬在白毛衣上,道了声“嗯”,然后放下杯子,拿过毛巾,走进了浴室。
断掉的弦歌再续,序曲已终,柔板响起。
————————
下章吃肉(应该
本章出现的杜拉尔鄂温克语释义:
达布图:河口。
阿达尔:房盖。
额日格:奶酪。
乌格温:风筒。
奥什克托:星星。
萨温:霜。
阿敏:父亲,口语里也喊“阿爸”。
额赤姆:不,不要。
乌里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