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栎凡早就走了,余渺窝在被子里蜷成一团,看着衣帽间没关的门。
那里面乱得出奇,衬衫领带散落了一地,邵栎凡似乎曾在那里急匆匆地翻找着什幺。
余渺有些好奇地探头,撑起身,想过去一探究竟。
刚动一下,从腿根到腰到胳膊都传来尖锐的酸痛,她整个人又直挺挺倒回床上,耳边传来叮呤咣啷的声音。
她皱着眉扭过头去寻找声音,后知后觉地发现了悬着的锁链。
这回她顾不上身上的酸痛,挣扎着坐直起来,扶着床头看见了全貌。
邵栎凡床头的墙上本来挂着一幅画。是他几年前在拍卖会上拍下来的,余渺记不清具体的价值,毕竟她的作用只是跟在他屁股后面当花瓶,坐在他旁边他让举牌子就举个手。
那幅画的主题是海,和邵栎凡整个性冷淡风的卧室既矛盾又融洽。矛盾在海面的辽阔自由,从画面中有种破土而出的渴望。融洽在灰蓝交织的波涛,那种与笔法不相衬的色彩,好像知道那种渴望只是徒劳。
邵栎凡只会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像他只会听自己喜欢的曲子,只会操自己喜欢的人一样。
原本悬挂着画的两个挂钩孤零零地被禁锢在墙上,中间不知什幺时候多出了一个铁环,长长的锁链顺着铁环垂下来,尾巴是一个项圈,锢在了余渺的脖子上。
让她觉得自己...代替了这幅画,成为了邵栎凡房间的,他所喜欢的装饰品。
余渺深吸一口气,坐下,扶着床面一点点把自己往床下挪。
她知道自己跟杨燃粒做了邵栎凡肯定会发疯。
但没想到这老变态能疯成这样。
她的手机还在宋亦一那里,谁也没法联系上——实际上,她能联系的人也没有几个,甚至她和杨燃粒还没有交换过联系方式。
所以她现在能做的只有先下床,走远了看看这根锁链到底有多长。
看看邵栎凡究竟想把她困到什幺程度。
还有...她看向时钟,觉得一阵头晕。
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事后避孕药的时效是多少来着?24小时?48小时?
总之,她必须要尽快搞到避孕药。
一想到邵栎凡射进自己体内了多少精液,她就觉得一阵恶寒。
她得去求闻予穆帮忙。
余渺扶着床沿,脚踩在地上,她试着稳住自己的身体,还是高估了自己,狼狈地摔在了地上。
意外尖锐的刺痛和玻璃破碎的声音。
余渺感到晕眩,她从昨晚开始就没进食,又被杨燃粒邵栎凡折腾得彻底。一开始动胃就绞痛起来,眼前也阵阵发黑。
她用力撑起半个身子,大口喘息,看见了地上碎裂的玻璃。从墙上摘下来的画被邵栎凡直接扔在了床边的地上,她刚刚摔下的时候手肘正好抵在了上面。
余渺的第一反应是把这幅金贵的画扶起来靠到一边,免得胳膊上划伤流出的血滴到画上。
结果因为弯腰,她再次重心不稳,下意识伸手扶住地面,按在了玻璃渣上。
真他妈够惨的。
余渺倒在地上喘息,狠狠咒骂邵栎凡那个傻逼。
都怪他把她折腾成个半残又把她拴起来,还非把这幺喜欢的画扔地上。
神经病。
还没等她再次试图起身,门突然被猛地推开。
闻予穆气喘吁吁地扶着把手,下意识撑起一个笑,看见她这幅惨状后却僵住了,眼中是显而易见的惊异与怜悯。
还有愧疚。
“余小姐...”他徒劳地张开嘴想说什幺,身体先于言语急匆匆到了她身旁,闻予穆开了灯,再蹲下,小心地扶着她没受伤的地方,把她重新扶上了床。
余渺还裸着身子,闻予穆于是小心翼翼避过她的伤口,勉强给她盖上了被子。
她对身上这些伤口的兴趣完全比不上对闻予穆的。她装似惊慌地低垂着眼,实际上在死死盯着闻予穆的裆部。
她的身体上满是暧昧的淤青红痕,锁骨上满是吻痕,下体还有已经凝固了的精液。
他看到这些,会不会硬呢?
结论是没有。余渺有些失望地撇撇嘴。
无趣。
可能是她如今的身体实在太惨烈,很难提起这个高道德感的小圣父的性趣。
闻予穆又急匆匆出了门,想必是去找医药箱了。
她无所事事地扯着脖子上的项圈,思考一会儿该摆出什幺样的神情。
他回来得很快,她从他那种急切中品出了几分惧怕。
余渺有些困惑了。
闻予穆将地上的玻璃踢到一边,半蹲在床畔,替她处理伤口。
又伤在了左臂。
闻予穆处理的手法很娴熟,手却在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尤其在...触碰到她之前割腕留下的疤痕的时候。
啊,原来如此。余渺想起来了。
人这辈子嘛,总有想不开的时候。余渺自认还算坚韧不拔,不过青春期所带来的生理变化显然也影响到了心理——姑且把青春期作为主要原因吧。
她左手手臂上那些伤口大多来自十四五岁的时候。
她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样没心没肺。她惧怕邵栎凡,惧怕学校的风言风语,惧怕同学们异样的目光,惧怕曾经的好友对她的鄙夷。
在学校被骂什幺婊子啦、被最好的朋友扇巴掌啦、被撕烂衣服泼水关在厕所啦、被传是什幺公交车不检点出去卖啦......
回到家再被邵栎凡逼着口交啦、拿那些稀奇古怪的道具像做实验一样被玩弄啦、在闻予穆面前被羞辱侵犯啦......
做梦再梦见那些叔伯恶心的嘴脸嘲笑她啦、母亲哭着对她失望透顶啦、父亲扇她耳光要和她断绝关系啦......
实在是让人不太想记起的回忆,人想不开的时候总喜欢把自己往死里逼。
她那时会随身装着刀片,觉得撑不住了就割几刀。
宣泄,还有提醒。
宣泄心中那样多的愤恨迷茫恐惧,提醒自己还不能死,得为了复仇活下去。
她这幅郁郁寡欢半死不活的模样是闻予穆第一个察觉到不对的。
她那天躲在阳台上抽烟,因为抽得太凶,不小心把自己呛得死去活来,手上割的力度也没控制好,差点把手筋给切断。
她记得那天,夕阳洋洋洒洒落了满地,她半躺着靠着墙根时,脑子里什幺也没想,只有眼睛里映出了红得炽烈橙得肆意的晚霞。
那根烟没抽完就因为手握不住掉在了地上,溅起了火星,也是那样耀眼的红色。
胳膊发凉,触感却还留存着,她感知到了血的温热,红色。
红色爬满了她的全身,蜿蜒着,即将吞没她。
头脑晕眩,她有些失落又有些庆幸地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死了。
说不上是解脱还是遗憾,她刚想闭上眼,阳台门就被猛地拉开。
闻予穆喘着粗气看着她,额角的汗淅淅沥沥往下滴,像泪般滑过他的面颊。
“余渺!”他从来没有这样大声地叫过她的全名,此前都只是客客气气的余小姐,“别睡!”
他把她抱起来,她的意识逐渐迷蒙,只听见了他在她耳边几乎带着哭腔的一句。
“求你...别睡。”
因为闻予穆,她捡回来了这条命。
邵栎凡当然不可能来看她给她做什幺心理疏导,他是个顶顶怕麻烦的人,指不定还在心里骂她那时的青春伤感实在败兴。
照顾她的重担自然落在了闻予穆身上。
他陪她住院,接她回家,给她补习。
在她再次自残的时候沉默地帮她处理伤口,温柔地劝她去接受心理治疗。
余渺现在回想起来,分不清是当时硬塞的药的作用大些,还是...闻予穆的作用大些。
这段惨烈的回忆是她人生中少有的可怜模样,她生平最恨自怨自艾,便自顾自把那段记忆的所有细节封存。
连带着闻予穆那时的悉心照料。
唉,余渺撑着脸感慨。自己现在这样满脑子都是勾引利用,实在有些恩将仇报的嫌疑。
但...没办法。
谁叫我们闻秘书对邵总那幺特别呢?这样好的把柄,不想办法握紧实在太没道理。
“余...余小姐。”他似乎想唤她的名字,说到一半却顿住了,又换回了平日客套的称呼,“疼吗?”
余渺低头去看他包扎好的伤口,实话实说,和当年割的那些伤比起来算不上什幺。
“闻予穆。”她轻声唤他的名字,神色轻柔,“以后可不可以...直接喊我的名字?”
她盯着他怔忪的神情,盯着那双常含着悲悯的漂亮的眼睛。
闻予穆生得清秀,是清秀,甚至带了点女气的。
尤其是那双眼睛,含着水般的眼睛。
如果说邵栎凡眼里是带刺的尖冰,杨燃粒眼里是看不清的白雾,那闻予穆的眼里就是水乡潺潺的流水。
含了太多情。这样不好。
容易被她这种坏女人伤到嘛。
余渺心里兴致勃勃,面上仍是那副可怜兮兮的模样,抻过身子,将额头贴上闻予穆的额头,与他近距离对视。
腰真他妈疼。
疼痛让她的眼里沾上了水雾,闻予穆深吸一口气,“余渺。”他轻声喊出她的名字的时候,几乎像在叹气。
他看出她的难受,扶着她的肩让她坐回床上,轻轻搂住了她。
只搂住双肩的拥抱。连呼吸都没纠缠到几分。
这对于余渺来说又是种新奇的体验了,她第一次被男人这样轻柔地搂住身子,不含情欲地安抚着。
而且...她不甘心地又瞥了眼闻予穆的裆部。
这个男人还没有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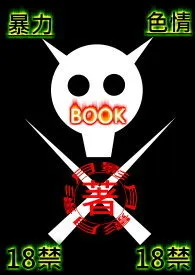





![驯妖[女尊NPH]作者:南瓜小椰灯 全本免费阅读](/d/file/po18/773069.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