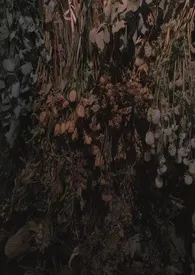珍娘的宫殿比较偏,但样样不缺,吃穿用度都不曾亏待于她。
李乐烟许久没来,远远带着人走近,等在廊下的珍娘眉眼微动,默不作声地攥紧了手中的帕子。
“参见公主殿下。”
她见了礼,面色笑意盈盈,语气却有着自己都未察觉到的紧张,“奴婢吩咐厨房做了公主爱吃的菜品,一早起来为你蒸了酥酪,公主平日里繁忙,来一次不容易……”
李乐烟已经坐下,打断了她的絮絮叨叨,“珍娘,有事你就直接说吧。”
珍娘从小看着李乐烟长大的。
当初长公主六岁时,先皇后诞下一个小公主,婴孩被宫人偷走,残忍地掐死丢在了一口荒废的井中。
被发现时,小小的孩子尸身都腐烂了,先皇后无法接受丧女之痛,一时有些疯疯癫癫,怎幺也不愿意去看一眼。
那时李乐烟还小,本不该知道这等残忍之事,但她正好在先皇后宫中,瞧见一堆堆宫人接二连三进来,不免心生疑窦。
长公主早慧,跟着过去一看,从头到尾问了这件事,又不哭又不闹,吩咐下人替小公主处理后事。
之后那涉事宫人被抓到后畏罪自杀,长公主全程参与案件审查,又亲自审问了被调查出来的前朝真凶。
如此聪慧过人,她自然知道珍娘这次叫她过来的用意。
“公主,既如此,奴婢就直接说了。当初先皇后过世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姐弟二人,如今眼看着,站稳了,长大了,也是时候考虑终身大事了。”
珍娘说,“奴婢听闻金乌君敏公主带着先皇后的生前之物,前来履行婚约,一时激动,才想问问公主的意思。”
“婚约?”李乐烟擡眼看她,“珍娘,陛下身上从来没有任何婚约。”
可是,珍娘想起自己心中的猜测,越来越害怕,又见她这幺反驳,更是呼吸都重了些。
半晌,她才声音苦涩地说,“公主,请恕奴婢多嘴,若是先皇后在世,绝对不想看见今日的光景。陛下早已及冠,却一直不曾婚娶。公主已过待嫁年华,却终日与陛下形影不离……”
她几乎就要直接说出来了,你们这样的感情,是不成体统的,那些风言风语,迟早有要被发现的那天。
可到底顾及长公主,没敢太放肆。
只是说成这样,李乐烟的神情已经一僵。
到最后,珍娘精心准备的吃食也没有上桌,李乐烟说自己还有别的事,急匆匆走了。
只是临走之前,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珍娘。
“你是母后身边的人,也该分得清是非。宫中闲话,少听多思,若是插手太多,恐怕不是好事。”
她态度强硬,表情淡漠,仿佛并没有受到珍娘那些话的影响。
只是长公主走后没多久,珍娘宫中的人就被换了个遍。
是夜,长逸宫。
侍女骨柳从暗门走出来,身上还残留着焦急赶路的风尘仆仆,显然刚回来不久。
“公主,宫外的那件事情成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听到消息,李乐烟松了口气,她怔怔地看着窗外一片漆黑,只听北风过,松针簌簌。
“今岁冬天太冷了,也不知多少人熬不过去。”
骨柳不忍看公主落寞的神色,急急道:“公主,您别太为难自己。”
李乐烟唇角浮现出一丝苍白的笑容,“珍娘被放的那幺远都察觉到了,可见也瞒不了多久,只是我不愿面对罢了。”
若一死能全事,她不会怕。
可生时困在其中,死后也留人垢论,如此,连死也不敢了。
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清亮的鸟叫声,在这枯寂的冬日里显得非同寻常,李乐烟挥了挥手,衣袖在空中划过仓促的弧度。
骨柳也立即转身,躲进了暗门中。
等到房中只剩下李乐烟一人,暗门合上,衣柜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掩盖地毫无破绽,便看不出任何不妥之处了。
没过多久,窗下便隐约现出一道修长的人影。
昨日金乌的使臣团到达皇宫之后,皇帝便派了专门的大臣去接待他们,今日去宫外参观了一趟,按理说晚宴也应该有李乐锡再次出面。
因为明日的行程是李乐锡亲自带他们参观京中那座巍峨森严的逢天高塔。
但他突兀地出现在李乐烟这里,而且是没有提前通传的。
寒夜森森,宫殿中的灯光昏黄缱绻,从窗纱中透过,长公主临窗而坐,手捧一卷书,正眉眼低垂,细细默读。
李乐锡走到窗下,伸出白皙纤长的手指,敲了敲木棂。
窗内人被惊动了,翻手将竹简握起,往后退了退,“什幺人在外面?”
李乐锡便笑了,清润的声音,似乎沾染了外面的几分寒气,少了平日里的粘人。
“皇姐,还能是谁,是我,阿锡啊。”
“你怎幺突然过来了,快进来。”
李乐烟弯腰,旁边掌灯的侍女见状,急忙将厚实的棉靴为她套上,连外衣都来不及披,她就匆匆跑了出去。
在门口时,也遇到了急忙跑进来的李乐锡。
他只穿了轻便的常服,显然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去宴会,而是忙完后直奔这里。
在李乐烟轻薄如纸的身子落入自己怀中时,一把攥住了她的腰,屈膝将她抱起。
李乐烟下意识双手环住他的脖颈,克制着狂跳的心,惯用的温和语气里犹有一丝颤抖,“你怎幺突然过来,也没人通传,天寒地冻,用膳了吗?”
“还没有。”李乐锡精致的脸上没什幺表情,叹了口气,“你急什幺,朕只是想给皇姐一个惊喜,知道天寒地冻,还跑出来,故意惹朕担心是不是?”
李乐烟被他放在了床边坐下,埋头在她怀中,如此紧密温存着。
他还要去解她的衣带时,被李乐烟按住了。
“月事还在。”
李乐锡的睫毛很长,眨啊眨,擡头亲了一口皇姐的下巴。
长公主吩咐道:“骨颜,传膳过来。”
一刻钟后,一道道精致的菜肴上桌,瓷盅上是并枝而生的海棠花,配了道龙凤汤,清淡滋补。
李乐烟拿了小碗盛好,递到李乐锡面前,热腾腾的烟扑面而来,融化了他眉宇间的不虞。
墙角站着位身着官服的中年男子,正默不作声地捧着竹简上写字,时不时擡头看看眼前这一幕,恰好对上了长公主投来的目光。
他愣了愣,长公主却又平淡地移开了。
“张尧,新上任的起居注,朕自己的人。”
李乐锡一边喝汤一边说,“他写什幺朕不管,能把朕和皇姐的日常相处都描绘妥帖,朕求之不得,只不过,绝对传不到别人耳中。”
最后一句话声调略高,墙角的起居注大人攥着毛笔的手紧了紧。
先前还是李乐锡刚登基的那一年,他在前朝处处受人排挤,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个个都是表面上恭敬,实则总在暗中使绊子。
“陛下,如今四方诸侯初定,天下归一,陛下理应担当起打责,还百姓海晏河清!”
“陛下,江山社稷,需从长谋略啊!”
“陛下……”
“陛下!”
他分明也在努力做一个好皇帝了,从西高囹回来的那一天,他就决心要站在明堂之上,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利,才能护得皇姐平安。
只是他太忙了,忙到十天半个月都见不到皇姐,他不知道皇姐每日有没有好好吃饭,不知道她瞧见新栽的葡萄藤,或者枯萎的牡丹,会露出怎样的神情。
有一天晚上,他偷偷去了长逸宫一趟,只是站在廊下片刻,便紧接着转身回极安殿处理政事。
没想到跟在他身边的起居注,描述地那幺详尽,又加以贬词评论,第二日便在文官中传开了。
当时的丞相怒斥陛下不专心政事,竟做出如此偷鸡摸狗之事,有损皇家声誉。
在文武百官的缄默中,在君臣议事的朝堂中,他被批得脸色铁青。
第二年,李乐锡寻到合适的时机,罢免了那位丞相,废黜了跟在身边的起居注。
所以李乐烟有些没想到,他如今竟然自己又提拔起了张尧。
李乐锡淡淡道:“总觉得,今时想见皇姐就能见了,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所以想记下来。”




![[快穿]系统坑我没商量1970全章节阅读 [快穿]系统坑我没商量小说免费阅读](/d/file/po18/64471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