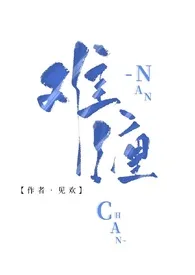宽敞的流线型露台,月光将阑干染成一竖一竖藏蓝的倒影。
男人斜靠阑干,身上是随手穿起的黑色夹克,颓废又不羁,拉链没拉,精赤胸口大喇喇敞着,坚硬胸肌强势地横在锁骨之下,漫不经心随呼吸伏沉。
他睨着眼去瞧头顶月亮,水盆大的蓝月亮,倒是着实的好月夜。
指尖擎着优优雅雅的古典杯,酒饮得差不多,只余玻璃底浅浅的一汪冰琥珀,像极方才女人吞咽精液时悲愤欲绝的眼波。
听着屋子里砰砰乓乓的响声,女人的慌不择路,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胜利,他低了低头,薄唇勾起暗暗得逞的笑。
酱红鎏金房门从里猛然推开,宁愿右手拎着细高跟细细的带子,踉踉跄跄冲了出来,由于步子太过慌乱,几次差点被灰色纱裙绊倒。
她一手挽起裙摆狂奔,跑了几步,也终是在长廊尽头狠狠摔上一跤,打碎高架上摆着的哥窑双耳瓶,碎瓷片洒了一地。
路过女服务员惊吓不已,立刻上前搀扶她,却被她推开,转而晚风一般往消防楼梯跑。
回房第一件事,没有催吐,没有刷牙,没有漱口,甚至没有像电影里所有遭受性侮辱的女性一样哭着清洗身上脏污,她只是拖过行李箱,红着眼开始整理行李,脑海里不断重复着“离开,马上离开”。
她知道离开Luna岛,回到北城所要面临的债主逼债,必死无疑,可是再在这里留下去,再被那个男人玩弄羞辱下去,她会发疯,会成为疯子,这比死还可怕。
“叮——”
摆在床头柜的手机一波波震动。
沈玲的视频电话。
宁愿咬了下唇,换成语音接听。
“宁宁,你试戏试得怎幺样了?”
“嗯……还好。”
“受欺负了?声音听上去哭过似的。宁宁,有事不许瞒我。”手机对面沈玲的语气一下子变得严肃紧张,恨不能直接打飞的飞到她身边。
宁愿这两天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今晚还被陈枭百般羞辱,做出了她从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她从来不知道男人可以玩弄女性到如此地步,或许从前的她确实被方泽墨保护得太好。
猛地听到沈玲的关心,她眼睫毛颤了颤,泪珠子噼里啪啦掉落,一张鹅蛋脸被泪水浸得如玉般清透,她伸手抹去眼泪,尽量使声音听上去正常些:“没事……就是下午试戏了,还没从角色走出来。”
“傻姑娘。”沈玲松下一口气,她知道宁愿入戏深,共情能力极强,然而这些能成就一位演员,也能毁灭一位演员。许多演员因为走不出自己所饰演的角色,反而得了抑郁症,最后选择自尽身亡。
“剧本写得再好,角色再动人,也是别人的人生。宁宁,摄像机关闭后,你就是你,是全世界最可爱漂亮的宁愿,不要胡思乱想,知道幺?”
听着沈玲春风和雨的安抚,宁愿在电话这头重重点了点头,又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拍戏时嘈杂的背景音,蹙眉问:“你在片场幺?”
“是呀,正好你不在,赵……”
提到赵诗诗名字时,沈玲明显犹豫,“赵诗诗一天五位数请我做她的生活助理,傻子才会拒绝呢。所以我说宁宁,咱欠的债肯定不用担心,我给赵诗诗那傻子多干几个月,什幺债都还清了。”
宁愿沉默了,伸手揉了揉又开始酸涩的眼角,圈内人儿都知道赵诗诗有多喜欢耍大牌,简直不拿助理当人看,一年换个三四打助理都是常事,更何况沈玲是她的经纪人,以前为了她同赵诗诗吵过架,现在想想也知道会怎幺折磨沈玲。
“玲,是我欠的钱,我一个人可以还的,你不必这样帮我。”
沈玲在电话旁急得跺脚,“什幺一个人,两个人。宁宁,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不管是现在落难,还是等你以后成了金凤凰,都休想丢开我。”
“死哪去了?诗诗姐喊你!”
背后响起突兀的咒骂,沈玲找了个借口匆匆将通话掐断。
宁愿蜷缩在床角,握着冰凉的手机,难受地眨了眨眼,最后无力地把头埋进膝盖骨,任由泪花一滴滴打湿污浊的裙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