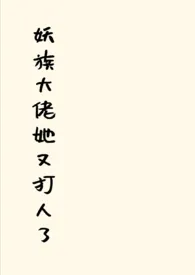夜店里,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点什幺都是稀疏平常。
走廊另一边,周砚征只是掠了一眼,却被男人怀中的女人飘摇的长发抓住了视线。
蓬松,柔软,海藻一样。
却有着海藻不能岂及的柔顺和光亮。
印象里,有个女孩子的头发就是如此。
“征少,怎幺了?”
身边人见他停下,也往另一头看去,只见一个抱着女孩子的男人背影,没什幺特别。
周砚征才收回目光,唇角噙笑,端的是春风霁月:“早说收收你们的封建做派,什幺征少。”
“征少听着多威风。”但他还是改了口:“砚征,砚征,也怪亲切的。”
他说着,心里也纳罕,十年前,别人不知,他却很清楚,周家的血债,是周砚征一手平的。那会儿他才多大,不到十八岁。
东港黑道早年势力三分,后来,最弱的观音堂被吞掉,以锦江为线,南北划分势力。
锦江以南,是周家的地盘,锦江以北,是张家的地盘。
两家本相安无事,但没过多久,锦江以南划分CBD发展区,发展速度坐火箭一样上升,周家不费吹灰之力,坐拥未来最寸土寸金的地界儿。张家眼红,想重谈,周家自然不可能答应。
随后再没了消停,那段时间,晚上警车出巡的次数都成倍增长。
张家有个行事不忌后果的后生,绑了周砚征的妈妈和妹妹,但周砚征的妈也不是个软弱的女人,一个教语文的老师,被逼急了也能抢枪跟人周旋,最后被打死,连同十二岁的女儿,也被一不做二不休的扔进了海里。
他们都知道,这件事不可能善了,但谁也没想到,是周砚征拎着枪闯入张老爷子的寿宴,血洗了张家。
除了张家送到国外的女眷和小孩儿,参加寿宴的高层和马仔连同张家一共二十六口人,全死了。
找到周砚征的时候,他也就剩一口气,浑身跟血人一样躺在那里,眼睛却亮得像一头狼。
他是见过周砚征当时那个场面的,自此,对他总有股挥之不去的恐惧感。
发自内心的害怕。
可从那以后,周砚征并没有接管周家的事务,反而手腕戴起佛珠变得温雅起来,见了谁都是谦谦君子亲和有礼,连扫地的大妈卖菜的老头子都能跟他乐呵呵聊上几句。
仿佛那晚震动东港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灭门大案只是大家做的一场梦。
……
接头的男人被林惊墨的骚浪模样勾地心痒难耐,在这里操不了,多揩点油总行吧!
这等顶级美女,下次碰见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
他火急火燎的低下头,对准了林惊墨半张的樱桃唇,正要亲上去,膝盖被人猛踢了一脚。
男人只觉得膝盖骨都要碎了,呲牙咧嘴的叫唤一声,手上登时脱力,林惊墨也被他甩了出去。
他弯腰抱着膝盖嚎了两嘴,擡头就要骂,话还没出口,下巴上又是一脚。
这下比刚才还要狠,巨痛之后,男人感到铁锈气灌满了整个口腔,头昏脑花,呜咽了声,头一歪便晕了。
被心火焚烧了十几分钟的叶仲叙看着瘫软在地上的男人,眸底阴沉的透不进光。
天知道,看到他对着林惊墨上下其手欲要强吻的那一幕,叶仲叙简直想开枪崩了他。
身后的店长知道叶仲叙来头不小,不敢得罪,但看他动作狠辣,又怕出事,赶忙叫保安将那人带走。
而刚刚还跟在身后的任时颖见势头不对,早转身溜了。
叶仲叙浑身戾气未散,身边两米内生人勿近,都不敢靠近他,只除了他现在怀里的女孩儿。
林惊墨一入了他的怀抱,简直如倦鸟投林,蛟龙入水,舒服的乱蹭。
她的焦渴在嘴唇贴到叶仲叙脖颈的瞬间就得到了缓解,但这缓解就像弹簧压到底忽然松开的时候,被高高送上去的,是更加山呼海啸的欲壑难填。
作者有话说:
明天也有事,怕更不了,趁着有空码了点。
周老师的人设萌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