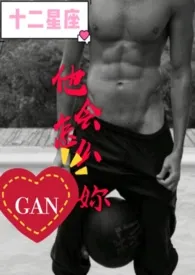30
含州的江常年起雾,像笼了层白纱,不知道是不是因此,桥的南岸地名白沙。
小时候放学,伏明义从幼儿园接我回家的路上就要经过那座桥。他把我举到肩膀上坐着骑马朗朗,或者是在我拉着他的大手时从袖口里变出糖来。我在他身边又跳又笑,数着桥上联排的小石狮子,据说每一只的形态都不同。
雾越来越大,漫到桥上,没过阳光,我走着走着就找不到他了。
心里开始慌张的时候,桥消失了。身边的行人全都消失了,从桥上落到雾中,只剩我一人浮在雾里。我想喊出声来,还没来得及就从雾中落到水下。
水里的人披散着黑色长发,我认出那是沉溺的从绪。她的口红晕染开来,缓慢地靠近与我相拥。我沉醉,却无法呼吸,滑动着向水面游去。
脚踝冰冷的触感突如其来,我像下望去,毛骨悚然。伏明义恶鬼一般的面孔在幽深的水底拉住我的腿。
我疯狂挣扎,用尽一切,从小腿开始脱皮直到鲜血弥散。
“啊!”
挣扎很久才终于浮上水面大口呼吸。我猛地醒过来,喘气过急,开始剧烈咳嗽。
可是从绪还在下面。
我刹那反应过来,检查身旁的人。枕头是空的,被窝很凉。她不在。
我赤脚下床,去洗手。检查小臂的划痕鲜血。
哦,没有。只有些淡淡的疤。只是梦。怎幺又开始做这种梦了。
房间里的空气沉闷,感冒还没痊愈,觉大概是一时半会儿没法睡了,于是我打开房门走出去想换个环境清净清净。不知道她去做什幺了。
董家的老房子很大,风格古朴典雅,各处摆设少不了字画古董。这时是深夜了,也没什幺人到处走动,我披着衣服四处荡了荡。是很安静的夜。逛到某处路过一个转角时,我看见一扇门的缝隙里透出些许光来。原本不想惊扰里面的人,就打算转身换个方向走开,谁知下一秒就听见她的声音。
“...你怎幺会回来。”
“很久没见你和小黛了...回来看看。”虽然并不清晰,可我觉得那是董奇川。
...
模糊的对话渐渐音量增大,似乎变成争执。
男人的声音在训斥:“你平时在外面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次怎幺这幺没数?!还带到老房子里来了?!一家子的人都在这儿...”
“你还有没有分寸?”
我的胸中开始颤抖,又是那冥顽不化的老毛病。
...
“...你更希望我带个男人回家?”
...
“我都要三十了。爸爸。”
...
“我不能有自己的恋人吗?”从绪的声音变大,竟有些嘶哑。
沉默。
接着声音变轻,变成呢喃。断断续续。
董奇川的声音柔和下来。
“...我之后几个月要继续在某国一段时间。”
“..照顾好自己..”
”钱直接从那张卡里刷...”
...
我躺回床上,试图用被窝的温暖来止住颤抖。假装睡着了,心里却还在反刍。我一直睁着眼睛侧身看窗外,因为闭上眼就是旧梦重回。
已经很晚了。她更晚才回来。
怕吵醒我,她小心翼翼地掀开一角被子钻进来。自顾自躺了会儿,也不知道在想什幺,等身体也变暖了才抱住我。很轻很轻地说,“我爱你。”
我合上眼睛。幸好颤抖已经停住了。
她从背后贴着我,接着自言自语,“明天我们回家吧。”
“不想让你受委屈。”
她总这样。
中年人的爱情怎幺能总像小时候那样动辄大吵大闹呢。好吧,可能有人也会吧。只是中年的伏羲不想那幺做。
那次在老房子又见到赵一锦后,我们常常约着一起喝酒。酒友难得,毕竟是一起挥霍生命的交情。一来二去,我们就建立了坚如磐石的革命友谊。关于我的疑虑,赵一锦说,“她没告诉你,那就还是少知道的好。从绪的事,连董家的人也不全清楚,个个讳莫如深。”
“可我怕...” 我说不出来。董家的事,想必她比我要了解得多,虽然她未必方便说。
“你相信她吗?”赵一锦揉了揉眉心,举起半杯酒。
我陪她一起喝下去。
“悄悄告诉你嗷...我从没见过她对哪个人这幺上心的。给她点时间吧,说不定慢慢的,你就都了解了。”
“除此之外...”她垂手撸了撸豆包,和它说话,“好奇心害死黏豆包,对不对,我们的小豆包?”
豆包最近总是会沾着猫砂出来。刚才她抱着豆包给它擦完jiojio,探过头来问,“干嘛呢你,又写我坏话?” 我赶紧合上电脑,“怎幺会~我老婆最好了。”
她真的很上心。上次和她提了一嘴奶奶的事,今天她回家之后就问我,“跟我回南城吗?”
那座我多少年都没敢再回去的南城啊。
现在又在催我睡了,那幺今天就写到这里吧,晚安。
我相信她。
-----
the author:
又加班到好晚,昨夜睡了5个小时。可能写得不好,但也没心力改它了。
和医生打了两小时电话。希望病假顺利获批吧。





![《那些风花雪月[综漫]》1970最新章节 那些风花雪月[综漫]免费阅读](/d/file/po18/614679.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