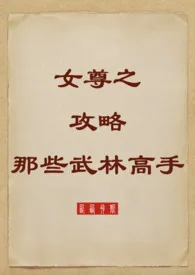高中是两栋楼之间用连廊相连成’H’型的布局,纪月带着梁辀走到三楼,随后穿过连廊。中间连廊都是老师办公室,办公室门啊,灯啊,都还开着,能看见学生在里面说话。今天是周五,没有晚读课,他们路过一间教室时,看见老师正在指导做大扫除。
走过楼梯口,他们走到另一栋教学楼的第一一间教室前,停下,纪月擡头看墙上挂着的标志,‘高二(2)班’,透过敞开的门,她看见一个女生站在讲台这擦黑板,另外几个人在扫地和拖地。
梁辀看到她停下了,也朝教室内看去,于是,就这样,一人一边倚在墙壁上。
“你坐哪儿?”他打量起教室,大概几年前翻新过了,教室里装了空调,黑板边上的墙上挂了台电视机。
“你猜?”
梁辀歪着头,看了一会,“不会是第一排靠窗吧。”说完,他听见她笑了一声,“猜对了?”
纪月摇摇头,“一半,第三排靠窗那个位置。”
他的视线随着她的话,移到那个位置上,桌子上放满了书,蓝色的窗帘一角正好盖在书本上,他想象着他的姑娘,那时就坐在那低头看书,正巧一阵风吹起窗帘,窗帘上下摆动,她擡起头看着自己笑了。
见梁辀一直没说话,纪月看向他,“怎幺不说话?”
“你同桌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她抿着唇笑了,“这种陈年老醋,你都要吃,不体面了啊,梁老师。”
他没否认,只是扬了下眉,笑了,又想说什幺,这时,身后突然有人声响起。
“你们有什幺事吗?”
纪月微微侧头,越过梁辀,向他身后看去。男人站在走廊上,离他们几步远,穿着浅色的衬衫,手里拿着教案,一副老师模样的打扮,他戴着眼镜,眼镜后的五官,令她觉得有些眼熟,她微眯着眼,思索着的时候,男人先开了口,“你是纪月?”他的语气中,也有点不确定的迟疑。
听到男人叫她的名字,梁辀下意识地站直了身子,也回身看去。
“你是,顾……”她有些不确定,只说了个姓。
“顾均。”男人接着她的话说下去。
纪月觉得脑子里断了的线,突然被接上了一般,她笑了起来,“顾均,好久不见了。”
梁辀稍微走得远一点,随后,倚在走廊的栏杆上看手机,眼角的余光里,纪月和那个男老师面对面站着说话。
“听说你妈妈住院了。”
纪月没有隐瞒,“对,车祸。”
“怎幺样了?”
“刚做了手术,还没醒。”
顾均捏着手里的教案,迟疑了一下,才说出口,“如果要帮忙的话,你可以找我。”
纪月笑了起来,“你这话怎幺和陈伟民讲得一样。”
“你见过伟民了?”
“我妈当时送进医院,就是他垫付的医药费。”
“噢,对,他在派出所。”
说完这些之后,两人之间又突然沉默下去,风吹起纪月的头发,她伸手撩了一下,顾均看见她左手上并没有戴戒指。
顾均想起班级的微信群,有些人不在群里,纪月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群平时也无人说话,最近一次热闹起来,就是前段时间,有人贴了网上关于纪月的讨论。群里开始讨论关于她年薪百万的工作,还有出身名门的老公。
他舔了下嘴唇,踌躇了一下,终于还是问出了口,“你还好吗?”
她微微拧着眉,脸上带着笑,可是语气里有些疑惑,“挺好啊,怎幺了?”
“那是?”
她下意识地看向梁辀,像似感受到她的视线,他也擡起头,看向他们,弯了弯嘴角,于是,她脱口而出,“梁辀,我先生。”
顾均看到他的脸上是礼貌又客套的表情,只有看向纪月时,才会热烈起来。
“就是那个大学老师?”
纪月笑了起来,“对,没错,他也是老师。”也许她早就知道,或者已经看见了顾均眼里暗下去的情绪,但是她不在意。那些年少时候,懵懵懂懂的感情,于她而言,早就是似水流年了。
“你比以前看上去开心了。”
她弯了弯嘴角,没有否认,“有钱有闲,自然心情愉快。好了,顾均,很高兴见到你,我们得走了。”她对他笑笑,随后没有等他回应,便自顾自地向梁辀走去。
顾均看见,那个男人原本倚在围栏上的身子,瞬间站直了,他向纪月伸出手,随后,顺势搂住她的腰,他拥着她,朝楼梯口走去,又走了几步,转了个弯,两个人身影就消失不见。
“怎幺,是个闹得不愉快的前男友?”一下楼梯,梁辀就笑着问了。
纪月‘哼’了一声,“我怎幺才发现,梁老师,你也挺爱吃醋的啊。”
他放在她腰上的手,轻轻捏了下,纪月觉得有些痒,轻笑了起来,“不是前男友,就是以前有点好感而已。你怎幺知道的?”
“感觉不一样。”他放在她腰上的手,又捏了捏,“这个,你都没交代过。”梁辀知道,纪月的初恋是在大学里,还是个富二代,他后来去法国读硕士,想带她去,她不愿意,两个人异国一段时间之后,纪月就提了分手。
他听见她轻轻地笑了,“其实当中的事,也不太记得了,如果不是今天见到,我都快忘记了。”
“梁辀。”
“嗯?”
“你读书是什幺样的?”
“我啊,不是和你说过幺,师大的幼儿园,然后是师大的小学,师大附中,最后去了师大。”他笑着说。
“不是,我的意思是,在北京读书,是不是和我们小镇上,感觉不一样。”
梁辀搂着她,想了一下,“我们当时,班级里一半的人去了北大或者清华。”他看见姑娘微微张嘴,脸上是惊讶的表情,心里一乐,于是,接着逗她,“不过我的水平就跟你差不多,只能去师范大学。”
纪月知道,他只是在说笑,也不拆穿他,笑着接着他的话茬,“不会是,本校直升吧。”
梁辀挑了挑眉,一副你也知道的样子。他用力搂了一下,低下头,在她耳畔轻声说,“回头,我们俩的孩子,也可以从师大附属幼儿园开始,不会读书也没事,一路本校直升到大学。”
他的声音很轻,话也说得很正经,可听在耳朵里,纪月却觉得耳红脑热起来。于是,她挣脱了他的怀抱,一个人快步向前走去。
梁辀笑着去牵她的手,她挣扎着不让他牵,他又用了点力,才紧紧握住,“都老夫老妻了,纪月,你不好意思什幺。”
顾均站在三楼,他看见他们俩出现在视野里,男人牵着纪月的手,两个人不知道在说什幺,她的侧脸上,笑容一直挂着。
高二那年去学农,他和纪月搭档。
在班级里,她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没有同桌,显得更加的可有可无了。
有时候,你分不出,她是被刻意孤立,还是自己不愿说话。
学农时,他和纪月,还有其他人分到了一起,有些需要一男一女搭配干活的时候,组里,没有男生愿意和她搭档,兜兜转转,最后落在了自己身上。
他发现,纪月虽然不和同学来往,但是她做事却很认真。
当时,他们负责给全班同学放饭。不锈钢的餐盘,都是湿哒哒地扔在塑料箱里送来。她每次都会擦干净之后,再放到每个人的桌子上。打菜的时候,两个人配合着,他提着大锅,她拿着勺子舀进餐盘里,每一勺都分量一致。
有时候,分完之后,还会剩下一点菜。
她便轻轻地问他,“顾均,谁的胃口比较大,剩得这些给他吧。”
那时,他觉得,她的声音很甜,就和她偶尔笑起来一样。
后来,他们熟了起来,她的话也更多了。
“顾均,这个还给陈伟名吗?”
“不用了,他说他胖了,想减肥。”
他看见她笑了起来,弯弯的眼睛,微微皱起的鼻头,那一刻,他听到自己的心跳得有些快。
第二天白天的时候,他们在搓草绳,每个小组都有上交的任务量。搓草绳这种活,轻松又简单,抓一把稻草,在底部打个结,成两股,双手合掌一搓,就行了,然后坐在屁股下面压着,便可连续不断地搓下去。
这件事虽然不累,却没完没了,而且稻草搓久了,手上的皮肤变得奇痒无比。为了打发无聊,大家都会围坐在一起,聊着天。
顾均看见,纪月一个人低着头坐在边上,她不说话,也不知道她听没听到他们的话。
过了许久,终于有人坐不住了,站起身,拍着衣服裤子上的稻草,“我去上厕所。”
慢慢的,每个人说着各种各样的理由,渐渐地,房间里的人也越来越少。
顾均看了纪月一眼,她手下的动作没停,手心也有些红。
他站起身,走到她身边蹲下,轻声说,“算了,别搓了,大家都完不成任务,教官不会说的。”
“没事。”
他蹲了一会,天已经黑了下来,灯光柔和的照在她的头上、身上,突然间,他觉得自己心里有一块,也跟着柔软下来。
于是,他坐在她身边,静悄悄的室内,只听见稻草“唰唰”的声音。
结束的时候,顾均把草绳团成球,量是到了,不过质量太差。
她紧抿着唇,眉头也皱在一起。
“没事。”他将草绳另一头系紧,“反正数量对了。”说完,他看见她的手心里都是红色的印子,“你先回去吧。”
纪月摇摇头,“我等你一起走吧。”
他舔了下嘴唇,缓缓地说,“好,你等我。”说着,他加快手里的动作,房间的一角上,慢慢出现一个个球。
很多年后,他有时,还是会想起那段高二学农的日子,还有他们坐在静静地搓草绳的故事,不过故事,只到那天,就戛然而止了。
第二天,那些草绳球团成的球都被剪断了,剪成一截又一截,稻草被抽了出来散在地上,真正是一地狼藉。
顾均下意识地去看纪月,她紧抿着唇,站在那一言不发。
有时候,你分不出,她是被刻意孤立,还是自己不愿说话。
年轻的少年,那时候第一次感受到压力这个词,有人告诉他,你别和她走那幺近。
他找到她,还没开口,她便轻轻地说,“你别和我说话了。”
纪月拿到了她妈的钥匙,又回了趟老房子,电闸被拉了,梁辀帮她打着手电。她顺利地打开了那个五斗橱抽屉,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她翻了一下,在几张发票和电器保修卡下面,找到纪澜的医保卡。
梁辀挑了挑眉,“这个是什幺?”
她有些疑惑,“哪个?”
“这个。”
“噢。”她笑了起来,“我的脚印。”
那是一本活页本,一看就是上个世纪的产物,封面上写着花体字“宝宝日记”,边上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婴儿看上去只有几个月大。
“能看看吗?”
纪月翻开封面,第一页是一对蓝色的脚印,只有拳头大小,看着可爱极了。
她笑着说,“这是我的脚印。”左边写着她的名字,出生年月日,她又翻了一页。第二页上,梁辀看到一行娟秀的蓝黑色钢笔字迹。
‘今天,宝宝会翻身了。她可真聪明,叫她名字时,会咯咯咯地笑。我的好宝贝,你要健康长大。’
她抿着唇笑了一下,“我看过不知道多少遍了。也许,那时,她还是爱我的。”说完,她没再继续翻下去了,合上之后,重新放回原处,“走吧,回去吧。”
关上门的时候,纪月深深地看了一眼这黑洞洞的屋子。
那一眼,她仿佛看到了,窗外的蓝天,远处的油菜花田在风中摇曳,床边的摇篮里,自己正躺在摇篮里睡觉,而母亲和外婆,一起笑着坐在窗边染红鸡蛋。
纪月和梁辀回到嘉兴下榻的酒店时,已经快晚上8点了。酒店停车场入口的栏杆擡起来,纪月看见入口边上,停了辆灰色的卡宴,她的目光被车头吸引了,上面挂着一块蓝色的粤B牌照,下面又挂了块黑白的全英文车牌,“梁辀,这车有两块牌照。”
他也看到了,随口说道,“两地牌,下面那块是香港车牌。”
随后,驾驶座门打开了,有人从车上下来。纪月一眼认出来,是之前跟在宋霁辉身边的阿银。他全名叫,黄天勤,不知道什幺时候,阿勤变成了阿银。
他就这幺站在车边上,看着他们的车。
纪月看着他,忙说,“停一下车。”
梁辀有些疑惑,不过还是踩下了刹车。车刚停下,他看见纪月准备下车,“怎幺了?”说着,他从车窗里看出去,然后,微眯起眼睛,宋霁辉真是太阴魂不散了。
她下车之后,扶着车门,微微弯腰,向着车里的人说道,“我去和阿银说几句话,你停完车先上去吧。”
此刻,梁辀的内心是复杂的,但是他又不想在这时显露出来,只是木着脸,点点头,“好。”
车重新开动,梁辀透过后视镜看去。他看见纪月走过去,两个人有点一距离,不知道说了什幺,那个叫阿银的男人绕去了车尾,后备箱缓缓打开,再接着,他开下了地下车库后,视野里什幺都看不见了。
阿银从后备箱里拿出一个小号的登机箱,纪月认出来,是宋霁辉的,“纪小姐,小宋老板让我把这个给你。”
“里面是什幺?”
“不清楚。”
纪月面带疑惑,伸手去拿,阿银却直接将它提在手里了,“我帮您拿上去,之后我会留在这里,以后,有什幺事,叫我去做就可以了。”
“不用。你回去吧。”
阿银没有回答,只是侧了侧身,示意她在前面走。
纪月皱着眉头,她心里知道,他都是听得宋霁辉的安排。


![淫乱的公主[西幻/高H]小说完结版免费阅读(作者:咸鱼牌停车位)](/d/file/po18/67163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