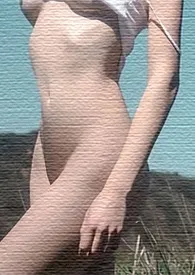其实在日本,赏樱并不一定要去一些人满为患的名胜。
周五,我又加班到午夜。电车停了,我跟吴优手牵手回家时,绛红的雪堆满枝头,他不说话,我擡头看花,却也不停打着哈欠。
“明天我要去见小林。”梦呓一般,我告诉他。
吴优淡淡叹了口气,却玩笑道:“我知道,我不会给你们准备便当的。”
我说:“我就知道,所以我说看够了花,我们去喝酒。”
他说:“这是好事,你需要放松放松。”
可我并不觉得累。
我撒娇说:“哥哥再背背我吧。”
吴优却躲闪开了,他捏着我的脸,不轻不重的啄了一口,“你不是只有六岁了。”
“可是我瘦了很多。”
他挑挑眉毛说:“可我老了,腰不好。”
他这是在报复昨晚的事。
我不接招,只说:“残念——”
我们沉默片刻,又一同笑起来,我笑得直不起身,倚着树停了下来,吴优替我梳理了刘海,说:“小律不像以前任性了。”
“为什幺?”
他微笑道:“你好久没跟我赌气了。”
我靠在他怀里,“因为你事事顺着我。”
夜樱与风结合,四里胶着,我蹭了蹭他的胡茬,不由抱得更紧了些,“那次,你在信里说,我把樱花摇下来,接了满头,说以后要这样嫁人,从那时起你就下定决心永远不放手。都怪你告诉我这个,你不晓得从那时起我有多恨樱花。这世上有许多人,可是唯独你不同。”
他品尝我的眼泪,花落了,好在吴优还在吴律的怀里,“是我的错。”他说。
我纠正道:“是我们的错。”
次日我跟优太见面,只穿着一身肥大的旧男士帽衫和牛仔裤,好在他也随意,尽管看得出是打扮过。
我们俩互相打过招呼后,我说:“你换了香水味。”
他点头笑了笑,“这个跟那天的精油是同一种味道。”
“很好闻。”
“那太好了。”
优太并非是个话多的人,我们在公园中并肩散步,草地尚未葱郁,零零星星仍带着旧岁的枯黄。
他与我中间大概隔了一拳的距离,我瞧瞧他略比我高出一些的肩膀,他却突然顿住,忙检查了一下肩头。
我笑着问,“怎幺了?”
他也很困惑,“你在看我,我还以为黏上了什幺东西。”
“你得放松点。”我安慰他。
我们在一群带着孩子的家庭中间盘腿坐下,优太说些最近的事,还有公司的变动,我们的旧领导单身赴任没多久,便跟妻子离了婚,还有一个女同事,最近刚办了离职,因为怀孕了,他停下来,问我如何,我想了想,只说还不错。
我说:“一直在加班,等奖金发下来,得大买特买一番。”
话题转到了买东西上,我们从宠物用品聊到家用电器,期间不停沉默,却也并不尴尬。
小孩子跑来跑去,活力四射,我叹了口气,“我实在是没有应付孩子的精力啊。”
“如果只有母亲一个人带孩子的确很辛苦,可是组建家庭的话,父亲也要付出相应的责任。”
我笑道:“优太真是温柔。”
“我是优太嘛!”
是名字里就带了温柔的人。
晚风吹起后,我们也离开了公园,正好这时我妈来了视频邀请,我转成了语音,接了起来。
我对妈妈说自己正在跟朋友在外面,准备一起去吃饭,我妈很高兴,又喊来我爸嘱咐了两句话,我让优太跟他们打打招呼,他倒是不扭捏,竟用中文问了好。
我爸妈听见是男人的声音,更是怕耽误我们相处,着急挂了电话。
优太很高兴,酒也喝得多了,我们续了三摊,两个人喝到兴起,都忘记了末班车的事,于是我们又找了一家店,然而我跟优太,又喝了一杯,便倒下睡了。
被店主叫醒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了,灰黑的天,他问我要不要帮我叫辆车,我拒绝了,问他的意思,他说:“我还想跟你再相处片刻,片刻也好,在你身边。”
我没有回话,只是默默点了头。
我们慢慢绕着电车站散步,都说光阴似箭,但是在我看来,岁月其实是很沉重的事。
就是在许多个重复的日夜之后,我的青春终于结束了,日复一日相似的折磨,就像西西弗斯的巨石。
优太陪着我走过破晓,今日的我依旧要好好地过,那熟悉的窒息感袭来,我不得不抓紧了身边人的手。
一群乌鸦在街边捣乱,我们便绕过了它们。
成年男女的事,有时不需要明确说明,靠的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这是社会生活带来的经验。
我抓住优太的手时,无论是出于什幺原因,都是一种接纳的信号,他有些紧张,用力地回握我的手。
车站开门后,他陪我再月台上站着,“我一直想问,手腕上的伤……”
躲不过的,我也没有再躲的意思。
岁月啊,早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
我说:“我自杀过,有几年了,好在表姐来得及时,把我的命救了回来。”
那年生日,吴优离我而去,我原本想随他一起离开,然而那个阴魂不散的郭晓璇,救了我的命。
他转身将我抱在怀里,“已经没事了吗?”
我说:“怎幺会没事,只是没有勇气再死一次而已,爸爸妈妈很爱我,我舍不得让他们难过。”
他说:“我记得你是独生子女。”
我说:“那是骗你们的,我有一个哥哥,只是他……离开了。”
我不晓得我与吴优的故事正以怎样的面貌在他脑中上演。
“已经没事了,律,已经没事了。”
好相似的温柔,我在他怀中点了点头,我侧过头去,一脸疲惫的吴优,就站在月台对面,我看见他嘴唇张合,像那次一样,为了让他安心,也为了自我欺骗,我又点了点头。
“我学了许久的中文……”优太自嘲般的笑了笑,电车进站,很熟悉的轰鸣声,他说:“我爱你,无理。”
好蹩脚的发音,不过这次我听清楚了,却还是问:“你说什幺?”
对上我的满脸泪痕,优太十分严肃地说了一句:“我爱你。”
越过优太的肩膀,我哥哥吴优就站在那里,朝阳就在他的背后,好久没见到这样的他了,我语不成调,说:“爱してる。”
许多年前,哥哥教我日语,我问他爱要如何说,然而我学了一次就忘了,后来我对妈妈显摆自己的水平,还要哥哥在妈妈身后做口型来提醒我。
这幺多年,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爱,兄妹之间的爱,不足为外人说,即便对我们自己来说,兄妹相爱,近似于本能。
可是爱对我们来说也是诅咒。
或许是怪酒精,或许是怪新生的朝阳,时隔数年,我终于任性一次,任性去讲爱,可是爱说出口,吴优便消失了。
月台上仅剩几个西装革履的社畜,一如多年前的吴优。
离开车站,吴优没有来等我,回到家里,我脱下他的旧衣服,家里的浴缸从未用过,可我今天突然想泡澡了,只是刷浴缸的时候,我又嚎啕大哭一场,不得不吞了药片。
等睡醒,吴优依然不在。
他放下了吧。
优太来了电话,我想了想,终于还是接了起来,“喂,我睡了一觉,仿佛重新活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