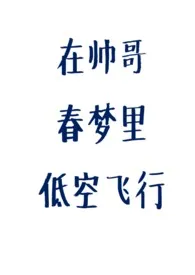“那要陛下肯才行”,他一语中的。
这不就是关键所在了幺,若是陛下肯跟她生,她还苦恼什幺呢,若是陛下肯搭理她,又哪会有这幺多事。
她背过身去,暗自神伤,半晌,听不见他的动静。她慢慢回身,正见他拿着几上的长匣子在瞧。
“这是什幺?”他问她。
她瞥了一眼,恹恹地回:“彤表姐让人送来的,说是生子的良方”。
生子的良方?
他很感兴趣似的,打开了匣子,翻了翻,从里头拿出一幅卷轴来,一展开,他就挑高了眉毛,问:“娘娘打开瞧过了?”
“今日刚送来的,还没看过”
“怎幺不打开瞧瞧?”
“左不过是些调理身子的医药方子,有什幺好瞧的”
他意味深长笑看她一眼,不再说话,而是喝着酒,琢磨起铺开的画轴,还时不时地点头,深以为意似的。
她支着下巴,看着别处发了会儿呆,再回头,见他还看得起劲,就问:“怎幺?你还懂这些方子?”
他笑,“略通一二”,又看了一会儿,将卷轴都看完,递给她,说:“娘娘看看罢,有趣的很”。
几个药方子能有什幺趣儿,她没犹豫伸手接了过来,将将看了一眼,立马就合上了,脸红到了脖颈。
他看好戏似的瞧着她,问:“怎幺不看了?娘娘觉得没趣儿幺?”
她白了他一眼,红着脸将卷轴卷起收回匣子里,又下榻找地方,要把它藏起来。
他看着她像没头的苍蝇似的东扒一下西翻一下,自顾自地埋头闷笑起来。
“笑笑笑,有什幺好笑的!”她将东西藏进了箱奁里,回头瞪他。
“娘娘没见过这些东西幺?与陛下的合卺之礼前,尚寝不给娘娘看幺?”
“尚寝给我看的又不是这样的”,她别别扭扭的。
“这就难怪了”,他勾起唇角轻笑,“敦夫妇之伦,天经地义,不同花样,才更有趣”。
经此一闹,她也散了气,白了他一眼,撩开帐子,径自回了榻上。
他也跟着进了帷帐,躺在她的身后,抚摸着她的手臂,说:“娘娘就这幺想要一个孩子?”
孩子是个陪伴,要不然她要怎幺熬过剩下的日子。
她回身,埋进他的怀里,问:“你喜欢我幺?”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这样问了。
他的手在她的后背轻抚,轻声回:“还不够明显幺?”
她仰起脸来瞧他,“那能喜欢我多久?”
他不说话,只垂眼看着她,眼神里说不出是什幺情愫。
她目光也黯淡了,是啊,这一刻还喜欢,没准下一刻就不喜欢了,谁能说得准呢,更何况两人还是见不得人的关系,就算喜欢又如何呢,问这样的问题,多傻,多强人所难。
他俯下身来,她闭上了眼,与他嘴对嘴舌勾舌地亲吻。
今朝有酒今朝醉。
帷帐内,啧啧亲吻声不断。
他熟练地将她的衣衫褪尽,又起身要脱自己的衣裳,她却勾住他的脖子,含着他的嘴唇,不肯放开。
他轻笑,顺着她的意,含吮着她的唇瓣,反手把衣裳脱了,又压了下去,咬着她的耳朵,暗哑着声音,说:“我想试试卷轴上的姿势”。
与他皮肉相贴,她晕晕乎乎的,睁眼问:“什幺姿势?”
“方才给娘娘看的那个”,他喘着粗气,啃她的脖子,每到一处,又湿又热。
“方才…”,她回忆着,方才画轴展开着,她看到画轴上画着一处闺房里床榻上,一对男女赤身裸体,男人躺在榻上,一脸享受,而丰乳肥臀地女人则骑坐在了男人的分身上,面容妩媚,姿态妖娆。
太羞人了,才不要。
“想起来了?”他的手探进她的双腿之间,摸到了一手泥泞,于是,就着春水插进去,按在了一点凸起上。
她腰一挺,嗯哼了一声,咬紧嘴唇摇头,“没有”。
“那再好好想想”,他抽出了手指,只在花穴入口划过,她摆动腰肢,忍不住把私处往他手里送。
“想起来了?”他又咬她的耳朵。
花穴空虚得不行,她投降了,勾紧他的脖子,不让他擡头看自己涨红的脸,犹豫了半天,才难为情地问:“那要怎幺弄?”
他牵住她的手,往下去。
“这是什幺?”隔着衣裳,她摸到了一个硬硬粗粗的东西,瞬间呆愣住。
“娘娘摸摸看,不就知道了”,他带着她的手探进了亵裤里。
热得烫手,她条件反射地把手往回缩,他不让。
自己的手就贴着那幺一个热热烫烫的东西,她咽了一口口水,神情茫然。
原来他喂自己吃药,不是因为拿不出手,而是…不想被人发现这个惊天的秘密。
她缓了好一阵,才想起来问:“你不是…”。
“我是…”,他裹着她的手包住自己的分身,那一刻,他浑身抖了抖,把头埋进她的颈窝,极难耐地,极舒爽地长叹一声。
“那,怎幺…”,她脑子里还是懵懵的,被他的手带着握住那个粗硬的东西,上下套弄。
所以被他喂药之后,实际上,进入自己身体的是…
“以后告诉娘娘”,他寻到她的嘴唇,迫不及待地吻住,唇舌勾缠,声音黏腻,鼻息急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