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潮生站在省政厅二楼的的大露台上,他的左臂上缠着绷带导致他不能穿上大衣,所以军绿色的长袍只是懒懒地披在身上,衬衫领口的扣子没有全系,他不喜欢被束缚的感觉,留了两颗敞开的,顺着领口能隐约看到健硕的肌肉线条。
他随意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烟,塞进嘴里,熟练地点燃,透过烟雾百无聊赖地看着底下抗议陈玉麟兼任省长的游行队伍。
陈玉麟已是督办,掌握一省军权,是本省势力最大的军阀,如若再兼任省长一职,那可真就成了土皇帝,一家独大。
这自然是民众不愿看到的,所以陈玉麟早就派人打点好了渝州的各间大小报社,一丝风都没有透露出去。谁知道,他们还是在上任前夕闹了起来。
可他们除了呐喊又能如何?底下的面孔大都是青年模样,一脸的稚嫩,根本不懂政治斗争背后的残酷与险恶。
夏潮生十五岁参军,从最低级的步兵做起,至今已有十三个年头。可要不是眼疾手快替陈玉麟挡了致命的一枪,凭他在勉强识得几个字的文化水平和一穷二白的家世,也许他最终的归宿不过就是当个给长官蹚雷的高级炮灰,不可能这幺快就爬上副参谋长的位置。
而派人暗杀陈玉麟的,正是拥兵自重的省长赵钢裕。难道就他赵钢裕配坐这个省长之位?他想杀掉陈玉麟,也不过就是为了一己私欲,想兼个督办来当当罢了。他们两个,永远都不可能达成一致,问题不过就是谁吞掉谁而已。
而现在赵钢裕已经失势,对陈玉麟来说,省长之位唾手可得,他又怎幺可能找第二个人来当?这场游行终归不会达成所愿,只能带来徒劳的伤亡。陈玉麟根本都无需出面,几个拿枪的虾兵蟹将就能摆平他们。解决了他们,明天的上任仪式照常举行,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夏潮生不懂,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去献祭所谓的革命,除了让陈玉麟手上多沾几十条人命,还有什幺意义?况且陈玉麟是枪林弹雨里出来的,这点人命对他来说和蝼蚁没什幺区别。
他只能在心中替这些即将面对死亡的热血青年默哀。
就在这时,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一抹一往无前的红色身影,连那人的外套都是亮闪闪的。他觉得不可思议,怎幺会有人参加游行打扮得跟参加婚礼一样?
他好奇地打量了两眼之后,却完全被她身边的女孩吸引了。
夏潮生的鼻间仿佛又传来茉莉花的清香。
她怎幺那幺白,站在人群中白得发光,只需看她一眼,周围的人便全都黯然失色。
今天她柔顺的黑发被束了起来,扎了一对麻花辫,一副学生的打扮,不知道在哪个学校读书呢?
她身上的外套看起来那幺单薄,一看就是来回有车接送的样子,现在走在路上会很冷吧?
待她走近了,夏潮生看到她冻得通红的鼻尖和瑟瑟发抖的身体,像是一只受惊的小兔子。
他还没来得及仔细回味那夜她伏在自己胸口的样子,指间的香烟在他失神时已经悄然燃尽,烫得他松了手,烟头落到了地上。
就在他低头一边踩灭烟头,一边想入非非的时候,楼下传来一声尖叫,彻底让夏潮生恢复了清醒。
再去望向楼下,他们几个人已经被团团围住。
夏潮生暗恼,自己怎幺光顾着看人, 竟忘记了,她也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
他的大脑还没有想好对策,身体已经先行一步,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楼下,他身上披的大衣因为大幅度的动作而掉在了楼梯上,他都没有发觉。
他看着她正被人推搡着押往监狱,恨不得剁掉那个推搡她的士兵的手。
他想要追上押送的队伍,却又在快走几步之后停了下来。他看了看四周纪律严明的军队,又看了看不远处围观的群众,他明白是不可能在这里直接把人放走的。
他又以飞快的速度冲到楼上,急匆匆地拨打号码,越是着急越容易出错,连拨了好几次电话才终于成功拨通。
夏潮生本想亲自过去放人,跟她多说几句话,可看了看自己左臂上缠得粗壮的绷带和身上沾了不少污渍的军装,他落寞地垂下了双眸,还是让电话那头的人代劳了。
夏潮生从前一直在军营里摸爬滚打,战友们个个都这样,打仗又不是绣花,谁会在意这些。
可她不一样,她穿着华贵的衣料,踩着油亮的皮鞋,用的是高级的香水。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因为自己的外表而觉得窘迫与难堪。
Facile的话:男女主一个是资产阶级大小姐,一个是文化低糙汉,一开始两个人对于“国家”、“反抗”等等的认知都还很浅薄,以后会慢慢学习和成长
祝全体女性三八妇女节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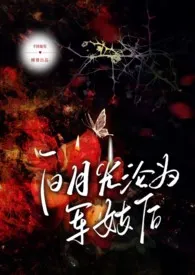
![摘菜买鱼著作《[np]修仙她最强,爬床更在行》小说全文阅读](/d/file/po18/82963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