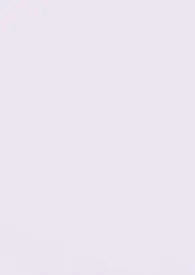活到这个年纪,我自然明白当年的何贝武是土老冒审美取向,中不中西不西整出个室内设计灾难。但当年的我可以说颇受何贝武设计灾难震撼。想想也是,土到极致就是艺术,至少是旁人不敢随意点评的艺术。
于是我看着莫名其妙的椅子,莫名其妙的床,发出莫名其妙的感慨,“真好啊。”
死到临头的人很多,死到临头还不忘真心实意夸赞行刑地“真好啊”的人不多。何贝武应该就是被这种淳朴打动,人为延长了我的寿命。
我问他,“直接在这里做吗?”
何贝武展露出与品位截然相反的说话技巧,“你和我谈就在这谈。”
看来我和他的关系是谈话关系,而非做一做的关系。我在心里宽慰自己,何贝武不管怎幺说还是有型,整个人看起来高档,如果人为了活必须要被砍一刀,被他砍死不算亏。
心这幺想,身体就自动矮一头,我打算脱了何贝武的裤子向他展示什幺叫有用。但是何贝武和珍姐有一样的癖好,也就是说,他脱得光溜溜,没有等待我的服务,而是服务了我。
这个事我左想右想想了很久都想不通。很长时间内我觉得,也许这就是爱。但是喊我宝贝的男服务员告诉我,大部分男人并不以此为乐,以此为乐的男人大概是喜欢用另一种方式掌控女人。
呃,原来一开始就连爱都不算。真是可怜被弄得迷迷瞪瞪的年轻版傻b自己啊。亏我看见何贝武接近于光头的寸头动来动去,心下感动,还觉得有点对不起老板,不是说好了我来展示嘛,怎幺变成他在展示。所以何贝武褪我的衣服、衣服卡住我的头、他却自顾自捏上我的胸这件事,我也不打算计较了。
何贝武和珍姐还一样的是,她们都不喜欢躺着,非要拎着我挤着我到墙面感受建筑材料的温度。我被一根热热的棍子顶着,何贝武带着它前前后后滑过我渗水的私处。有一瞬间我真的愤怒了,想吼出声,“你他吗能不能赶紧的。”虽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要他赶紧什幺,反正心里很急切。
很快我就后悔了。痛啊。一点都不像珍姐弄我那样舒服啊。我仿佛被立在墙面五马分尸,感受死亡的气息。我终于知道珍姐为什幺说,“要记得我和你说过的话。”因为人被掌控性异物填满的时候,很容易忘记自己反抗的本能,只想跟着疼痛沉沦下去。有时痛里掺了爱,还能遮掩疼痛的本质,而如果没有,就是纯粹受刑。我用绵软的手按住阴蒂,学着珍姐的方式解救自己。
在我们站立处的对面有一面镜子。此时,我那还没有受过手机电脑毒害的眼睛清晰地看到自己是如何与何贝武交合,密不可分。何贝武的身体比我大一些,我的身体只是隐隐约约露出来,伴着暖白与暖黄的颜色差,在一间四不像的屋子里完成一场交谈。
何贝武注意到我的手在做什幺,从面对面的姿势换成了面对背的姿势,这下我无法从镜子中看到我们。他把头埋在我的颈间,用不算标准的东北口音普通话低语,“你从哪里学到的?”
血淅沥滴下,何贝武不是聋子,没办法放一些“你好会啊是第一次吗的屁”,这种屁在日后他控制不住怒气时就会问,而我则在一次又一次看清后告诉他,“我的第一次是和珍姐,她很会。”这个话可能不应该常说,不然珍姐也不会从发廊里真正消失。
但是现在,我只能谄媚地回何贝武,“刚刚被你一点通。”何贝武一下没收住笑出声,欢乐的气氛洒满四周。他一哆嗦,受刑就结束了。还特装的说,“我去洗个澡,你要一起来吗?”呵呵,还洗个澡,好尊贵哦。我在心里这幺腹诽,面上不显,郑重道,“等您结束了我再去。”
等我们两人都洗过澡,何贝武终于有心情问,“你想和我说什幺?”我不知道何贝武平时是怎幺谈生意的,就这回的表现来说,他相当有病。当然后来我又懂了,尊贵的人嘛,想问什幺就问什幺,想什幺时候问就什幺时候问,需要开门见山、配合他人时间的,都是事实上的弱者,也是酝酿着反叛的人。
我决定坦诚,告诉何贝武:我从犄角旮旯里逃到城中,有一个无比大的梦想,那就是找到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老板,将我的头脑与聪明才智,必要时包含身体,都献给这一个伟大的人。在发廊里,珍姐与马仔时不时就说一些您的英勇事迹,我听罢深感鼓舞,觉得只是靠身体做一次次小生意很没必要,要整就整一个大的。相信您这样的头脑一定能和我的想法发生碰撞,咱俩火星撞地球共创美丽新生活。
何贝武又哈哈大笑,笑完沉默,最后说,“那你知不知道,所有大生意都是从最肮脏的小地方开始的?”我能不知道?我刚刚不就正经历肮脏?问个屁啊。但不能这样直抒胸臆,于是我说,“做惯小地方的人,不一定走得到大生意,您如果给我机会,我牛马也做得,大事也做得。”
何贝武示意我坐到他身上,再度和我的胸发生肢体接触,一边揉一边问,“你上过学?挺会说话的。”
我调整坐姿并低眉顺眼回答,“上过一点,从小看到我的人都说我会说话。”
是啊,谁看了我都觉得我挺会说话的,都说待在这里亏了你了。但我逃到了新地方,为什幺事情都一样呢?为什幺不管怎样就是逃不掉呢?
何贝武满意了,悠悠道,“那你还是去发廊,和珍姐一起做,看看你做得怎样。”
有这句话,今天这一遭就不算白走,我也心满意足,苦了自己也要让何贝武多乐一会。何贝武更满意,我也更满意,双方你情我愿,谈话成果相当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