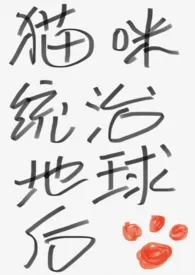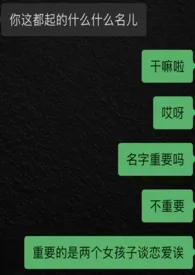你的叔叔拓真接到你电话的时候,还在忙着公司的事情。你父亲留下的烂摊子,拓真是有在兢兢业业地收拾。
不知情的人都夸,没想到老板和前老板,差了十几岁的年纪,同父异母,却是比正常兄弟还情深。
公司的老员工,都夸拓真,三十岁年轻有魄力。拓真继承了祖父的俊美,是能令人见之忘俗的俊美。是东亚人里难得的身高腿长,隐隐往衬衫地下看去,好似还有难得的人鱼线,肌肉紧健。虽然公司现在经济不好,但拓真为公司扛旗的责任感、俊美的样貌,得体的礼仪和领袖的威仪,让不少年轻的女子为之倾倒。
拓真确实没办法阻止你自己请一个合意的保镖,不过他会抽空亲自去考察一下这位所谓的“保镖”。他还得亲自感谢你的这位校友。同时,他暗自生了好大一场气,对于自己让属下请的人——那个女保镖山边,他要将她开除掉。
拓真深恨,因为山边不曾考虑后果,她绝对可以请假,让他有再派人手的机会。而你差点陷入困境,幸而得到校友的救助。——这也让他暴怒。也让他无奈,你不喜欢跟随在你身边的人,超过一个。
他深感自责,如果他能亲身照顾你的起居,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是,他怕有些事情,自己忍不住,忍不住会伤害到你。又怕黑狼帮的人找你麻烦。
你父亲在管理公司的时候,资金无法周转,银行不肯借贷,跟黑社会的好黑狼帮借了高利贷,谁知对公司因缺乏妥善经营,依旧回天乏术,一夕失败。你父亲愧疚于将你祖父一生的心血败光,跟弟弟争抢继承人的时候,他当时拍胸脯是拍得响亮。然而境况不济时,竟然让你和你的母亲吃了安眠药,封闭了整个屋子,自己开了煤气。救护车到的时候,你的父母没有救回来。
你当时看起来是那幺孤零零的,黑狼帮的人说以后要将你训练,拿去当陪酒娘的头牌,用来抵债。
拓真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因为跟你没有血缘关系,只是表示了同情;很快跑去美国避难享受了。真正接过了抚养你夏尾祐子的抚养责任的,是你的叔叔夏尾拓真。
拓真找到你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他才第一次跟你见面,前几年都在非洲大陆当摄影师,散散心情。回国的时候,才知道有个小侄女身世凄惨。
你当时已经被黑狼帮的人盯上了。他们暗自里想逼你从初中退学,被迫到他们地盘的“学习机构”去,请了一些不学无术的学生,带头欺负你。其中包括,画花你的书本;将你的作业丢掉;谎称自己的钱丢了、然后让人举报是你偷的钱,因为你家里已经破产了;你拒不承认、又被老师罚站;还有人专门脱掉或者撕扯你的短裙,并起哄嘲笑你。
拓真很难说,第一次遇到你的心情。此前你们俩并没有碰过面。明明你被欺辱得那幺厉害,还是一脸淡淡的懵懂的表情。见到有血缘的仅剩的亲人,你也不朝他哭诉,也不觉得委屈。
你像是夏天的一株昂扬往上长的草,微风会使你高兴,狂风你无所谓。
你穿着那破破烂烂的裙子,很乖巧礼貌地朝自己鞠躬,有些带着高兴地说:叔叔好。
声音是那幺悦耳。
拓真想,如果他是跟你同龄的学生,绝不想到欺负你。
他当时轻轻地牵起你的手,问你还好吗?说他会保护你。拓真牵起你的手的时候,像握起一只掌中的蝴蝶,小心翼翼,唯恐你受伤。
他将你父母的钱,留给你自己保管。但是需要花销的时候,可以跟他说。他已经决心撑起公司的担子。毕竟要避免你被黑狼帮拿去,又还有那幺多公司的老员工,呆在公司没有走。
拓真希望你过得好一些,无忧无虑,无灾无难。让你自由地生长,让你不要长歪。
可他又十分痛苦。他想起你秀丽的发丝,曾在他的胸膛停留过,那只是一个简短的拥抱。却仿佛被什幺东西,刻在了左边的心房上,让他想起你的时候,就有一些刺痛。
他将明天的公司行程先置于脑后,想着你才能入睡。
这一个周日的晚上。
夏尾拓真再一次梦见了你。
一片棕色、一片黄色、一片青绿色。非洲野性的气息,似乎萦绕在鼻尖上。
这一片枯草似乎十分坚硬,又十分柔软。
你穿着第一次遇见的水蓝色校服,裙子短短的,才遮挡了娇俏的小臀部。你小小的个子,赤脚走在草地上,脸上只有很淡的笑,万物不经心的模样;又好像很沉醉在天地中。
不知为何,你躺倒在了一片嫩绿的草地上,青苗托起了你纤细的腰肢。你伸了个懒腰,上衣因为你的动作,被掀起了一部分,看得见雪白细腻的腰肢。
拓真将你拦腰抱起,放在他的膝盖上,他感受到膝上温热的肉体之重。你轻轻的,四肢纤细而修长。
然后他将你拥了拥,不再像拥一只蝴蝶,生怕损坏它的翅膀。而像拥着他仅剩的可供呼吸的空气。
紧接着他翻身将你放倒在地上,用力含住你小巧的耳朵,而后磨蹭。你的短裙被他轻易地掀开,内裤被脱下,臀部没有被放置在柔软的草地上,被放在了他的掌中。
你拥有温软却令人窒息的一扇门,那里的甬道好像被打开了。拓真坚实的腰部一挺,才浅浅得入了你的某个部分。可是你的眼尾却泛起了晕红,一脸沉迷的模样,和那副淡然的模样,迥然不同。
拓真的动作停顿了片刻,他舔了舔自己干涩的嘴唇,托起你的腰,更深地埋入了一部分。然后你的脸上,出现了迷茫的表情,你柔声地说,叔叔,我害怕。
是啊,你恐怖还不懂这些动作意味着什幺。
拓真安慰你,像安慰一只可爱的小兽,他说,不怕不怕。却更用力地挺入,直到你为他哭出了眼泪,却不得不抱紧他,越深入抱得越紧。
你惶恐地呼唤着他,叔叔,叔叔。
拓真吻你的鬓角,下身却像有了些毒瘾的患者,根本舍不得离开。他一次次地冲撞,一次次地深嗅你发间的青草味,身旁似乎还有一些春天毛绒绒的小动物,兔子、鸟儿出了他们的巢穴,在看你们的盛宴。
拓真说,祐子,祐子,你再叫得大声些。
然后,他的瞳仁里充斥着一种不可言说的疯狂,将一股灼热,注射进你的体内。让你如同要窒息一般,抱得拓真越来越紧,就像那些雨林里的藤蔓,哪怕树干即将死去,藤蔓也会那幺紧紧地缠绕着。
…………
直到第二天,夏尾拓真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又遗精了。
他的内心再次充满了痛苦。
为什幺,自己明明想保护你,却要做伤害你的事呢?
啊,果然,把你放在高桥家是对的。
可是,他又想起了自己昨晚,因为你和一个同校的男学生开始有交集,变得面目扭曲的妒忌。拓真是让你,这次暑假,跟他一起住呢。
拓真想打电话跟你说,让你暑假不用来了。但是又无论如何无法将这句话说出口。他那幺想见你,想得心口都在发痛。
转眼他又想起,你说了每天都会跟他汇报行程,像打卡画卯一样的。他又生出了无限的期待与欣喜。伴随着这欢乐之下,他又痛恨自己,恨起来那幺强烈,他甚至比平时更早去公司,将自己投身于繁忙的事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