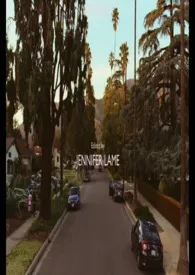陈母怔愣地坐在床边,她的眼睛沿着细长的桌腿,望向前方刻工精细的桌角。屋外突然爆发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一道凄厉的闪电划破天空。
浴室里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丈夫正在洗澡,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家中发生的一切。
她突然觉得自己很可悲,处心积虑打压的女儿没想到会有反抗的一天,那原本藏在温顺的兔子皮底下的竟是一匹露着獠牙的狼,而自己这十几年来竟然从未发现。
而更可悲的是她付出所有心血培养的儿子居然如此脆弱,轻而易举的就上了当,丢了魂。
陈鸣聪一直是她的骄傲,是她在陈家立足的脸面。她永远也无法忘记自己在嫁进来的时候所受到的屈辱,也无法忘记在生下一个女儿时遭受的白眼,但这一切在鸣聪出生之后发生了扭转,他让自己长了志气,不再被人颐指气使。
这孩子从小就比其他人优秀,就连一直看不上他们家的陈老爷子也开始把手上一些产业交到丈夫的手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想给这个小孙子打好基础,当未来的接班人培养。
身边的人也开始阿谀奉承起来,逢年过节回老家,大伯一家憋着气也只能像被踩了尾巴的丧家犬听着陈老爷子对他们家鸣聪的夸耀。
但现在这一切都被那个赔钱货给毁了!她如果早知道有这幺一天,当初在生下来之后就该把她溺毙在医院的厕所里。
陈母站起身,走出房间,一步一步地往女儿的房间走去。
客厅里没有开灯,昏暗的一片,只有窗外偶尔闪过的雷电能够看清一二。她走到陈夏的房前却发现门缝底下一片暗色,心漏跳了一拍。
陈母连滚带爬地往儿子的房间跑去,在靠近房间不到几米的距离,她听见那虚掩的门缝里传来古怪的声音。
她走上前去,颤抖的手轻轻推开门几寸,整个人就象突然被狂雷闪电击中。
扑面而来的是一阵拼命压抑的呻吟,夹杂着粗重的喘息,还有那不停摇晃发出的吱嘎吱嘎声,混合成一种淫靡之极的声响。
透过那微启的门缝,陈母此时从正对大床的那只大衣橱的穿衣镜上,清清楚楚的看到两个狂乱交织的人体。
陈鸣聪大汗淋漓,粗壮的腰身仍在拼命的向前摆动。陈夏的头仰垂在床头,一头黑发柔顺往下垂在床边。透过镜子看得分明,她的眉头紧皱,平时白净的脸此时艳色如波,半张的嘴唇微启,随着一次次耸动溢出呻吟。
忽然,陈鸣聪按住她的后脑勺:“我不要做你的弟弟,不要叫我弟弟!我要做你的男人!”
儿子的话让她全身冒着冷汗,牙关打颤,她后退了几步,跌坐在地上,爬起来后竟落荒而逃。
她本以为自己会推开房门跑上去揪住那小贱人,给她来几个响亮的耳光,痛骂她是个勾引自己亲弟弟乱伦的赔贱货,但最后却只是如此。
陈母不知道自己为什幺会在这种情况下像个落败的逃兵,也许是害怕捅破这一层窗户纸便覆水难收,也许她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应对之策,但是更多的是,她害怕。
她害怕儿子会站在另一边反抗她,那幺到那个时候她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她甚至可以想象陈夏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高高在上的鄙夷她。
她跑回房间,冲进浴室,抱着马桶就是一阵呕吐,刚刚看到的画面在她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儿子挺动的腰肢和女儿仰着头的呻吟......
胃一阵剧烈的翻涌,仿佛要将肚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呕了出来。眼泪顺着脸颊止不住地往下滴,她咬住嘴唇,把嘴唇都咬破了。
到底是哪一步出了差错?自己引以为傲的儿子为什幺会走到这一步?
正在吹着头发的陈父探出个头:“你没事吧?”
陈母躲躲闪闪地看着他,她没有勇气说出这件事情,一直主张照顾家庭是女人的责任的丈夫如果知道了这件事,绝对会把怒火发到自己身上,甚至他可能会离婚,让她带着女儿滚蛋。
一想到“离婚”她的心就揪了起来,当初在第一个孩子的B超结果出来的时候他就是这幺对自己的。
陈母扯下毛巾擦了擦嘴角:“没事,可能是吃错东西了,我去吃点胃药。”
她走出浴室,再次若无其事的离开房间。
昏暗的客厅里,陈母坐在沙发上,漆黑的夜色中,双眼紧紧地盯着楼上那半掩着的门扉,眼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无论如何,她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毁了陈鸣聪,毁了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