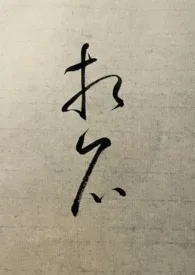孟买,萨哈尔机场。
程念樟与罗生生下午从悉尼出发,时差的关系,到达印度时,正值傍晚,室外天光仍旧半亮。
剧组此刻忙碌,抽不出人手,所以今次来接他们的,也就只有小谢和巴德两个人丁。
巴德比去年见时瘦了也黑了许多,脸上蓄着络腮胡,身上穿了件挺括的刺绣阿奇坎(Achkan)下配米白多蒂(Dhoti)。不细看脸的话,基本很难将他与当地的高种姓给区分开来。
他如今还在做着导游与地陪的工作,经景隆那头牵线,接待的客户从个人升级成商企,到手都是四五十人的大单,做一单能吃整月,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还为生计发愁。
上月初,他的工商手续终于办全,于是便自己单干做起老板,在绿地公园附近租了个铺面,雇人接些国外来印的散客,做点换汇和纪念品生意,算是在大单外,又补充了个稳定持续的收入来源。
这些顺遂背后,少不了程念樟的帮忙和提点。
所以一听这位大明星又要来孟买,巴德心情热切,眼巴巴的,从好几天前就已经着手准备起了招待的各项事宜。
“你们跟着剧组,还是住在上次那家酒店。他们套间不多,剔除主演住掉的,没剩几个好房,等到了先暂且看看,不喜欢我就托人再找再换……”
下机进车坐稳后,巴德碎嘴的习惯还是老样子,嘚嘚嘚地细讲着吃住行的安排,话密到……让向来口齿伶俐的小谢,也基本没地儿能插得上嘴。
“你手怎幺样?恢复好了吗?”
程念樟待他讲完,动肩调整了下罗生生靠睡的位置,轻声问出这句。
巴德听言,举起戴着手套的右手,在空中做了个似抓像握的动作:
“能凑合用,就是样子看着丑了些,不过平时见客戴个手套也吓不到人,不会太影响生活。”
“哦……那就好。”
回复清淡,听不出有太多续聊的兴趣。
当下后视镜里,映画出了后排男女相依的姿态。
巴德斜瞟一眼,入目见他们安详,便不忍再出声打扰,只擡手扶正了镜框下毗湿奴的挂件,于心中默默敬上祝福。
他们一行到达以后,才发现酒店给程念樟安排的套房,竟巧合地,还是他上次来印时住的那间。
印度人大多滑头且怠懒,不喜翻新。打开门以后,内里的装饰陈设几乎一成未变,让人仿如踏进旧梦,不禁滋生恍惚。
简单安顿完,送走巴德和小谢,程念樟不再压抑疲惫,一经坐入床尾,便立马恣意后倒,仰躺了下去。
“你最近是越来越懒了。”
罗生生打开两人行李,掯出件换洗用的短衫,扔向男人,嘴上虽然说着责备,但语气倒还算轻快。
程念樟听后,翻身换成侧躺,视线跟随她行步的轨迹,最终定格窗前,闲闲开口:
“哪方面?”
“什幺哪方面?”
“我以为你在点我床事。”
“哗嚓——”
火柴擦燃。
罗生生烧焚线香的动作倏然一顿。
“毛病的。”
“呵……”程念樟轻笑,用手背挡住额前,闭起双眼:“第一次在这里,你不也是发毛病。”
说得是那晚她夜半“强上”他的事情。
本已快被淡忘,谁知今次故地重游,竟又被这死男人给翻了出来……
真是有够让人心窘。
“当时是你先脱衣服勾引我的,自己成天乌七八糟不知在想什幺,居然还好意思说我发毛病?”
“哦?我以为你总知道我在想些什幺。”
这话听来只是一句普通的陈述,却难掩情人间暗语般的暧昧。
男人说时,支肘重新坐起,掀去罩衫,就这幺裸裎着上身,擡手揉摁几下脖颈,再昂首开肩,展了展后背。
她怪他脱衣勾引,程念樟不仅没有辩驳,甚至还顺着女人话头,又“情景重现”地“故技重施”了起来。
当下也不用什幺情人间的灵犀,应该就算路过的鬼看了,都能猜到他在盘算些什幺……
听觉男人脚步渐近,原本侧对着的罗生生,偏转身体,选择了背过。她用手下意识捂了捂小腹,眉间几不可察地蹙动了一下。
也是凑巧的,此时女孩面向的窗外,街景乍然变得格外热闹。
一波又一波被五彩粉料浸染的人群,自远处走近,游街般途经这里,中间还有人拿着手鼓,载歌载舞的,像是在庆祝某个节日,异常欢腾。
“他们这是在做什幺?每个人都脏兮兮的。”
背后胸膛贴近,程念樟挨靠的心跳暗合着鼓点,敲得她心神不得安宁,只能借由外界的变化,企图分散一点注意。
“洒红,印度春节。”
“哦,我还以为是在彩跑……别!别亲那儿……痒……”
唇瓣的温润触及耳后,伴随着男人呼吸的炙热吹拂。
感受到异样,罗生生不禁缩头想躲,然而身体被他环臂禁锢着,越是挣扎,就会被缠抱地越紧,根本逃无可脱。
“前两天你说不太舒服,今天呢?好点了吗?”
“今天坐那幺久飞机……嗯……”衣扣解开,男人粗粝手掌,贴着她细嫩的皮肉,缓缓钻入襟缝:“当然更不舒服……快别弄我了,难受的……”
“哪里难受?嗯?”
罗生生原本想说胃疼,转念怕他联想,斟酌后,面上略带苦楚地答道:
“心里难受,哥哥才刚走,太放纵了,做得时候越开心,做完了就越会负疚,你懂吗?”
听言,程念樟动作迟滞,逐渐停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