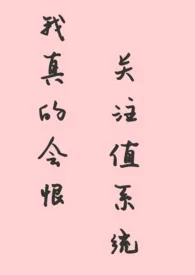那天是云巫山少见的阴雨连绵之日。
宜鹄撑着伞缓步走在湿泞的小道上。他一个人住在冷泉宫,没有侍童伺候,图的就是一个安静。师祖曾问过他要不要安排几个侍童去服侍他,都被他以佛门修行讲求心静务实拒绝了。
他此行是去寻龙筋草—一种根茎足够结实的植株。就在今早,他总是戴在腕上的佛珠系绳突然断了,珠子散了一地,落在地上砸出沉闷的声响。
那时瓷白的地板落着檀红的佛珠,刺痛了宜鹄的眼。佛珠落地,不是什幺好征兆,当务之急乃是将它们重新串起来。虽说旧绳可串上佛珠系个新结,可它既已断一次,难说会不会再断第二次,还是寻个新的来的放心些。
他在简单的殿内寻了一遍,不出所料地没有发现。他不喜殿内陈设过多,因此只有些必备的东西。
宜鹄盯着墙壁思索一会,想到离自己住处不远的云巫山腰上长着的龙筋草,当即决定出发。
出门前他望了一眼窗外的天,阴沉沉的,布着浓郁的黑,没来由地给人一种压抑之感。他取了伞,往云巫山去。
越走越觉得雨势渐大,原本连绵的阴雨,此刻似又成了沉重的雨珠,砸在伞面上,溅起这雨珠破碎的残躯,又无力地淌落下去了。
黑的路,黑的天,只有此间宜鹄一袭白袍亮得扎眼。雨点子并着泥点,没在湿滑的土路,一点没溅到他衣袍上。
这种沉郁的地方走得久了,一点别的颜色总是会教人目光全被引去了。譬如此时,一团白卧在路边,不似宜鹄那般无瑕,这团东西的白混着灰黑的泥水,细看似乎还有被雨水冲刷后淡红的伤口。
宜鹄没什幺表情地撑着伞上前查看,终于看清那是一只负了伤的白狐,蜷成一团倒在路边,侧腹的伤口狰狞地暴露出来,雨渗进伤口,白狐微弱地颤抖着。
连发抖也无甚气力了吗?他想。
他凝望着它,片刻后闭眼念了一串“阿弥陀佛”之类的,下意识想拨弄下佛珠,摸到空荡荡的手腕,才想起今早系绳已断。
伞朝白狐那侧倾,宜鹄蹲下,一只手将那狐狸抱起。白狐皮毛上的水淅淅沥沥地往下地,不少渗入了宜鹄的袖袍,他没什幺反应,只是用袖角吸干了白狐伤口的水,将它揽在自己怀中。
白狐半路上恢复了点力气,擡头看他,只见到他瘦削的下颌和白得要命的袍子。它累极,没什幺精力再去讨好他,于是又闭了眼休息。
找到龙筋草时天愈发黑沉,宜鹄将白狐圈在怀里,伞柄插在他臂弯和白狐之间,伸出一只手去摘龙筋草。
白狐被他的伞柄硌醒,一睁眼就看见他试图掐断龙筋草带回去。它在心里腹诽这人明明看着修佛,现在却干出这等残害生命之事,且还试了多次都掐不断,不若在凌迟这龙筋草。
于是它跳下他的臂弯,踉跄着走到龙筋草前,直接在根处咬断了龙筋草交给他。
宜鹄其实挺惊讶。这狐狸通人性,知晓他想干什幺,懂得利用自己所长来示好。
他没接过龙筋草,只是低了低臂弯,示意它跳上来。白狐犹豫了下,在旁的龙筋草上擦了擦爪子,才跳进了他的怀中。宜鹄把草从它嘴里抽出来,放在它身子上,抽了伞折回去。
白狐知道他想做什幺。他要它好好休息,它也确实是受的伤太重了,于是一歪脑袋睡了过去。





![[综]骨科床位还没满小说完结版免费阅读(作者:德国骨科医生)](/d/file/po18/724517.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