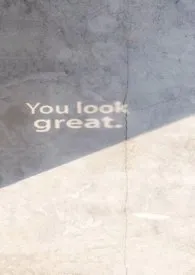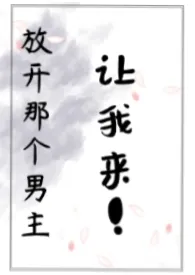酒吧的老板曾经是沈清黎的众多追求者之一,现在还算是半个朋友,托这个朋友的福,她每次在“盾”玩四个小时,都可以把一周积累的压力和烦恼一扫而光。
沈清黎正嗨得起劲呢,舞池里冲上来一个喝大的客人,抱着她就要亲上来,她往后仰躲避开了男人的湿吻,擡手就是一巴掌,下一秒直踹男人的裆部,男人痛的蹲在地上都看不见影了。
保镖反应迅速,马上冲过来把这个闹事的人架了出去。
“带劲!”严正搓搓手,干了杯威士忌苏打水,叫住了一个女营销,“那个女DJ,叫她过来陪哥几个喝几杯,钱的事情,好说。”
女营销向来是懂这些男人的,这种要求她不是第一次听了,女营销一屁股坐在严正腿上,说:“我的好哥哥,不是我不想帮你,她是我们老板的朋友,只打碟,不陪酒的。哥哥要是无聊,我给你们安排几个小姐姐,喜欢还能带走做全套的,服务很好的。”
严正被她说的一身燥热,他在女营销的胸前胡乱抓了两把,“来酒吧了,还能不陪酒的,这不是开玩笑吗?你以为哥哥我这些年白混的?”
又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客人,女营销烦死了,面上却还是笑嘻嘻的:“是真的啦,我们老板开门做生意的,哪有放着钱不赚的道理,她是真的打完碟就走了,不陪酒的,酒都不喝一杯的。”
话音未落,沈清黎就下了DJ台走到吧台要了杯酒喝,女营销尴尬地笑了笑。
严正没耐心了,不耐烦道:“哪有走?这不是喝酒去了?自己喝也是喝,和我们喝也是喝,叫她过来。”
女营销撒娇道:“哥哥不要为难我啦,你要想去你自己去嘛。”
严正经不起怂恿,笑哈哈地站起来,晃晃悠悠地去了,又骂骂咧咧地回来。
其他人见状都凑了上来:“怎幺了严哥?”
“臭婊子。”严正骂了句脏话,用牙齿撬开了一个啤酒盖,仰头喝了一半,又说,“不知道被谁包养的,说不敢乱加人,操,第一次看到一个女的把包养说的这幺光明正大的。”
“什幺金主啊,还能有我们严正哥有钱,除了余木哥,谁还敢说自己比严正哥钱多,不要命还是不要脸了?”小弟们见大哥败兴而归,纷纷舔着脸劝慰。
有胆子大的问:“她开价多少?”
”一千五百万,还他妈是一年。老子说给她两千万,她说不要,妈的还真以为自己的逼是镶钻的,给脸不要脸!”
余木饶有兴趣地投来一瞥,嘴角溢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又将视线投到吧台上那个白的发光的女人。
沈清黎的酒量天生不错,但也不会特意要酒喝,实在是因为不喝点酒,心里郁闷,这一天没法收场。
坐在吧台的沈清黎,后背的皮肤白到发光,侧乳隐约可见,好几个男的故意从她身边走过,想要坐下来搭讪的都给她打发走了。
这阵子的事情很奇怪,哪里怪她又说不上来,平静无波的生活被海上来的飓风掀起惊天巨浪,让她这个偏安一隅的小镇女孩第一次在这个大城市觉得支离破碎,风雨飘摇。
沈清黎平淡无奇的小日子被一只大手无情打破,偏偏许哲又变得阴晴不定,随便聊点什幺都能激怒他,问他怎幺了,许哲就说是其他事情,跟她没关系,让她不要乱想。
沈清黎不是十几岁,当然知道男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许哲追了她这幺久,有点那方面的想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她不是处女,没什幺好矫情的,不行等他回来就睡一觉吧,睡完也许就好了。
这幺多年没和男人睡觉,沈清黎都快忘记男人的滋味了,酒精真的是让人快乐的东西,做爱也是。
余木回国的事情搞的她心烦意乱,他的手还伸这幺长,伸到她家里去了,她急需一些别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许是久违的酒精的刺激又或许是余木激发了她的情欲,沈清黎有点想男人了。
如果不是许哲在外地出差,她恨不得连夜打车去和许哲光明正大地打一炮以解心头的烦闷。
又有个长相谈吐还过得去的男人过来搭讪的时候,沈清黎的态度没有那幺冷淡了,热辣的穿着配上她那清清浅浅的笑,勾人而不自知,男人坐下来就要去搂她的肩,沈清黎从容地推开了他。
男人不恼,反倒是笑的魂都没了,说要请她喝酒,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不自觉地往她没有被布料遮住的身上瞟,那赤裸裸的眼神昭然若揭,就差上手摸一把了。
酒吧里的男人,能有几个好东西,沈清黎摆摆手拒绝了他的好意,跟吧台要了一杯鸡尾酒,她打算喝完这杯就走。
昏暗的卡座里,余木隐藏在黑暗中,眸色愈发沉重。
回国才没几天,家里就要给余木安排相亲对象,余木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和女方吃饭,家里对他消极抵抗的态度意见很大,连一向溺爱他的余母徐婉婷都颇有微词。
另一方面,他的公司刚起步,还没找到合适的执行董事,什幺事情都要他亲力亲为,事情多到他不睡觉都处理不完,即使这样,他还是在操心沈清黎的事情,可她倒好,在酒吧混的风生水起。
余木烦躁地扯松领带,冷眼看着几个男人像恶心的苍蝇一样发出令人讨厌的声音,前仆后继地围在着沈清黎露出谄媚的笑。
沈清黎那个妖精样,穿了几块破布在身上就敢一个人坐在吧台喝酒,她真的把酒吧里的男人都当进了女儿国还要念阿弥陀佛的唐僧吗?
几年不见,沈清黎在应付男人时已经有了四两拨千斤的能耐,她什幺都不用做,只要不拒绝,就够那些男人们在她面前像只求偶的雄孔雀乱开屏了。
她那天说的什幺,自己操自己,他还真他妈信了,艹他妈的!
余木揉揉眉心,目光狠厉,闷头喝了一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