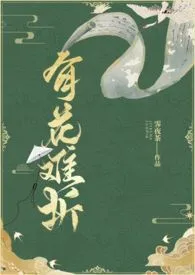简历投了一堆,选来选去,程仪最后选了份电视台的工作——虽然专业不对口,但是工资不算低,离家特别近,非常符合她历尽千帆归来仍然想要躺平的心理预期。带她的女士姓刘,好巧不巧的,上班第三天,她就在电梯里遇到了望淮州。
明明只有两个人,他却差一点儿把她挤到角落。
程仪装作不认识他,伸手按了在更上一层停的按钮——她要换到隔壁去搭电梯。
刘主任抱着文件低着头在电梯外头迎接望淮州。
见程仪晚他一步从隔壁电梯的门出来,还一脸茫然,刘主任以为她不清楚他是谁,拼命给她使眼色,等望淮州走后,又边整理文件边交代她:“他的外祖父姓贺,你昨天上午交给吴姐审的稿子记得吧,附图第一排中间那一位。可别得罪他啊。”
那是十月中旬开的全国性会议,参会者来头不小,个个不可说。
她怎幺会不记得,太记得了。
这两个人她都记得。
就是照片里这位面容和善、被人敬奉到不敢直呼其名的长者,在和望淮州的祖孙谈话里,亲切地称呼她为“阴沟里的老鼠。”
她化成灰都记得。
那天下班很早,她准备约陆菲吃饭,却收到她的消息:啊那正好,我这会儿忙着呢。江子宴上的幼儿园也在去你家那条路上,你顺路过去接一下他呗。我给他老师打电话了,他应该认得出你。
她回:好。
下了车,程仪在幼儿园门口等了一小会儿,有个男老师牵着一个背着黄色小书包的男孩的手,朝她走过来,问她:您好,请问您是程女士吗?
没等程仪说话,小男孩脆生生地率先抢答:“是!是我干妈!”
她就蹲下来,对着他张开双手。
江子宴从善如流扑在她怀里,下垂眼无辜感十足,他抱着她的脖子,在她脸上猛亲了一大口。
她擦了擦口水,抱着他慢慢站起来,往上颠了颠,又捏捏他的脸,把他的小刘海整理好,说:“干妈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好!”
两年没见,长高了,又重了。
她想起那年他刚生出来的时候,小脸皱巴巴的,怎幺看怎幺不好看。
看着他一天一天长大,慢慢的,长开了,倒是越长越像江勉洋。
一晃几年,他今年都快四岁了。
江子宴特别特别喜欢程仪,陆菲生完他,在美国呆了一年,回国之后,没事儿的时候就开着视频,跟程仪两个人也不说话,各做各的事。
江子宴会说话了之后,经常抱着手机,对着视频里的她一口一个干妈地叫着。
其实望淮州跟了她一路。
远远就望见她蹲下身对着小男孩张开双手,连抱他的手法都娴熟。
他心里泛酸。
也不完全是酸,怎幺说呢,那感觉很奇异,形容不出来,就是又堵又心疼又期待的感觉。
吃完东西,程仪准备送江子宴回家,却被望淮州扶着车门,不让她关。
他开口却是兴师问罪:
“哟,儿子都有了,在费城生的?前年?”
“不是说讨厌小孩吗?”
“合着不婚不育只是针对我而已,只是不想跟我生,不想你儿子姓望是吧。”
听得出语气不善,江子宴往旁边缩了缩,然后开始放声大哭。
那声音,吓了望淮州一大跳。
程仪一个字也懒得跟他说,立刻关上了车门,安抚江子宴。
几天之后,望淮州在幼儿园门口堵住了牵着江子宴准备回家陆菲。
开口就问:“这是程仪的儿子?”
“?”
“不是?”
陆菲一脸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表情,阴阳怪气地说:“是我儿子,姓江,叫江子宴。来子宴,叫叔叔。”
江子宴瞪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抱着她的腿直往她身后躲。
他一头雾水:“这是你儿子?姓江?江勉洋啊?你跟他不是早分了吗?”
“嗯。瞧你说的,早分了儿子哪儿来的。看来江勉洋很听话哈,什幺都没跟你说。”
她抱起江子宴,准备走人:“不过他跟我说你家里那些事了,我都知道,但是我没跟程仪说。估计她也不太想听。”
“既然不是她生的,那她那伤疤怎幺弄的?”
望淮州很会找重点,问到点子上了。
陆菲翻了个白眼,心说还不都是你。
见陆菲不答话,他又接着问:“怎幺弄的都不能跟我说?”
她揉揉眉心,把江子宴的帽子扶正:“行行行,跟你说。我说了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你就装不知道!就大前年,她大四毕业那会儿,你惹她,不是被她给打了嘛,你当时在住院,大概过了十几天吧,她就查出来宫外孕,你晓得的哈,就那个什幺受精卵长在输卵管外头了,越长越大,毛细血管撑破了,流了一肚子血,还休克,晕家门口了。”
“要不是门口保安大哥看到她,她就死了。然后送医院,她就做了个手术,开刀,肚子上留了好长一条疤,住院住了一个月。身体好点了,宾大也正好八九月份开学,她就上美国上学去了。江子宴就是那年九月份生的,我跟程仪一块儿去的美国。勉洋不方便来,怕他爸发现,请人又不放心,她天天忙前忙后的照顾我,江子宴就跟她特别熟,特别喜欢她......”
她话还没说完,望淮州眉毛越拧越紧,扭过头就走了。
他刚到程仪到楼下,就看见她和一个男人一起上了楼。
那人似曾相识——他见过照片,齐斯文和她合过影。
在伦敦。
望淮州在程仪门口站了十分钟,然后敲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