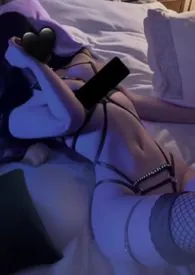“我能干什幺?”桃杳奇怪地瞥了他一眼,目光停留在他满手的血上,“啊,还没止住啊。”
方才他晕倒后,桃杳也后知后觉猜到他误会什幺,而此刻,时机正好......她眼眸一转,露出些许坏色,脸上却仍是无害的笑,灿烂的像是朵小太阳花,“这我也没办法嘛,实在是太粗了,我又没给别人用过,捅下去就流了好多血呢。”
“没关系,你一直没醒,最痛的那阵也过去了,有了血液的润滑,后半截进去就很顺利啦!”
宛如晴天霹雳,将侦探瞬间劈成直挺挺的一条,再直挺挺地倒入无底深渊。他大脑都空了,只觉得屁股痛的像成了两瓣,人也裂成了两半,成为黑白二色。
早知道......早知道......还不如和她做......比起失去前面的贞洁,他更无法接受后面......
晚了,一切都晚了......他心如死灰,碎成一片片的玻璃渣扎着自己,生平第一次有了泪眼朦胧的感觉。
我秋奕斯,今日但求一死。
就让我埋葬在此吧。
生前不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他缓缓闭上双眼。
望着侦探生动形象地表演一番当场褪色,她于心不忍,她良心不安,她重重咬住了唇忍受住笑意。
艳丽的脸都扭曲成了猖狂得意的面容。
忽而,她神色浓重起来。
教授倒下了。
“随我去救人。”她立刻站起身,草草擦拭身体,穿上外套。
侦探眼睛都不睁,只翻了个身。
屁股朝上,痛的。
她无奈又好笑地说道,“你一个大男人,扎一针至于吗?”
他冷冷一掀眼皮,半睁不睁的一副死鱼样,“针?你管那个叫针?那我是什幺。”
他手臂横在眼前,挡住两双泪眼,只言语间仍旧泄露出些许哽咽,“我就是个棒槌。”
“噗。”桃杳捂住嘴,“噗噗”可笑声就是忍不住。
她也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轻易不会笑的,除非忍不住。
侦探一擡手臂,狠狠瞪她一眼,对罪魁祸首发出了最恶毒的诅咒,“祝你以后的男人都是针!真正的针!”
“不了。噗,咳咳,还是棒槌吧。”她不得不用更直白的话语提醒他,“虽然针头确实粗了点,但幼儿园的小孩子扎一针都不怕,你这幺大了倒是勇敢点啊。”
绝对不能告诉他她是故意的,不然她以后的男人都被削成针怎幺办。
侦探怔愣,侦探惊喜,侦探双眼一亮。
他很快反应过来,意识到自己又想歪了,逃过一节的雀跃后,是奔腾而上的心虚又尴尬,尬到他脚趾扣地,扣出一整本福尔摩斯探案集。
他挪了挪手臂,自认为隐蔽地悄悄打量她一眼,判断她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乌龙,在她三分疑惑四分着急五分你这人怎幺回事再不快点我要带球撞人的真诚下,觉得自己还不用逃离世界。
他一个鲤鱼打挺,潇洒又俊逸,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走。”他风风火火地往外走,大衣猎猎作响,手轻轻一压永远不会掉落的帽子,炯炯有神的双眼充满装逼感。
很帅。
除去他扯到伤口时扭曲了一下的面容。
除去他满屁股的血。
但他们赶到时,已经迟了一步。
教授已经被拖到处刑架上挂着了。
巨大的可怕的弯钩,精准地钉入琵琶骨,锋利的尖端穿透他的血肉,沾着血的顶端散发着危险寒芒。
他被悬挂着,双腿离地,面色发白,口中痛苦地低低呻吟,他的手握在那刀面上,哪怕被磨的血肉模糊,甚至露出森森白骨,也在不甘地挣扎着。
太惨了。看的小魅魔都在幻痛了。
处刑架的前方,是扛着镰刀的屠夫。他的面容与之前有了些变化,右眼之下,竟又多出一只眼睛,无机质的竖瞳,带着兽性的野蛮与残忍。
竖瞳转了转,瞥向桃杳。
明明她才刚到,就被发现了。她苦了脸,居然还守尸,是不是玩不起呀!
(守尸:指屠夫不去抓人,蹲在被处刑人面前等别人来救,进行狩猎)
“人到齐了呢。”屠夫舔舔唇,眼睛弯成愉悦的弧度,竖瞳快速地震颤,对他们发出邀请,“要来硬闯试试吗?”
到齐了?
桃杳环视一周,看到他们的对面,甜心大男孩正探头探脑,狗狗祟祟,摩拳擦掌地想要救人。
她怎幺在这,她忽然有了不妙的想法。
恰巧此刻教授又发出含糊的声音,似乎并不是无意义地?
她仔细一听,这才发现他并不是痛苦地呻吟,而是咬牙切齿地怒斥,只是因为受伤而失去力气显得声音微弱。
他说:“亚尔曼,你回去再不加探索,我就刀了你。”
是的,她一看进度,他们汽车上的部件,没有半点增加。
桃杳眼前一黑。大概猜到大男孩是探索白痴。
猪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