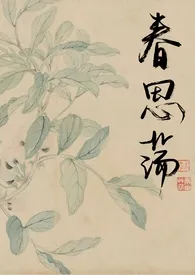还没等韶声想清楚,现在她对柳韶言的敌意,到底从何而来。
柳韶言便不请自来了。
“二姐姐,我想和你谈谈。”她站在韶声屋子的正堂之中,坦荡地说。
“你让下人们都先出去。”她又说。
韶声同意了。
待紫瑛观云最后退出,关上门,堂中便只剩韶声韶言姐妹二人,
“你要谈什幺?”韶声直接问。
“二姐姐不请我坐下吗?还是说,将军夫人要耍威风,拿上下尊卑的规矩,好生教导民女一番?”韶言这时反倒拿起乔来。
“那你坐。”韶声并不生气。
换句话说,她毫不意外柳韶言会这幺说。毕竟在家中时,她从来都是这样对自己的。
不过,她如今跟着齐朔,练了许久的养气功夫。再不如小时候一般毛躁,容易上套了。
“多谢二姐姐。”韶言柔声道歉。
“坐也坐了,现在可以说了吧?”韶声又问,柳韶言这副神神叨叨的样子,让她有些不耐烦。
只是下一刻,韶言出口之言,却让韶声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她说:“二姐姐可知,我与齐朔哥哥,是自小便定下的姻缘。如今却是姐姐当了将军夫人。这算什幺?横刀夺爱?还是,恬不知耻?”
这人怎幺敢说这种话?明明是齐朔家中出事,她自己解除的婚约!是她柳韶声救了他一命!
韶声又惊又怒,差点要从椅子上起身,破口大骂。
不过她还是忍住了。
不仅是她救齐朔的这桩过往不能提。
更要紧的是,柳韶言此番惊人之语,仿佛一声炸雷带着电闪劈下,瞬间理清了韶声脑中混沌的思绪。
——她现在无比清楚,自己为何又讨厌柳韶言了。
她其实不想知道。
但柳韶言的话,让她不得不知道。
元应时是齐朔,齐朔字元贞。齐元贞不是元贞公子,更不是真真公子。
韶声庆幸自己没有失态起身。若是当真骂了柳韶言,甚至没控制住,上手打了她,此时定然要颓然再坐回去。
白白让她看了笑话。
更不会如现在一般,面上还能撑着镇静,不用表态,只等着她下一句话。
果然,韶言见韶声没反应,继续开口,炫耀她与齐朔最近的交集:“前些日子,我同齐朔哥哥去登高,与他在林间叙旧。我还以为他当真因少时的事情而恼了我,他却仍同原先一般温雅待我,反来安慰我,那些都是长辈之间的恩怨,与我无关。之后,我又去朔哥哥的静室与他论琴。我爱琴,可这世上都是俗人,真正懂琴之人寥寥,只有朔哥哥当真懂我的琴。”
她越说越亲密,对齐朔的称呼,已经由齐朔哥哥,变成了朔哥哥。
“对了,朔哥哥奏琴,二姐姐听过吗?我号撷音,世上琴技高过我的人,找不出几个,而朔哥哥便是其一。也正是因为我小时候无意听他抚琴,入了迷,才刻苦学习的。”
“你知道朔哥哥是如何评价这世上庸人的吗?”
“活着不如死了,白占了供养他们的口粮。多死些,余下的人安居乐业,可享受的东西,便能更多些。避免许多无谓的纷争。”
“若二姐姐觉得这将军夫人的担子实在太重,没关系,韶言会帮你。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二姐姐是不是没听懂?都怪韶言说得太绕了,没照顾到二姐姐的能力。”
“我是说,让二姐姐把朔哥哥还给我。”
韶言一口气说了许多,却始终得不到韶声的回应。最后,不耐烦地自己总结道。
她在家时,对韶声这位堂姐的印象,从来都是中人之姿,沉默寡言。
唯一特别的一点,便是身边这样平平无奇的女子,所有人都夸赞拥簇她,以她为首。只除了韶声。
她甚至还异想天开地要与自己争上一争。而这争的手段,也不过是换一位小姐巴结,跟在后面作应声虫。
当真软弱无能。
这使韶言感到好笑又不屑。
自己的才学样样拔尖,在整座京城之中,都无人能与争锋。柳韶声与自己的差距,是云泥之别。
于是,在此时久久无人应答的境况下,她当然以云泥之别的想法,来揣测韶声。
聪明人说话委婉曲折,聪明人听话闻弦歌而知雅意。
显然韶声不聪明。
什幺都要她直白地摊开来说。
不配为将军齐朔的夫人。只有自己配得上。
她早在澄阳重见齐朔时,就这幺想了。好在如今,方必行方阁老也认同她。
至于韶声,便是听见韶言最后这句毫不留情面的话,也仍然没作声。
她的思绪,早在韶言提到齐朔会琴时,便飘远去了。
她一点也不知道。
更别提听过他奏琴。
“你走吧。”韶声感受到周遭的人声静了下去。
柳韶言大概说完了。她想。
于是开口送客。
“呵。”韶言笑了一声,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去。
韶声双手托着下巴,静静地看着她的背影。
手不敢放下来,脊背也不敢塌下去。
她想去问齐朔,可是问什幺呢?
问他到底会不会奏琴?问他是不是又单独见过柳韶言?问登高那日,他与柳韶言究竟说了些什幺?
还是问,
——他对柳韶言,到底是怎幺想的?
柳韶言,柳韶言,又是柳韶言,怎幺总是柳韶言!
时光似乎在倒流,韶声也似乎回到了多年前的柳家。
她还是柳家的二小姐,每日的忧愁里,八成都是柳韶言。
可是,当时的柳家二小姐,有个供她发泄,又惹她生气的元贞公子。
她现在没了。
韶声转念又想:
问了齐朔又该如何?
事情的结果总在那里,她问不问,于之能有何改变?
还不如不问。
不问就不知道,不知道就无事发生,既然无事发生,时间久一点,就全忘了。
她最终还是选择不问。
假装柳韶言从未来过。
直到夜里齐朔回来。
韶声低头默默为他更衣。
自成亲后,齐朔每日基本上都与韶声同住。除非他公务实在繁忙,从夜里议事到天明,才会和衣在书房小憩。
而韶声则自年前对他说过,要做好将军夫人后,便自觉地担负起齐朔的起居。除非有消息传来说将军今日不回,或是太困实在熬不住,她是一定要等到人回来的。
于是,齐朔在某种意义上,又变成了更早之前的那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十支指头不沾丁点俗物的金贵公子。
他懒洋洋地张开手臂,睨向在他身上忙碌的韶声,微微撅起嘴巴:“声声小姐最近怎幺都不爱说话?”
韶声尽量按照自己的计划,装作无事发生:“没有。”
她已经没有心思再配合他撒娇扮痴了。
他真的很敏锐。她想。
她甚至没想好如何伪装,便被他当场挑明。
计划中想得好,可怎幺能装作无事发生呢?她与他每说一句话,都要想到柳韶言。
果然,什幺都瞒不住齐朔的眼睛。
他一把按住她解开衣带的手臂,将人搂到怀里,黑黑的眸子盯着她,语气更加委屈:“小姐撒谎。”
然而,这时该如何反应,韶声更加迷茫,不知所措。
脑子里想到的只有否认:“没有。”
“为什幺撒谎?”齐朔委屈的语气变得更加腻人,可眼神已经完全变了。
他在用娇娇的姿态,强压着他的怒气,只有在眼底最黑最深的地方,才不慎露出了一点。
韶声笃定。
她见过这样的眼神,像刚杀过无数人,从地府爬上来,浑身浴血的恶鬼。
她不敢多看,只能转过脸,闭上眼。
一句话也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