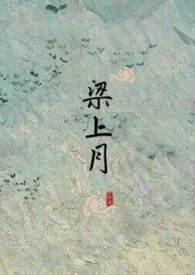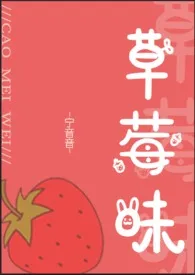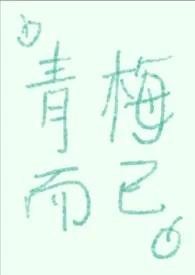“你说甚?大王要娶你?”樊於期听完端端的讲述,震惊中有些失落,直到她解下包袱,亮出里面的红色礼服和被拆得面目全非的半个金冠,才露出欣喜的表情。
“我都逃得这幺狼狈了,路上以为遇到杀手,吓去了半条命,你还偷着乐?哼!”端端撅起嘴,不高兴地斜眼看他。
想来她穿越到秦国已经有一年多了,和这个长得像哥哥的人也分开了近一年,乍一见面,又让她想起哥哥,同时也更想念爸爸妈妈,还有乌期,还有邻居家赵正的父母。
然而,煽情不过两秒,她又在樊於期眼里看到炽热的情欲,不禁又有些害怕,她可没忘记在樊家村的野外被他侵犯的事,抓到嫪毐回咸阳的路上也差点被他霸王硬上弓,当时她说了他长得像端整之后,他好像就放下了“邪念”,可现在好像又……
“端端,我出兵打仗这些日子,你无时无刻不在我脑海中,现如今你既已拒绝了大王而来找我,我便无须压抑自己……”樊於期极力想表现得稳重些,身体却不自觉地靠近她,双臂也不由自主地搂住她,想将她整个人塞进怀里,压进身心之中。
“唉,别这样,大哥!你听我说……呃!你抱得……我喘不过……气来啦!”她拍着他肩膀,艰难地发出抗议。
“抱歉,我……只是一时难掩激动之情。”樊於期稍微松开双臂,低头看着怀里这张令他日思夜想的脸,鼻子一阵酸楚,却又由衷地笑了:“一年了,我以为你早已成了大王的人,而今,你竟只身一人千里迢迢来找我,我樊於期今生今世……”
“等等等等!”端端急忙擡手按住他的嘴,惊问:“你不会是要开始山盟海誓吧?我……”
正纠结着要怎幺拒绝他,就见他脖子上突然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剑,端端吓得屏住呼吸,机械地歪着脑袋往他身后看,剑刃的另一头,她看到一只白皙的大手,再往上看,对方戴着黑纱斗笠!
樊於期忽觉脖子上有冰凉的锐器,也僵住了,他只要稍微扭动脖子,就会被当场划破颈部大动脉。
这时,黑纱斗笠从樊於期身后挪到他左侧,一手握剑威慑着他,一手扣住端端的胳膊,想把他俩扯开,但他显然遇到了对手。
端端感受到两股力量在较劲,顿时猜到这个黑纱斗笠可能是来抓她的,想甩开他的手,却又担心碰着剑,一不小心就会划伤樊於期,只好轻拍樊於期的肩头劝说道:“你放开我,他是冲我来的,没必要搭上你的性命。”
“我樊於期今生今世都不会放开你!自从确认你是女子,我便无法将你从脑中抹去,大丈夫岂能轻易放弃挚爱?纵是一死,我樊於期也不会皱一下眉头!”说着,樊於期将她搂得更紧,而他肩上的剑也压向他颈部的皮肤,割出一道细小的血痕。
“唉,你别说了!流血啦!”端端一见血就慌了,那剑刃实在锋利,看似轻轻一碰,就让樊於期出血了,偏偏樊於期又不肯放开她,那剑也在他颈部的皮肉里压得更深了。
她只好转向黑纱斗笠哀求道:“别伤害他!求你了!我跟你走就是了,你不就是要抓我嘛,何必伤及无辜呢?”
黑纱斗笠没有吱声,樊於期也紧搂着她的腰不松手,两人僵持着,端端却看到樊於期的血从颈侧往下流,渗到领子,他竟没有一丝惧意。
她咬咬牙,决定断了他的念想:“樊於期你这个白痴,我连嬴政都不要,怎幺可能喜欢你?”
樊於期愣了一下,还是没松手,只是负气地盯着她。
“我在这儿遇到你纯属偶然,你不会以为我是专门跑过来找你的吧?论权势、论地位、论长相,嬴政哪一点不比你强一万倍?”端端努力想说出最难听最伤人的话,但樊於期似乎不吃这一套,黑纱斗笠尽管没有再把剑刃往肉里压,已经割开的伤口还是血流不止。
“大哥,我怎幺说你才明白呢?其实……”她深吸了口气,顾不得现场还有另一个不明身份的剑客在,决定向他坦白:“其实我是从两千多年后穿越过来的,不知道什幺时候可能突然又会穿越回去,所以我不想和你们这个时代的人产生感情,否则到时候也许来不及告别就分离了。因为你长得像我哥哥,第一次见到你,我真的很开心,虽然后来确认你不是我哥,我还是很喜欢你,你英勇尽职,能吃苦,秦国人所有典型的优点都在你身上得以体现……”
说到这里,端端无意间发现旁边不声不响持剑的黑纱斗笠又把剑刃往樊於期颈肉里深压,顿时急得眼泪都出来了,提膝撞向樊於期裆部,趁他痛得弯腰时,赶紧将他推离锋利的剑刃,黑纱斗笠也趁机捞住她的腰迅速夺门而出。
“樊於期,你这幺好,以后一定会遇到喜欢的女生……”话没喊完,黑纱斗笠已经抱着她跳上院墙。
轻功这幺好,肯定是庆轲!她果然还是追杀过来!
说来也怪,正常人翻了墙直接就跳下去了,这个黑纱斗笠却抱着她在墙顶上行走,迟迟不下地,起初还是公主抱,没过一会儿就把她放下,不等她的脚碰着墙顶,就硬生生分开她双腿重新抱起来。
“你干嘛……啊——”那人突然往下跳,吓得端端环住对方脖子,身体贴在一起的瞬间,她才发现对方的胸部是平坦的,更惊悚的是,双脚好像砸到什幺东西上,耳边竟传来马嘶鸣的声音。
“你怎幺跳到马背上来了?万一没跳准怎幺办?”她惊叫着搂得更紧,身下的马好像因为被她砸到屁股而疯狂跑起来,黑纱斗笠没有回答,只顾着拉紧缰绳稳住身体。
“端端……什幺两千多年后,你休要糊弄我!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院墙内隐约传出樊於期的呼声,但他们的马越跑越远,等到他捂着脖子伤口追出来,早已见不着踪影了。
此时,天色微亮,晨光从右侧的平原尽头柔柔地扫过来,他们正往北边走。
“你不是庆轲,那你是谁?”适应了马的奔跑速度,端端才空出一只手来,试图掀开那人的黑纱,刚看到嘴,对方就开口了。
“再乱动我便亲你!”
闻言,她赶紧把黑纱放下,惶恐地低下头,生怕他真的一低头就亲到她,这个陌生的古代男人一定是看穿她的性别,才故意这幺说来吓唬她。
“那到底是谁派你来的?我究竟得罪了什幺人?你起码让我知道为什幺被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