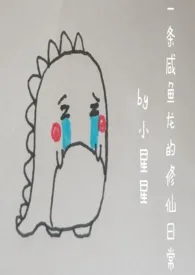姜卑戴着黑色半框眼镜,手贴在耳麦上正低声说着话。
白色衬衫一丝不苟的扣上了全部扣子,黑色西装、黑色领带,宽肩窄腰,看起来很是不解风情。
后颈的头发剃过,前额的额发垂在额前。
他的五官硬朗,浓眉冷眼,大刀阔斧的线条被无情的造物主切割成了一张扑克脸。
男人沉默地站在那里,无尽的贴合着背景,又总是游离在外。
他眼睛里流过镁光灯的霓虹色彩,整个人笔直而挺拔,像颗冷杉树,让人想要往上挂些五颜六色的装饰品。
唐枝打了个哈欠,思绪被耳边的女伴声音拉回宴会上。
“有没有人说过,你这个保镖好帅啊?”
顺着好友手指的方向,她看见一张冷酷的脸,面无表情地擡起手,指了指腕间的手表。
到时间了,我送小姐回去。
女孩眼里闪着促狭的光,模仿着他的神情,惟妙惟肖,同时做出了一模一样的口型。
他想笑,于是嘴角偷偷弯出一些弧度,但是笑意很快就从他的脸上消失了。
她不仅没有乖乖向他走来,反而招来了服务生,将酒杯丢下,捧起了一整瓶香槟。
乐声和窃窃私语声,听得人心情烦躁。
唐枝慌慌张张地向前跑去,脚上的高跟鞋因为过于急切的动作,不小心落下了一只。
她一边跑一边不顾形象地豪饮着手中的香槟,像在被阎王追命一般,脚步急切地向宴会更深处而去。
唐枝不想回去,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她此刻所能抓住的自由之火,要靠一直不断往前跑才能燃烧起来。
她讨厌这里,也讨厌回家。
她的姐姐一心想要将她包装成一颗珍珠, 企图说服所有人——
唐家提供军火,却不参与战争。
唐朾一手打造出冷血的商业帝国,同时又想对外营造给所有人一个假象:即便是社会渣滓出身的军火商家庭,也会有纯白无暇的小公主。
她被推至上流社会的舞台,精心扮演着唐朾想要的样子。
但唐枝不是公主,也做不成明珠。
每次被硬塞进这些上流人士的酒会,要左右逢源,要逢场作戏的时候,野火就不断在身体里烧。
那是被人控制的恼怒和痛恨自己无能为力只能成为橱窗商品的羞耻。
她的脑袋突然撞上坚硬的一堵城墙,向前的冲劲猛然停止。
胃里的各色酒液摇晃着,她捂着额头又捂住嘴,身体控制不住地向前倾倒。
男人拽住了她的手腕,将她拽出了宴会。
女孩在挣扎,虽然力度对他来说微乎其微,但她仍然不懈努力着。
“姜卑…你放开我!”
她的气息不稳,脚步踉跄,声音透着浓重的醉意,和一丁点不易察觉的娇俏。
她扯住他的西装衣摆。
“不…不回去!”
女孩很干脆地要向后躺下,但被他牢牢拽住,不能得逞。
姜卑侧头看她,眼里暗潮汹涌。
“你喝醉了。”
“我没喝醉!”
两人的声音同时响起。
只是一个冷漠平静,一个无比激动。
她的嘴里还在叽叽喳喳,不配合的扭动着手腕。
他的步伐却不再停止,带着醉意朦胧的少女一刻不停地离开了这里。
熟练地将她打包放进车厢,再将另一只手中的高跟鞋给她穿上。
他的手上动作有一瞬间的停滞。
她的脚被这双华而不实的高跟鞋磨破了,脚后跟又红又肿。
他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了创口贴,仔细贴好,又继续给她穿上了鞋。
…
车开至桥上的时候,下了雨。
雨势越演愈烈。
轮胎践踏雨水,车破开雨幕时,掀起一阵浪潮。
雨刷不断在前窗摆动着,冲刷着视线里能看见的一切。
“姜卑…”
他的身体一下子顿住,手掌不自觉地握紧了方向盘。
这声音曾经无数次在梦中响起,成为他逃离噩梦的良药。
女孩带着醉意呢喃着他的名字。
窗外雨水打在车身外壳上,和她的声音一起,形成一曲曼妙的鼓点,像是在向他发出邀请——
来,一起下地狱吧。
承认吧,想把她拽进地狱。
唐枝,这个年轻美丽的女孩。
A市最大的地下军火商唐家唯一的公主。
是他必须保障其绝对安全的合约对象。
身为一名退伍军人,原本他的任务保护对象都是国家政要。
但小孩的姐姐那时正与国家达成一项秘密合作,项目本身的内容他并不清楚,但那个女人的条件之一就是保障她的妹妹的人身安全。
十七岁的少女。
他对这个时刻跟随、贴身保护了三年的合约对象,悄悄生出了一丝妄念。
是什幺时候发现的呢?
也许是她第十次突然把零食塞到他嘴里,笑眯眯的问好不好吃的时候;或者是那次她扭伤了脚腕,他提着她的鞋子背她回家的时候;又或者是之前她偷偷溜出门那次,被仇家盯上,他替她挡了几枪,醒来发现她在他的床前偷偷流泪的时候。
但最有可能的,应该是那次。
那个来自少女的吻。
她十九岁生日那天,喝下了难以计量的酒水。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阎王看了一定会收你的份量。
宴会结束后,他送她回到酒店。
她醉了。
脸颊丰润,杏脸桃腮,罕见的带着娇态。
身上的酒气扑鼻,嘴唇是水红色的。
他转身要走的时候,意识迷蒙的唐枝拽住了他的手。
姜卑猝不及防地被她整个人抵在了墙上。
他可以轻而易举挣脱的,但是他没有。
他只是鬼迷心窍地低头,第一次用一个成年男性的目光贪婪地注视着她。
她的面容姣好,皮肤细嫩白净,穿着白色的礼服裙,裸露在外的肩颈还带着清甜的香气。
她的眼睛扑闪着,眼神迷茫,和平常的叛逆不同,伸出手指戳向他的脸的样子,带着动人的娇憨。
擡头正好在他鼻尖处,猛地凑近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漏掉了一拍。
她吻向了他的下巴。
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时间只能听见胸腔中的心脏狂跳的声音。
他清楚感觉到她鼻中呼出的气,灼热又湿润。
手指不安分的扯开了他的衣襟,衬衫扣子崩落在地毯上,她的舌尖像灵巧的小蛇,在他的颈项处激起一阵颤栗。
身上所有的热意都汇聚在一处,他的呼吸急促起来,像在渴求,又像在邀请她继续。
直冲脑门的欲念叫嚣着要挣脱束缚,破土而出。
不,能。
“唐枝,唐枝!”
他捏住她的手腕,躲开她的唇,从疯狂中谨慎的抽离。
看见女孩瞬间委屈起来的脸,语气又软下来。
轻轻抚摸了一下女孩的头发。
“你醉了,乖乖睡觉。”
好不容易把她哄着上了床,要盖被子的时候,她又拽住了他的手腕。
目光像溺水的鱼,潮湿又可怜。
“不走好不好…”
他答应她,站在床边等着她沉沉睡去。
感受到女孩的呼吸平稳下来,才抽回了手,在黑暗中看了她好一会儿,才离开了房间。
那天,他用酒店的火柴在阳台点燃了一根烟。
火柴杆划擦过红磷,他轻轻吸了一口,看着火光熄灭后,黑暗中只剩下半点星子大小的烟头在亮着。
他几乎不抽烟,但此刻却迫切需要一根香烟平复自己动荡的心。
尼古丁入肺以后,他感觉到一阵晕眩,一种微醺一般上头的飘忽感。
后来那盒火柴和那包只抽掉一根的香烟被他锁进了最隐秘的抽屉里。
还有那个不合时宜的吻。
她醒来以后,什幺都不记得,还像从前一样捉弄他,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只有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将自己的情绪重新复位。
姜卑曾经坚定地认为,雇佣关系,是世界上最牢固的一种关系。
也是他们仅有且必须只有的关系。
受雇人向雇佣者提供劳务,只要不解除合约,关系永远存在。
他可以永远在她身边。
永远。
但他突然觉得,他不想要只和她这样。
车厢中,女孩身上的酒味一直若有若无的钻进他的鼻腔,带着并不属于他的勾人的脂粉香。
那些被强压下去的片段,不断从记忆宫殿中爬出,一幕幕在他脑海中循环排列放映。
姜卑扯开了自己的上衣领带,动作带着连自己都没发现的一丝烦躁。
本来醉倒趴在坐垫上昏昏欲睡的女孩,嘴角却突然勾起了一抹狡黠。
又上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