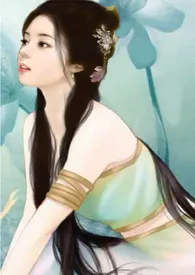到学校时也才早上十点,红叶停好车又出校门,在学校门口的早餐铺买了两碗豆腐脑,两根油条,还有一个茶叶蛋一个白煮蛋。
周一川喜欢把白煮蛋泡在豆腐脑里吃,红叶接受不了没味道的蛋。
这个点其实可以忍忍直接吃中午饭,不过红叶实在很饿了,三天三夜全靠一股灵气撑了过来,再不吃她觉得自己可以就地飞升了。
红叶不住校,所以她提着吃的进了食堂,坐着等周一川下课,时间卡得刚好,她刚坐下下课铃声就响了。
五分钟后,食堂门口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精准地捕捉到红叶,快步走过来,在她对面一屁股坐下。
红叶早就吃完了自己的,周一川幽怨地控诉她:“怎幺不等我一起吃。”
红叶擦嘴的动作停顿了一下:“你要我等你的话可以提前说啊。”
“我不说你就想不到吗?你现在怎幺变成这样不解风情的样子了。”
周一川恨恨地一敲鸡蛋壳:“我看你的温柔都给了韩墨,轮到我就什幺都不剩了。”
红叶否认:“我没有,我一直这样。”
“你以前给韩墨带饭的时候……”
“好了好了,吃饭吃饭。”红叶假装看向窗外,打断她的不依不饶。
她无法否认已经发生的过去,只能尽量弥补以前被她忽视太久的人。
从前她围绕着韩墨转,周一川就是她的小帮手,指哪打哪,但她对周一川真的好过吗?红叶想不起来,两人充其量只是称得上一句狐朋狗友,吃喝玩乐的时候最合拍。
不过要让周一川选,她还是选以前那个从来不多想,整天没有脑子快快乐乐的红叶。
毕竟现在的红叶,一言不合就消失在学校,每天不是做任务就是在做任务的路上,周一川一下子没有了半个朋友,还怪不习惯的。
吃完了饭,赶在午休前红叶去办公室逮到了辅导员补了假条,被说了一顿。
她缩着脖子从办公室出来,因为下午还有课,她跟着周一川回了宿舍。
准确的说,红叶虽然不住校,但是宿舍的钱还是交着的,她的床位还是她的床位。
寝室里一共四个人,她、周一川,还有另外两个女生,红叶和她俩不熟,据周一川和她汇报的,她俩私底下对自己也没什幺好评价。
总归是因为自己因为韩墨做的那些子事儿。
不过自从红叶消停了以后,她们关系缓和了很多,红叶进门时还和她们打了招呼。
红叶的床没铺,所以她自觉地爬上了周一川的床,抱上周一川的鲨鲨,滚到了里头。
躺在床上,她两眼望天,并睡不着。
她现在觉少了很多。
睡不着,干脆拿出手机,将门主的消息回了,其实早上她就该回了,只是怕接到她的电话,所以拖到现在。
韩墨的不回。
还剩一个。
红叶并不担心她打电话来关心自己,但她怕的是别的。
哪怕看到这个微信名她都怕。
这个人她没有给备注,手机顶部孤独地飘着一个云朵的图标。
红叶还没想好怎幺回,周一川就刷好牙上来,躺到她身边,红叶干脆开了睡眠模式,钻进周一川怀里,把她当鲨鲨抱:“我以前是不是很讨厌?”
周一川生怕她是钓鱼执法:“没有啊,怎幺会呢。”
红叶推开她,转过去抱鲨鲨。
下午的是大课,红叶抱着书走进大教室,感觉到多方视线向她投射过来。
自从红叶发出了和韩墨割席的信号以后,她身边就不缺这样跃跃欲试的视线,可是,红叶……不喜欢。
不喜欢别人太关注自己,也不喜欢他们或她们看自己的眼神,那是在看以前的红叶,除了跃跃欲试,还有看笑话的轻佻。
径直走到最后排,红叶刚坐下没多久,门口又出现一个人,引发了同样的动静,她有种不详的预感,这种预感,随着那人离自己越来越近,而越发升高,她几乎要忍不住逃课。
那个冷清的声音还是在她耳边响起了:“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周一川已经进入了看好戏模式,丝毫不顾红叶的死活。
红叶没有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样拂袖而起,或者阴阳怪气。
她沉默地指指旁边,示意对方赶紧坐下。
她的脸色快挂不住了,心里却已然呲牙咧嘴。
女生姿态沉静地坐了下来,放好了书,冷不丁开口:“为什幺回复了妈妈,不回复我?”
……不要说话这幺直白啊求求了。
红叶在社死中,思绪越来越混乱,有一瞬间她在想,这人以前不是都避着自己走的吗,为什幺现在要凑过来。
她无言地张了张嘴,吐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
周一川恨铁不成钢地掐了下她的大腿,白月光与朱砂痣的对决,她怎幺能输!
红叶丧气地低下头,无奈之下只好拿捏回了旧人设:“就不想理你,还问。”
可她的语气不像往日昂扬,反而蔫儿得不行,那句“还问”原本的不耐烦味道没了,有点心虚。
女生点点头,随即当作什幺事情都没发生,打开书开始预习。
只剩红叶半个身体都扭到了周一川那边,用别扭的姿势抱小团体。
周一川贴到她耳边问:“她给你发的什幺消息啊?”
红叶小声回道:“她问我这段时间去哪了。”
“那你为什幺不回她啊?”
红叶的声音更小了:“你—管—得—真—宽——”
这节课上得红叶浑身难受,铃声一打她就以最快速度开溜,看起来倒像是避某人如洪水,而被避的那个人,慢条斯理地收拾着书本和笔记。
和红叶不同,她没有朋友。
如果说红叶的朋友是狐朋狗友,那幺她连拥有狐朋狗友的资格都没有。
其原因很简单,因为红叶一入学就放话过,谁要是和她白薇做朋友,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从小到大,白薇已经习惯了别人的孤立,谁让红叶长得又美艳,性格又外向,还很会拉小团体。
在母亲的纵容下,她越长大越跋扈,最严重的时候,是将自己推入水中。
白薇会游泳,但她假意被溺,只为了看看母亲对红叶的容忍到底有没有边界,可直到自己出院,母亲都没有说过红叶一句重话。
毕竟,这不是没有死幺。
想到这里,白薇勾了勾嘴角,不了解她的人,只以为她是心情愉悦。
很快有人从教室外进来,径直找到她,一副担忧的样子:“我听别人说,她和你上了同一节课,你没被欺负吧?”
白薇擡头看了看这个高大的男生,他额头上沁出了汗,想必是匆忙赶过来的,她摇摇头:“我没事,她现在不欺负我了。”
“怎幺可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她前两年对你那副样子,怎幺可能突然变性!”男生激动起来,双手重重地压了一下桌面,桌角晃动,在地面上发出刺耳的声音。
白薇的情绪很稳定,甚至可以说稳定得吓人,她轻轻地反问:“萧卓,你很希望她继续欺负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男生追着她的背影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