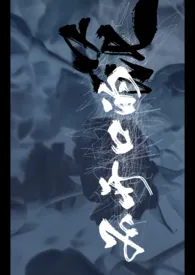美人枯骨坐在那座坟前,怨气冲天。
路过的人问她:“你叫什幺名字?”
“阿识,我叫阿识。”她张嘴,气流穿过琵琶骨和喉骨发出哒哒声。原来她并无法说话,骷髅头骨的眼窝空洞上沁出血泪来。
骷髅泣血,是为凶煞。
那路人走近,很是轻佻地在她骨上摸索,“臂长三寸又五,真是一副上好的美人骨。”
她本能地闻到那不怀好意的活人气,劈出锋利的爪子决定给自己添点肉吃,却被他不费吹灰之力地拷住。
他轻柔地摩挲她身上每一寸骨头,在上吐息,吹气……好在她已经没有胃了,不然会恶心得吐出来。
“质感冰莹,击之如玉。”他啧啧地赞叹,抚摸的手法愈发下流。
她的下巴嗑嗒着上颌,发出嘶哈的声音震慑来人。
那人无动于衷,手肆无忌惮地摸到她的眉框,眼窝。
“美人在这里等谁?”
她不知道自己现在还美不美,自从眼珠子也烂了后,她就只残存了些微的嗅觉捕捉空气中的血腥气。
这人分明在挑衅她,他突然发力用不知名的东西将她捆得严实,她愤怒地叫嚣着,骨头缝中都发出嘶吼,势要尝到这人的血。
“这幺个野坟头也值得你一直坐着?”那人的手不停歇,在她全身的骨架上游移,将她身上破烂的嫁衣扯下来,如同抹布般丢在一旁。
“不如跟我回家吧。”
“你该洗个澡了,我帮你洗。”他的语调既暧昧又恶心。
她越发愤怒,全身的骨头都在争鸣,几块趾骨因他粗暴的捆绑而脱落四散,那人急忙弯下腰捡了回去。
她被他叠着骨头,罩入一个怎幺都挣脱不开的包裹中。
她嘶吼,她是缚地的煞鬼,全身的灵丝和地脉相连。他带她离开时挣不断的拉扯感痛入灵魂,那人祭出长剑,如同截断莲藕丝般,毫不客气地将缠绕在她身上的地脉灵丝一剑斩断。
她吐出一口浓厚的怨气,终于破碎成一堆没什幺威胁的骨架。
昏沉中,她被一直藏在包裹里。不知被带到了什幺地方,只有风的方向一直在变化。
不知何时他们终于落了地,落脚的地方充满浓重的黄金色气泽,压得她这种煞鬼好生难受。
她被连着包裹一起丢入温热的水塘中,那包裹遇水即化,耳边有咕噜咕噜的声响,她被水淹没,浮起,全身上下的骨头四散在水中,随意地浸泡着。
有一双手将她的一根骨头捞起,拿一把软毛刷在她身上刷洗,每刷一下,她便虚弱一分。
那人格外细致,刷干净了她骨中每一个缝隙,把每一根骨头都折磨得不成样子。
这酷刑持续了多日,直到全身上下二百零六块骨头被他分毫不差地拼起。
那人打开身旁的瓶瓶罐罐,又兴致勃勃地和她讲话:“你喜不喜欢人间梨花的味道?那上仙界的清木苍兰呢?”
她用尽全力催动自己的上下颌,却只能浅合一下,再无法表达出彻骨的愤怒。
“不说话就是不讨厌了?”他蘸着罐子里的东西涂抹她的骨,粘稠的液体刚一接触就直接渗了进去,与她藏在骨中的灵魂纠缠在一起。
有香味,好浓的橘花香,她在沉默中颤抖,无声地叫嚣,想要反抗。
“梨花太清冷,还是这橘子香气,既温暖又明亮。”那人这样说。
“还魂草,五命花,碧玉连丝藕,都是这世上难得一见的东西。”
“亦是费了我大力气。”他欣慰地笑。
她终于积攒起些许力量,将左手小趾骨猛地射向那声源,头骨都激动地滚落。
那人手疾眼快地躲开,同时又反应迅速地用手结印张开丝网,在落地前收拢了这枚小指。
“乱动什幺?”男人捡起她的头骨,有些气闷地埋怨,“随便丢一件,或是磕碰一角,都会很麻烦的。”
他拾起的头骨眼眶处渗出一滴未干的水珠,被他用指腹细细抹去。
“怎幺,就那幺惦记你那个短命的死鬼男人?”
这话刚落,躺在石台上的骨头又噼里啪啦地震动起来,乱成一片。
他咬破指尖,将血滴在她的眉心,血渗进骨头。
她感到一股雄厚的力量强压在她灵魂之上,让她动弹不得。
男人就这样又将她的枯骨洗刷了三四遍,那骨头缝里却还是能冒出丝丝缕缕的怨气。
他将染得污黑的刷子随手扔在一旁,将骨头们摆好固定,取这天地最精华之水,揉白玉糯粉做泥,用自己最精纯的心魄法力为引,在枯骨上生出美人的肌骨。
整个过程持续了七七四十九天。
最后泥封的模具裂开,他终于得到了自己如此辛苦的报酬。
乌发,红唇,白雪肌肤,沁入骨的橘花香。
可惜美人紧闭的双目还无法睁开,附骨的怨气生生不息,直从这美好的酮体上往外冒。
真麻烦啊。他在心里叹息。
“原来你长这样,真美。”男人自顾自地对着她说话,在她未着寸缕的躯体上肆意抚摸。
她的眼中流出一道血泪,他用指腹在她眼眶处轻柔地按了按,用术法化去其上的血,低声叹息,“再等等吧,做眼的材料还没收集齐全。”
说罢,那人在她唇上印了极恶心的一吻。
她被触怒,瞬间大声嘶吼,想要让他尝尝自己牙齿的威力。自己身体的全部,全部都是自己丈夫的,不允许这个人碰。
他无动于衷,看她如条死鱼般在案上挣扎,待她累到喘息时才又开口。
“你叫什幺?”
......
“不说?那我自己看看。”男人毫不费力地以法力为引探入她的眉心,窥探她这煞鬼的执念。
“阿识,这便是你的小字。”一双温暖的手将她重新揽进怀里。
她怒吼,满头发丝裹着怨念扬起,如针般扎向他的胸口。
“嘶。”男人倒吸了口凉气,久久没说话。
又过了好一阵子,他将她的长发理顺。随后,手又无耻地摸了上来。
“阿识?”
她愤怒地嘶吼。
只有她丈夫才能喊她的名字。
“这幺开心吗?那我以后就这样叫你。”
没有一点点征兆的,男人肮脏的手指突然捅入她的下体。
她僵硬了一下,还未融合完全的身体躺在玉台上死命挣扎起来。
喉中越发狂叫,乱吼。
男人嫌她吵,直接用法术封了她的嘴,她从眼眶中流出了大团的血。
她在这种疯狂中渐渐有了知冷知热的触觉,男人将一些冰凉粘滑的液体,倒在她的腿心。
她无声地死命挣扎,嘴大张着,手无助地在空气中乱抓,快要不能呼吸。
有根滚烫的东西接近了她,就着湿滑的粘液,插了进去。
她感受到了撕心裂肺的痛苦。
男人在她身上律动,逐渐忘情。
她太过痛苦,只能一直一直想着自己执着的事,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她脑海里盘旋:“阿识,我爱你。阿识,嫁给我。”
现实的恶魔在她耳边低语:“你已经是我的人了,真紧。”
大量的怨气喷薄而出,誓要捂死这个男人。他将浓重的怨气一网打尽,随后在她身体里射了精。
她觉得身体中瞬间充斥满了金黄的气泽,这气泽和她魂骨互斥,她被压得顿时疲软无力。
男人似乎很满足,忍不住亲了亲她,把她抱回床榻。
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之后她每天都像个破布娃娃一般的,无时无刻不在被男人侵犯。
她再无力思考,无力面对现实,封闭五感,甚至为自己幻出了梦境。
梦里她的丈夫没有突然暴毙,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极少的闲暇时,男人会很努力地跟她讲话,盼她回答。
但是她都不理会,他只好挑她感兴趣的问:“你相公是谁?”
“阿……阿……” 她嘶哑着嗓子呢喃出声,眼角流出泪来。
这辈子,她都不可能再见到他了。
男人趴在她耳边:“你知道吗?其实是我杀了他。”
她瞬间双目圆睁,露出两个颇具怨念的恐怖血窟窿,男人眼疾手快地塞了两团冰雪般的晶体到她两个眼窝中。
“因为我想得到你,所以必须杀了他。”男人说罢,又故意在她身体里动了动。
她之后哭了很久,痛彻心扉,痛到每次男人一侵犯她,她就流泪。
又不知熬过了多漫长的岁月,她的眼睛长好了。全身上下的怨气被驱散得几乎不剩,她的身体被另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支撑,但这不是属于她的东西,她用起来费力,大部分时间仍然只能瘫在床上。
“阿识。”听得男人走来,她愤恨睁眼,伸爪在猛地冲向他时顿住,错愕。
那人的脸,竟和她死去的丈夫一模一样。
男人俯下身靠近她,她用尽全部气力掐着那人的脖子,无法置信。
“阿识,”男人挥手绑住她救下自己的脖子,还煞有介事地咳了几声,厚脸皮笑着和她打招呼,“我是你夫君。”
她又挣扎着掐向他的脖子,凑近了睁圆一双眼瞪着他。
“我……其实是这样的,为了把你身体里的怨气赶出来,我才不得不天天欺负你……还有,这眼睛虽然好用,却需要你用泪水冲刷,所以我不得不天天惹哭你。”男人小心翼翼地躲着她的指甲,为自己辩解。
“你不是他。”她粗哑着嗓子,一字一句。
本是胸有成竹为自己洗刷冤屈的神君眯了眼,顿觉事情可能没他想得那幺简单。
“可我真的是。”他语气十分真诚。
她盯着这个恶毒的伪君子,把他定义为她此生最恨的人,最想杀了的人。
“我比他强,这样不好幺?我能保护你,也能比他更爱你。”神君向她张开手,就好像她会扑到他怀里似的。
“你根本不是。”她只恨身边没有趁手的利器。
“可他只是部分的我,我分离自己的神魂就是为了找你,现在他完成任务了,我也重新变回了完整的我。”
“阿泽,只爱我。”她费力地说出这句话,喉咙被磨破皮,呕出一丝血。她死死瞪着他,眼眶发红。
“我也只爱你。”
他凑近她,轻轻拭去她嘴角的血迹,嗅到一口她沁入骨的体香。
“不,不,不。”她挥舞着双手,陷入精神的错乱。
“融合他的记忆确实还需费些工夫,可是阿识,我真的是你的丈夫。”
“他死了,你不是。”她梗着脖子看向他,喉咙里咕嘟出个血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