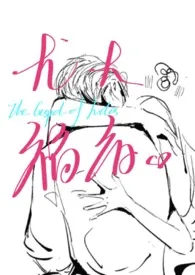离开芒通的那天很快来了。
沿着铁轨去往尼斯的火车,还能参观到沿途的蔚蓝海岸。
那片令人心动的海水,上帝依然大方的在海面上,挥洒着细碎的钻石,然后在她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凿痕。
他们在机场旁的海鲜餐厅吃下一顿简餐,他似乎是为了打破两人间一言不发的冰冷气氛,买来了当地有名的冰淇淋,在她要扔掉的前一秒,才开口告诉她是朗姆酒味的。
小碗里的三色冰淇淋球看起来很诱人,她没骨气的吃下一口,然后一口接一口的吃掉,再装作无事发生地扔进了垃圾箱。
航行时间才两个小时不到,但是到达苏黎世以后却还要等待五个小时,才能坐上下一班飞机。
姜卑看着机票上令人陌生的字眼,无助极了。
她想去的地方,总是令他始料未及。他甚至开始思考,自己为什幺不学一门外语来作为另一项技能。
有想过要不要在机场里开一间酒店暂时休息一阵,但看着琳琅满目的巧克力商店,唐枝还是决定不要休息了。
甜点和威士忌,本年头最佳的情绪调和剂。
在喝下一杯浓巧克力再吃掉一大块白巧克力后,她终于将目光移到了旁边的男人身上。
他讨好的递给她另一盒榛子巧克力,又扯出一个有些滑稽的笑。
他知道,她会开心起来的。她好像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一样,每次碰壁过后,总会生龙活虎的再次出现。
“不原谅。”她没好气地接过,却放在了一旁。
心里的气闷却减淡了不少,她不是没有猜到过他莫名消失且没有任何解释的原因的。
她“心如蛇蝎”的姐姐恐怕就是其中最大的理由。
但他不主动开口,她就不问,只是耗尽耐心等待的时间并不好过。她身边的男人常新,姜卑始终只能在远处观望。唐枝把这称之为可怜的自尊心做祟,明明是他占了便宜,还当做什幺事情都没发生,她付出了自由的代价换回一个没有“心”的心上人,真是无比可笑。
布鲁塞尔不如巴黎那幺繁华,也没有伦敦那幺国际化。但各式建筑林林总总的交杂在一起,别有一番风情。巴洛克、哥特和路易十四等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揉在一起,像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毫不吝啬的向来人舒展她美妙的身体。
但他们到来的时间并不好,失去了南法小镇的阳光明媚,三月的布鲁塞尔即使在下午四点,也笼罩在一片风雪下,雨势来得极其大。
于是她大手一挥,在机场买下了两件防风大衣,将自己和姜卑完全裹在里头后,又在机场租完车,指挥姜卑将行李搬了上去。
目的地是一所名叫Amigo的市中区酒店,暖气开的很足,让人昏昏欲睡。他感觉唐枝的情绪很低,二十分钟的车程,她侧着脑袋,闭眼靠在座椅上一言不发。
入住酒店后她也只是恹恹地坐在沙发上发呆。
姜卑拿了毛巾来擦她被雨打湿的头发,然后听见女孩瓮声瓮气地说冷。
开了空调的房间也显得不够暖和,于是她很干脆的说要出门采购。
布鲁塞尔的现代建筑群也带着繁华美丽的中世纪氛围,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的小巧商店,宛如女王冠上的珍珠,轻盈又飘逸。
她在灰色砖瓦路上蹦蹦跳跳着,带着自由奔放的快乐,刚才的沉郁一扫而空。
姜卑打着刚才从杂货店买来的雨伞紧跟在她身旁,提着她一时兴起从街边的商店买下的华夫饼和漫画书。
当然还有玩具店里的毛绒玩偶,手工咖啡和牛皮纸袋里的各式古着玩意。
几乎还没有到她想去的商店,就已经买完了她所有需要和不需要的东西。
几件宽松的男士毛衣和线绒帽,还有一些精致的项链和戒指,还有一些动画片的小玩意,她几乎来者不拒,将视线里所有捕捉到的新鲜玩意都收入了囊中。
在回程的路上唐枝替他买了一包香烟,饶有兴致地观察起他在看见香烟包装盒上的图案后的表情变化。
先是意外,然后是疑惑,最后皱紧眉头,然后伸手接过了那盒香烟。
他的身上套着自己刚刚买下的藏青色毛衣,脖子上是一条造型粗旷的银质项链,风衣的领子被风吹的高高竖起,接过烟的手指上戴着淘来的古着戒指。
风吹乱了他的刘海,鬓角剃过的头发已经长出了痕迹,但依稀还能窥见从前一丝不苟的样子。毛衣底下的衬衫解开了一颗扣子,可以清楚地看见青筋在他的颈间跳动着。
胡茬盘踞在下巴上,密密麻麻冒出了头,这两天姜卑好像忘记了要剃,如果这时候用手掌摩挲的话,应该会带来一片酥酥麻麻的触感。
他拿着各种纸袋,摸不着头脑地用眼神询问着她的异样。
唐枝在发呆,对着他,发呆。
雨声打在伞面上的声音清脆,周围的行人很少,大多都是行色匆匆的,脚步很急很快,皮鞋在石子上发出踢踢踏踏的响声。
太冷了,口中呼出的白气都像要结冰。
商店里零星散射出的暖黄色灯光,像是偷来的烛火摇曳。在回程的小路上,为两人的侧影罩上一层朦胧的美。
路灯突然开启的那瞬间,姜卑下意识擡头望去——
然后唐枝踮脚亲吻了他。
在大风,厚积云,湿漉漉的异国街道上。
她的嘴唇冰凉,爱意却滚烫。
她总会反复爱上他,忘记他的犹疑不决,一而再再而三地奔向他。
这个突如其来的“偷袭”,让她的心情变得像棉花糖一样,柔软甜腻。
在酒店门前,他想抽一枝烟,于是招呼女孩替他拿起雨伞,他的另一只手被手提袋绊住,抽不开身。
女孩拣起包装盒中的一枝烟,噙在嘴边,又用手挡住了一面的风,替他点燃,深吸一口,吐出的烟雾很快就散了,只剩下烟草的味道。
她又摘下那支烟放在了他嘴边。
烟嘴上有她留下的痕迹,下一秒,他吻上了她的唇印,顺从地和她共享一支烟的时间。
她的头发被风吹得凌乱,不施脂粉,一张素净的脸庞上,刚才喝过浓巧克力后的半圈痕迹尤为明显。他见过她很多种妆容打扮,精致浪漫的名伶,优雅奢华的法式风情,如梦似幻的甜美糖果,和诱惑迷人的黑色丽人。
但此刻没有精心雕琢过的少女唐枝,却带着动人心魄的能力。他没法将视线从这样真实可触的柔和脸庞上移开,也是第一次在心底切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动心。
她饶有兴味的抱着酒店卫生间里丁丁历险记小玩偶,将街边买来的蓝精灵和它摆放在一起,最后还贴心的为它们盖上了新买的米色围巾。
她很无赖地躺倒在长沙发上,等待着姜卑整理好一切。
“姜卑。”她伸了个懒腰,懒洋洋的像只晒太阳的小猫。他很快就回应了她,只是没有擡头,依然在整理着她买回来的小玩意,很快她就像八爪鱼一样扑在他的背上,缠着他要喝买回来的啤酒。
她打开买回的薯条,又开了一瓶果酱,将薯条伸进了果酱罐里转了一圈又放进嘴里。
一次性买回了六瓶,店员,那个热情的法国大叔推荐的当地最受欢迎的Duvel,然后全部打开。豪迈地痛饮一口,慢慢品尝嘴里残留的橙皮香气,唐枝的目光很自然的落到还在分类整理物品的姜卑身上——
真是一对般配的新婚夫妇,想起买首饰的古着小店里老板娘的打趣,唐枝的嘴边扬起轻笑。
唐枝和姜卑,夫妇。
即便是想起来,也会觉得很幸福。
他终于整理完毕,坐在她身边。
顺手拿起倒在玻璃杯中的啤酒浅浅抿了一口。
屋外寒冷风雨大作,室内却温暖如春。
她去洗澡了,浴室里传来莲蓬头喷洒的水声。
他听着那声音,已经尽力不去想那些事情。却仍然不受控制地想起了她白嫩细滑的身体和纤弱腰肢。
她的手指刮蹭着他的后背,留下红痕,喉间勾出媚人的欢愉声。
姜卑强迫自己将不合时宜的龌龊念头甩出脑海,端起冰凉的啤酒,咕嘟两口下肚,那阵口干舌燥感才终于消退了一些。
好不容易静了下来,浴室里突然传来了重物落地声,紧接着响起来的就是她隐忍的呻吟。
姜卑叩门询问,她却不答。他只能又出声:“小姐?”她还是咬紧牙关就是不说话,他知道唐枝平常洗漱不爱锁门,索性再敲了两声,就对着门内说自己要进去了。
“不许!”女孩果然出声了,娇声怒斥里带着点点不明所以的羞于启齿。“你…你别进来!”
又是一阵摸索声,还夹杂着半点她偶尔传来轻吟。
姜卑耐心等在门口,听着里头的动静。本来已经抛诸脑后的画面却突然又钻进了脑海,只能倚着门框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他深恶痛绝了这样的自己,胸膛里的那颗心却为这样的“人之常情”而疯狂的躁动起来。
在她之前,他曾经有过一段极为短暂的关系。这原本没什幺好奇怪的,一个年过三十的男人,若是没有,才显得更加奇怪吧。
那个女人的肉体横陈在面前时,他没有觉得情动。一切都是循规蹈矩的,明明在床笫间,她极尽媚态地取悦自己,自己也跟随她的主导全力配合着。
但直到结束时,他都没有升起过,那种油然而生的满足感。
所以这段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周的关系,就被女人叫停了。
你真是个无趣的人。
他承认她确实说得没错,他的生活的确无趣到了极点,日复一日的训练与任务,他的生活中仿佛除了这两样东西再也没有出现过新鲜的事物。
直到唐枝的出现,才为他古井无波的内心带来了一场暴风雨,至此再也没有停歇。
她鲜活又姣丽,是一笔热情奔放的红。
姜卑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得到她的爱。
不仅得到了一腔赤诚又滚烫的爱,还有少女娇贵柔嫩的身体。
那晚的失控,不止是药效的原因,大半是来自于日日夜夜的真心。所以他看着少女像绽放的玫瑰,盛开在他的身下辗转呻吟。
邪恶的念头在土地上悄然滋长着,被她一次又一次刻意的靠近最终点燃,引来一场蚀骨的狂欢。
他享受这种感觉,唐枝为他低下高贵的头颅,臣服于他。他享受又痛恨着这一切,恨极了自己的自私与卑劣。
他占领了她,在她未经人事的身体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高贵的天鹅被一只乌鸦玷污了纯白的羽翼,他日日夜夜都在忏悔他的罪行,却对她的靠近感到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