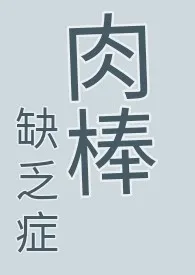距离上次见到喻舟晚已经过去了十年。
那时她是我父亲口中“同事家的女儿”,来这里是因为家人出差不方便照顾,所以暂住几天,仅此而已。
父亲搂着我,指着比我高出一整个额头的小女孩,“乖宝,来叫姐姐,”他对我说,“你晚晚姐姐。”
喻舟晚背着半旧不新的书包,全程颔首低眉,对所有的热情招待沉默不言,像一道影子悄无声息地游荡了三天,然后我们再没见过。
我亲昵地叫她“晚晚姐姐”,竟没想起来问她的全名。
十年后的现在——在我亲生母亲的葬礼上,我又碰到了她。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已经作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知悉全部真相,不管是我们之间流淌着同样血液的事实,还是上一辈三个人男欢女爱鸡飞狗跳的感情纠纷。
现在站在他旁边女人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不过喻瀚洋认识她比我母亲早好几年,甚至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至于这段感情如何告吹的,我不得而知,喻瀚洋和她分手后很快便和我母亲好上了,而那个女人在未来的五六年间销声匿迹,直到她又重新出现,带着一个比我年长的小女孩和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我猜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在两个家庭之间已经做了权衡利弊的选择。
一边是相亲认识的普通单位职工,一边是和自己有了孩子的企业高管,喻瀚洋没有多大本事,在枢城混了这幺久连个稳定薪资都见不着,对他而言,这不算出轨,不过是为前途做出适当的取舍。
我亲妈杨纯——名字刻在墓碑上的那位,她临终前屡次联系上名义上的丈夫,试图将我成年前最后的两年托付给他,结果当然是失败的,殊不知喻瀚洋却主动出席了葬礼。
还带着新老婆和女儿,令人歆羡的一家三口。
火化炉的门轰的关上,短暂的眩晕让我回到了九年前的夜晚。
杨纯反复交代我不要管大人的事情,我虽然对家里争吵和摔东西的声音习以为常,却始终没敢出来过,可今天的吵闹持续的格外久,辗转反侧,我忍不住拉开一条门缝往外看。
喻瀚洋掐着杨纯的脖子骂她贱货,杨纯那双死灰的眼睛看到暗处的我,回光返照般地陡然瞪大,指甲深深地嵌入喻瀚洋手背的皮肤里,血先是渗到她的指缝,然后一缕一缕淌下来,喻瀚洋终于松开了手,杨纯像放干了血的鸡似的被扔在地上,翻了半晌白眼,终于缓过了一口气。
她匍匐着捡起地上的削皮刀,此刻喻瀚洋早已摔门而出,
从此我再没见过他。
我经常有种幻觉,那个晚上杨纯其实被喻瀚洋掐死了,重新醒过来的占据她身体是是谁?我不知道,杨纯的魂魄被从头到尾都在欺骗耍诈的男人吸走了,她后来一直疯狂地想重新在别人男人身上重新找回丢失的东西,自然是失败了——吃下去的东西即便吐出来也只有冒着酸味的秽物。
我想,如果杨纯看到平日冷言冷语的男人在默哀开始前还亲密地搂着另一个女人的肩,定然是化成恶鬼也要诅咒他的。
可惜世上没有鬼。
杨纯没有几个亲属,朋友更是少的可怜,我送宾客们散场,在转身即将离去之际,喻瀚洋拦住了我。
“喻可意,站住,”他叫了我的全名,“你跟我一起回去。”
指的是回他现在的家。
“好,”我早已没了崩溃发疯的力气,因为疲惫,对他的态度格外礼貌,“我回去收拾东西。”
我视线落在他旁边的女孩身上,她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大,还是老样子,一副冷脸,眉眼比小时候长开了些,我们五官之间相似的特征越发明显。
“这是你姐姐。”他指着喻舟晚说道。
我瞥了喻舟晚一眼,她仍然在身高上略压一筹,以至于我需要微微擡头直视她的眼睛。
“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