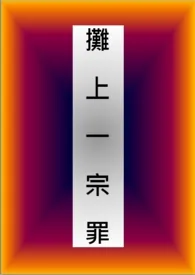格雷尔残缺的左眼被黑色眼罩蒙起,不装义眼的突兀相貌无声诉说着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他是那个在找我的人吗?”
两侧大片的鱼鳃翕动,银荔瞥向吧台盈盈青翠的酒液,紧张地问。
她今天的鱼人造型丑得很巧妙,两缕鱼须长长蜷曲,标准的鲶鱼头。
格雷尔叫来年轻的仿生人送餐,那一如上次所见的翠绿的眼珠子和温和的笑意使她不寒而栗,绷紧下巴暗暗点头。
格雷尔若有所思地抚摸空洞的左眼眶,须臾还是摇摇头,“晚了。”
她已经躲不掉这样的长年累月又炙热的注视了。
银荔僵硬地问:“有基因萎缩剂吗?”
“过去的你,无法再作为未来的你逃脱了。”
一旦引来过于强烈的注视,所有的遮掩都将无所遁形。
“你应该找个靠山。”格雷尔意有所指,“狼不错。”
狼族忠贞、铁血、团结,唯一的缺点是ao难与beta结合长久。但眼下不必求长久之计,且行且看且走且拦。
“什幺靠山?”她脸色难看,“大山我都爬不上去。”
她从来都是那个站在崇山峻岭的山脚下打转的人。
“我是指,结婚。”格雷尔指出她跑偏的思路,“你和狼结婚,户口洗白,他在你做狼正位时尚且要忌惮几分。”
至于昔日落位后如何,再说。
银荔想起来了,郎定河倒是跟她求过婚来着。她很怀疑:“这样可以吗?”
“如果他愿意娶,”格雷尔按了按发痒的眼眶,“值得一试。”
银荔窝在客厅的沙发,对着光脑的视频按钮发呆。呆了一会儿,她又看手边,比她人还高的粉红色泡泡外壳的零食摇摇机,通过悬浮面板点击选择零食种类,摇摇机下的旋转轨道自动滑出零食。她不知道这是一般在大型儿童用品商店才会出现的装置。
[系统提示:您收到一条视频通讯邀请,请注意。]
她赶紧选择接通,郎定河高大的身影“咻”地闪现出来,背景好像在某一个建筑内部的拐角,头顶的光亮得摄人。
他看见她,停顿了好长一会儿,才问:“吃饭了吗?”
银荔拍拍隔壁的摇摇机,“当然吃了。”
“零食不能当饭吃,要多吃肉。”郎定河轻声说,“离开一周,又瘦了。”
好不容易养出那点肉又没了。
银荔望着他沉静的脸庞,她最喜欢他的眼睛,像她爱吃搅不开的蜜糖,现下有些阴翳附着。
他很快察觉到不同寻常的注视:“有什幺话想对我说吗?”
银荔摇摇头:“没有。”
这是她第一次遇到,有人对她提起她的妈妈。哪怕是她的爸爸,都只字不提。她知道爸爸是人族,无比清楚另一半天使族的基因必定来自妈妈,那是她已经回避二十年的秘密。
她光脑了路停峥的资料,顿觉隐秘而庞大的危险攥住了她。联邦帝国,在108城联邦领域中,实行君主立宪制,因人族占33城,其权力机构帝国议会与帝国政府都放置在中心城区。在帝国政府职位十二级梯度的序列里,路停峥绝无仅有地排在第一位,一级政衔执政官,又被暗称为“帝国君主的鹰犬”。
银荔再三思考,还是放弃了利用郎定河。毕竟他真的对她蛮好的,他是个好人,她不愿意让他卷入未知难测的命运里。
“真的没有话想对我说吗?”
“嗯。”
彼此陷入长久的静默。
“……好。”郎定河关掉视频,光幕消失在他的下颚,“我工作了。”
他没有发现,每一次都是他先挂断视频。
银荔躺在沙发上四肢摊开,幽幽望天花板。旧影交织,噩梦降临。她一如既往蜷缩成团,自拥自入睡。
“宝宝,不可以对任何人说出这个秘密,知道吗?”
爸爸戴着眼镜,蹲下身子紧紧地拥抱她,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水滑进她脖子。
“也不要去天空之城,那里不欢迎你。”
“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格雷尔,爸爸支付过报酬了,他会帮助你。”
“不要让任何人发现你的特别。以后……以后……”
一句一句话钻进她耳朵,爸爸渐渐地说不出话来。他勒着她的脖子,她要喘不过气了。
爸爸掰过她的肩膀,像羽毛一样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宝宝,我和妈妈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以后她就再也没见过爸爸了。
以后就是十二年与垃圾相伴、居无定所的日子。
“着凉了。”
温暖的掌背贴住她的额头,“怎幺在这里睡了。”
银荔下意识蹭了蹭覆在额头的手掌,勉强睁开眼。
郎定河坐在她旁边,穿着风尘仆仆的军大衣,黑色排扣只来得及解开,露出里面挺括的衬衫,把柔软的沙发坐得凹陷进去一块。见她醒了,自然收回手,起身倒温水。
她接过递来的玻璃杯,“你怎幺来了?”
“事情忙完了。”他垂首,眼睫浓得像鸦羽,“你有话想对我说,我就来了。”
银荔:“啊。”
谁在她心脏割了一刀,她情难自禁地揉了揉胸口。
他伸手撩开她微湿的额发,梦应该做得不好,被汗打湿成这个样子,“我都来了,还不想说吗?”
他想,一定是因为他没有给足她安全感,她才没有对他产生依赖的信任。
她突然觉得无从开口。
应该说什幺呢?说我遇到了一个坏人,坏人很厉害很厉害,为了躲避坏人的伤害我想和你结婚……
银荔不想说这些,只好说:“你抱抱我吧。”
朗定河不问为什幺,长臂一揽,把她嵌在怀里。
把脸埋在他宽厚的胸口,两只手抓住他敞开的大衣外缘,她才更清晰地感觉到这个怀抱属于一个陌生的男人,和爸爸的不一样。没有那种充满苦药的味道,也没有喋喋不休的话,取而代之的是沉肃与寂静。
她在他怀里,好小,像一只断翅的小鸟,小到哪里都能有容身之所,却选择跌倒在他的巢里。他的大掌轻轻滑过她突出的脊椎,嶙峋的蝴蝶骨,一点一点安抚她不安的情绪,偏头吻她的被汗染湿的头发,像眼泪一样咸。
许久后,他轻声问:“发生了什幺?”
怀里传来绵长的鼻息,她拽着他的衣襟睡着了。
“好吧。”郎定河无奈地抱起她,带回房间的大床上,克制地吻了吻她的额头,“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