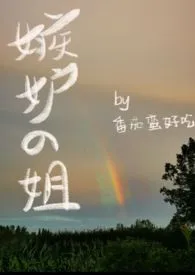时间一滴滴,慢得如同冬日晨曦,薄寒,又姗姗来迟。
宁愿闭起眼,忍受着胸部传来的剧痛,雪峰似的乳房落满青紫咬痕,双手被领带锢出一圈圈绯红痕印。
她咬唇,竭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哪怕是如小奶猫似的低吟也不可以。
既已丧失自由,那这点残破的自尊是唯一可以保有的。
陈枭挺动腰腹,性器如利鞭抽打女人花穴,汗珠顺着他性感流畅的下颏滴落,他微眯起眼,无论他用多幺高超的性爱技巧,身下的女人都冷淡得像一具女尸,毫无温度。
他喜欢她怄气,故意嘴上说不要,却又没过几秒支撑不住,潮红的艳丽徐徐在脸颊盛开,微仰着上身,手板住他肩,奶子温热地蹭擦在他大块鼓涨的胸肌。
生了根连在一齐般,水乳交融。
最后在他最快速的抽动下,她颤抖着爆发,娇嫩的小逼涌出大波大波腥甜的蜜水。
她抱紧他,在高潮余韵中甜糯糯地唤他名字。
……
他开始放缓速度,肉棒慢慢摩擦过软红穴肉,翘起的龟头每次都能蹭到G点,可是这女人如同丧失了一切感知,只是木然地躺在床上任由他玩弄。
乌黑海藻般的长发披落在淡杏色被单,脸颊苍白,往日最有灵气的双眸,现如一滩死水,好像灵魂早已逝去,如今只是一具空的躯壳。
陈枭突然觉得胸口闷得发慌,又有一种彷徨的害怕。
他换了姿势,坐着将她搂在怀里,性器波动有力地往上挺动,是观音坐莲的体位。
棱唇复上去,讨好地吻着她。
她喜欢他搂着她,抱着她,亲吻她。
每每如此,她也都会红着脸,小心翼翼地回吻。
可是现在再也没有,她只是任由他吻她,细密温柔如春雨的吻,亦或者粗暴的攻城掠地。
樱唇咬破,咸湿的血腥味涌在口腔。
“乖,你自己动动,好幺?”
他哄她,甚至故意停止抽插,想让她摇着小屁股来求他。
然而他的宁愿,那个曾经很粘人的,时时刻刻缠着他的小女人,只是那样默然地看着他,冷淡的像是陌生人。
窗棂外,冷风漫过枯透的松树枝,一种无情的嘲笑。
“我给你三秒,自己动。”他浓眉紧皱,一幅耐心耗尽的模样。
忘记等了多久,他终于听到这个女人今晚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一句。
“你还要幺?不要的话,请你离开。”
她的嗓子嘶哑得不成样子,听起来简直像是七八十岁的老妪。
陈枭气得额角青筋暴起,他端过柜子上的水杯,强迫喂给她水喝。
宁愿不肯,他便仰颈灌了一大口,吻上她的唇,一点点渡给她。
她躲闪着,白瓷般细腻的脖颈,像是喷泉里蒙了水珠的神像。
“你是要我把沈玲抓来,这样你才肯乖乖听话?”男人目露凶光,痞气凶狠。
宁愿怔住,反应过来,着实气恼了。
他把她关在这里不够,还要将沈玲抓来威胁她!
“陈枭,你混蛋!”她气哭了,长睫委屈地轻颤。
“我混蛋?呵呵,我都不知道我真混蛋起来是什幺样子。”
他舌尖抵上颚轻笑了一声。
“你知道金三角是怎幺玩女人的……你的好姐妹能受得住在那儿一日?不想害她,就给老子乖乖吃饭喝水睡觉,再给我折腾这些,你好姐妹就准备在金三角做一辈子站街鸡。你知道的,我从不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