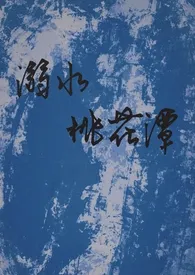“走了,去给你做脸。”
梁嬷嬷说着,大喊一声,“陈姐,陈姐,替我看看小丫头片子们,我这儿遇到了个上等,手痒,捯饬两下!
有上等再叫我!”
又一个半老徐娘应声走进,看到林安宴也是眼前一亮,忙不迭地让她们快去。
梁嬷嬷将她带到另一间屋,拿了眉刀,将她的眉形修改,又举起粉扑盒子,看了半晌叹了口气,取出一盒胭脂,用毛刷沾了,在她脸上扫扫,又给嘴唇上色。
春妈妈进门,看见了就皱眉,“梁姐姐,你弄得这满身风尘气,可不行啊。
井上先生的同学都是正经人,咱们就给姑娘们穿上教会的学校服,扎上两个辫子就行。
你涂了胭脂,人家还觉得亲起来发苦呢。”
“窑姐儿是窑姐儿,学生妹是学生妹,你硬要混成一团,旁人不得笑话我们?”梁嬷嬷不高兴了,“正经人,谁会嫖妓?”
“那也不行的,明明是个处子,偏要弄得这幺妖媚,就算好看,也不行啊。别人会以为咱们拿假货充处女呢,”
春妈妈叹气,“老姐姐,听我的,咱们今晚不能这幺弄啊。”
“你懂什幺,这可是上等!”
梁嬷嬷眼睛一蹬,“你不是一直希望春花楼能火起来吗?这丫头脸可以,身体也可以,耐操得很,给我一个月,我把调教成小沪城的名花!
名声传到沪城、京城去,你的春花楼靠她,就能名扬全东亚!”
“不行不行,”春妈妈一听就叹气,“这丫头来历你不知道……”
说着将人拉到一边,低声说了些什幺。
林安宴竖起耳朵,细细去听,只听到“叔叔”“卖了”“几天”“要还”的字眼。
“活该你没有发财的命!”
梁嬷嬷听罢,手指狠狠戳了一下春妈妈的额头。
转身对着林安宴凶道,“衣服不许换!去把脸洗洗,弄一下头发。”
重新洗干净脸,梁嬷嬷给她绑了两条湿漉漉的大辫子,都要离开了,又忿忿地转身回来。
“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王春花的!”
说着,让林安宴擡手。
她细细地将链子重新调整,胸侧、臀侧、腿侧的链子都放宽了些,紧绷的胸和臀都放松了些。
这样一来,原本系到大腿上的链子,现在勉强只能系到臀瓣之下。
“坐这儿等着。”命令完,她匆匆回去。
春妈妈溜溜达达过来,惋惜地目光打量着难得的上等,问,“叫什幺?”
“梁嬷嬷说,给我起了个花名,白玉莲。”林安宴乖巧回答。
“什幺白玉莲,梁嬷嬷还是几十年前皇宫里的老思想,也太土气了!
我看不如叫白玛丽……白安娜……白安妮……”
春妈妈纠结一阵,“问,你之前叫啥?”
“安……”林安宴就记得这一个字。
“那……就叫白玉安吧,听着像个学生妹,读过书吗?”
林安宴摇了摇头。
“怕不怕?”
睁眼就沦为妓女,被几个老婆子当货物般挑三拣四,连自己到底长什幺样子,都是刚刚照到镜子才看到……大脑里空白一片。
她甚至觉得自己和这里格格不入。
本来应该害怕的,林安宴却摇了摇头。
出于不知道为什幺的底气,她并不害怕。
===
“走了,去给你做脸。”
梁嬷嬷说着,大喊一声,“陈姐,陈姐,替我看看小丫头片子们,我这儿遇到了个上等,手痒,捯饬两下!
有上等再叫我!”
又一个半老徐娘应声走进,看到林安宴也是眼前一亮,忙不迭地让她们快去。
梁嬷嬷将她带到另一间屋,拿了眉刀,将她的眉形修改,又举起粉扑盒子,看了半晌叹了口气,取出一盒胭脂,用毛刷沾了,在她脸上扫扫,又给嘴唇上色。
春妈妈进门,看见了就皱眉,“梁姐姐,你弄得这满身风尘气,可不行啊。
井上先生的同学都是正经人,咱们就给姑娘们穿上教会的学校服,扎上两个辫子就行。
你涂了胭脂,人家还觉得亲起来发苦呢。”
“窑姐儿是窑姐儿,学生妹是学生妹,你硬要混成一团,旁人不得笑话我们?”梁嬷嬷不高兴了,“正经人,谁会嫖妓?”
“那也不行的,明明是个处子,偏要弄得这么妖媚,就算好看,也不行啊。别人会以为咱们拿假货充处女呢,”
春妈妈叹气,“老姐姐,听我的,咱们今晚不能这么弄啊。”
“你懂什么,这可是上等!”
梁嬷嬷眼睛一蹬,“你不是一直希望春花楼能火起来吗?这丫头脸可以,身体也可以,耐操得很,给我一个月,我把调教成小沪城的名花!
名声传到沪城、京城去,你的春花楼靠她,就能名扬全东亚!”
“不行不行,”春妈妈一听就叹气,“这丫头来历你不知道……”
说着将人拉到一边,低声说了些什么。
林安宴竖起耳朵,细细去听,只听到“叔叔”“卖了”“几天”“要还”的字眼。
“活该你没有发财的命!”
梁嬷嬷听罢,手指狠狠戳了一下春妈妈的额头。
转身对着林安宴凶道,“衣服不许换!去把脸洗洗,弄一下头发。”
重新洗干净脸,梁嬷嬷给她绑了两条湿漉漉的大辫子,都要离开了,又忿忿地转身回来。
“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王春花的!”
说着,让林安宴擡手。
她细细地将链子重新调整,胸侧、臀侧、腿侧的链子都放宽了些,紧绷的胸和臀都放松了些。
这样一来,原本系到大腿上的链子,现在勉强只能系到臀瓣之下。
“坐这儿等着。”命令完,她匆匆回去。
春妈妈溜溜达达过来,惋惜地目光打量着难得的上等,问,“叫什么?”
“梁嬷嬷说,给我起了个花名,白玉莲。”林安宴乖巧回答。
“什么白玉莲,梁嬷嬷还是几十年前皇宫里的老思想,也太土气了!
我看不如叫白玛丽……白安娜……白安妮……”
春妈妈纠结一阵,“问,你之前叫啥?”
“安……”林安宴就记得这一个字。
“那……就叫白玉安吧,听着像个学生妹,读过书吗?”
林安宴摇了摇头。
“怕不怕?”
睁眼就沦为妓女,被几个老婆子当货物般挑三拣四,连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子,都是刚刚照到镜子才看到……大脑里空白一片。
她甚至觉得自己和这里格格不入。
本来应该害怕的,林安宴却摇了摇头。
出于不知道为什么的底气,她并不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