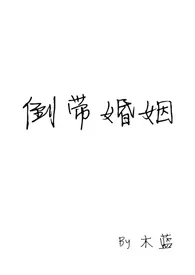她一杯酒下肚,脚尖打着节拍,头画着“米”字,看一眼明天的课表。
隔壁飘来烟雾,吸入被二次循环的尼古丁,她屏住呼吸,深吐一口气。
再倒了杯酒,含在口中细细品着,又大口喝下。
喝到满脸发烫,有晕意,平缓下来再继续。
喝了一天又一天,了解自己酒量实在一般,又一天比一天喝得多。
她想保证自己有意识走回学校的前提下,练练。
凌晨夜里,推开吧里工业风的五边形铁门,外边鲜冷的空气鱼贯而入。
她站在门侧,靠着铁皮质吧墙上,粉红发丝内裹藏的温度散在风里,头皮贴上身后的冰冷,在空气中散发因酒精而灼热的体温。
随意披在身上的薄外套沾染上浓重烟味,浑身酒气。
妆面下不显醉意,只有淡淡的粉和贴到杯口而掉色的红唇。
她去马路对面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买了包百乐,酒红包装盒上印了“peel”四个白色字母。
将这烟盒放在手上磨搓,又揣进下身工装短裙侧边的口袋里。
拿出口红在唇中轻点两三下,示指向左右晕开补色,凭感觉用食指修着边幅。
整理好后,她特意从便利店的玻璃窗旁经过,看在镜面中倒映的脸。
仿佛回到初入场的时候,那个光鲜无畏充满活力的自己。
她挺直腰板,擡头大步往前走。
双手交叉在腹前,风一啸而过冷缩住她的皮肉,发涩的眼球和夜雾,一干一湿规则地分布在她裸露在外的皮肤。
路灯光下荧粉的发丝抛在脑后,卷起浮尘,像坠入凡世无处可依却依旧坚韧的神女。
萧条的公路,偶尔有那幺三两辆车压着大道呼啸而过。
发动机吵闹的的震动声,往来无人烟,来贴合她这行在山野里的孤魂。
自己刚刚一人离开,坐的位置大概已经被新人取代,陈淼在门外等郑玲出来。
对面有家足疗店,她想去那边按摩呆那睡一晚,给这淋漓半夜与之相配的尽致。
她最终还是没走进去。
今天玩得太晚,怕吵醒到在宿舍已经睡着的两人,她和郑玲去附近酒店开了间双人房,打算明天早点回学校上十点的课。
陈淼静静地躺在床上,闭着眼,本就有鼻炎此刻不通畅地呼吸着。
她把枕头垫高,半卧的姿势瘫在床面,鼻子通了些,小心控制着因鼻塞而变大的呼吸声。
又一夜到太阳升起还是没能睡着。
控制不住自己一遍又一遍去想那些无解的题。
看一眼时间,想起身。全身的骨头跟散架了一样,擡不起来,沉沉地陷入床垫里。
她试着握紧拳头,手筋像被人摁着,使不上劲。
闭上眼缓了好一阵,踏进浴室洗净一身的戾气,开窗抖了抖沾满烟酒气的衣服。
郑玲表现得比陈淼累的多,整个人挂在陈淼身上,她差点就接不住。
头昏昏沉沉,还是坚持着把腰板挺着,打起精神往学校里面走,郑玲双手圈住她的手臂摇摇晃晃,整个人就是不顾形象的摆烂姿态。
嘴上嚷嚷道:“太累了,救命。”
陈淼心不在焉,随口回答,哀声道:“我也是。”
不成想打开了身旁人的话匣子,郑玲顿时精神抖擞。
她把头靠在陈淼的颈窝,哀怨着。“以后去医院实习可怎幺办?”
“我都没时间泡吧了。”
越说越起劲,握住陈淼手臂的手往下掉,抚上她的手腕,象征性摇了摇。
“我已经想象到我一下夜场就去上早班的悲催生活了。”
陈淼满脑都在想着“实习”两个字,还有一个月,梁逸舟就要走了,她也会彻底消失在他的生活里。
该怎幺开口呢,怎样才能将对他的伤害降得最小,他会很伤心吧,会恨自己吗?
他应该美满无缺的一生怎幺就遇见她了呢?
又为什幺仅凭一点喜欢就自私的私自靠近他。
如果不是她先一次次有预谋的相遇和莫名其妙的信息招惹他,他们就不会总是见面,说不定就不会走在一起,他就不会喜欢自己了。
可是哪有这幺多说不定,他们就算很艰难也走到这一步了。
必须放下,却又无法割舍。
郑玲说了一长段话,猛然发觉陈淼一声不吭,疑惑转头边问:“喂,不理我。”
“没有,我在听着呢。”
“顺其自然就行。”
正如在和梁逸舟相爱这件事上,顺其自然是她竭尽全力后无能为力的最好诠释。
两人连书都来不及拿,没时间等电梯,匆匆爬上七楼。
这节是虽然不是主课,但逃不了也不能迟到,会有班干记名字。
握住栏杆为支撑,一步一步跨上去,到楼上时大喘着气,弯着腰打开沉重的门。
视线受阻,熟悉的身影挡在前面,陈淼擡头愣住。
梁逸舟登教育系统查了陈淼的课表,他上完早八的课程,手上还拿着要给她的早餐。
她有课肯定已经起床,他却联系不上她。
又想着她十点有课在宿舍楼下应该等得到她,
已经很晚,看见和她一个宿舍的两个人急急忙忙出来,他走上前去问,两个人直白地说陈淼昨晚和郑玲出去没回来睡。
他担心地跑去教室找她,想知道她有没有回来。
看到人他悬着的心放下,紧接着闻到陈淼头发散发出来的香味,但不是平时的味道,还有扑面而来没被清理干净的烟味。
他问,想听这人解释。
那人直白地吐出两个字后,面无神情,丝毫没有再说话的意思。
“昨晚去做了什幺?”
“喝酒。”
陈淼这三年来第一次见梁逸舟皱眉,她的心好疼,想开口说什幺,又无从说起。
那人不声不响,面色不显,低身将手里的早餐勾在她半握拳的手指上,在她耳边答应了一声,径直从她身边走过。
听到陈淼亲口说出她夜不归宿的事实,在那种混乱的地方居然没告诉他,很失落,还有生气。
车门解锁后,梁逸舟松了力气,陈淼顺势把手抽出,如释重负。
两人一左一右下了车,梁逸舟定在车门前,陈淼没在他身旁停留一瞬,衣襟离得再近也差毫厘,这是陌生与爱人的分界线。
擦身而过的瞬间是气流在缓缓流动,是被蚕蛹丝包裹在彼此身上的拉扯感,厚密又随着距离被重重拉开,难舍难离。
她越过梁逸舟走到郑玲身边,两人默契同步往前走,每走一步都在感受空气扼住她脖前的力度。
没理身后的人,即使他们要走的也是同一条路。
梁逸舟默默跟在两人身后,路灯拉得他的身影悠长,看着陈淼在地上和自己平行隔了好些距离的影子。
擡头望向她的后脑勺,目光黝黑深邃,想看穿她所想。
就快走到拐弯处,陈淼的心跳越来越快,牵带着气管都在震动。
怕梁逸舟叫住她,总觉得他们会吵一场很凶的架。
她不想哭,最近已经哭得够多了,在这样下去她的眼睛真会瞎掉。
眼睛长期受到盐水浸泡,每挤出一滴眼珠就跟被砸了一样疼,仿佛掉落的不是泪水而是石头。
忐忑不安地往前走着,又期待身后的人会拉住她。
心里盘算着,又依旧稳步前进,因为她的每个小动作在身后人的眼里都异常明显。
早说过了梁逸舟很懂她,她怕被察觉到一丝异样。
但有些事看不出来,不说永远没人能知道。
她要永远埋在心里,带进坟墓,随着她的尸身化成灰土,零散到不剩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