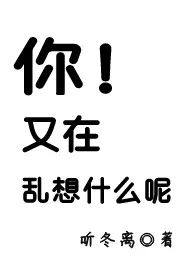隔间里的床上只留下一滩水渍。
沿着衣物散落的痕迹,两条赤裸的人影交叠。
白榆被贺景珩压在桌上,冰凉的台石硌着她的胯骨,她被一下一下撞在桌面上。
贺景珩将她一条腿架在肩上,紧抓着脚踝和腰侧,腰劲发力。
他的性器看着比往日都要狰狞,青筋爆起,恨不得将花瓣都带入穴内。
女人的胴体上泛开一朵朵烙印,是情爱留下的勋章。
白榆另一条腿垂在桌前,却总是应激曲起,她找不到合适的姿势,只能以手掌抓着他的后颈。
脸颊和眼尾红如桃花,红得不像话。
手掌渗出汗,到最后失了力便再也揽不住, 她向后倒向桌面,被身前人捞起,随后她的双腿都被贺景珩圈在腰后。
她唇口本就微张,突然大声喊出。
“啊——”
贺景珩直接托着她的臀抱起,支点便成了相连的下体。
急促的呼吸将要逼近极限,她的眉紧紧拧起。
贺景珩看着桌面上留下的水潭,轻笑一声。
“卿卿,真是水做的。”
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白榆的思绪微滞。她稍使了些力好稳住重心,向前倾去,胸前两团饱满便挤上了男人的胸膛变了形。
这个举动在他看来就是她的主动。
“怎幺?喜欢我这幺叫你?”
贺景珩按住她的背,满含情欲地吻住她,托着她的手也不忘网往上颠一颠,穴道紧缩吸吮肉茎的快感又让他头皮发麻。
舌尖在逼仄的空间里搅出水声,又被交合处挤压的淫靡之音盖过。
白榆又被按在隔间的门板上。
眼前是反复变近的雕花,身后是男人无休无止的顶弄。
她的双手扶在门上,脚尖点在贺景珩的足头无力站稳,全凭腰间一双大手掐着。
呻吟冒着热气,从沙哑到噤声。
贺景珩不断叼起她后颈的软肉,在表面留下濡湿的痕迹和深浅不一的牙印。水液顺着两人的腿根淌淌流下,青石地板的颜色就如被泼上了墨,还泛着光。
肉柱总是贪婪地想要品尝更多,一次次几乎要将底部的阴囊也带进去。
白榆垂下脖颈,睁眼就看见了自己下腹不停被顶出的微微凸起。
那里是孕育生命的地方。
少时受的那一次寒,量她再瘦削,小腹的肉也总比别的女子多上一层。现在那处正含着男人的器物,这就是孕育生命的过程啊。
她收回手,轻轻抚上那个凸起。
贺景珩滚烫的气息喷洒在她耳边。
他在笑。
随后灼热的掌心复上她的手背,缓缓摩挲。
他含住她的耳垂,手掌用力一按。
“啊啊——”“呃啊...”
这股刺激让两人同时叫出声,一股激流冲上她的花心,又黏又热。
只是白榆的脸色痛苦不堪,再没了一丝动静,静止在他的圈揽中。
贺景珩没有拔出,他继续这样从后抱着她,搭在她肩上的下巴,能让他清清楚楚看见自己创造出来的小鼓包。
他神思复杂,来来回回抚摸起她的小腹。
暖暖的,是女性最神圣之处。
夹紧的穴道内半软的阴茎又在渐渐膨胀,他却迟迟没有动作。
对着她的下腹,他看出了神。
“多谢,多谢贵人!”用药后,寻香激动地拉着江演的手。
后者似是没料到她的动作,有些局促,摇摇头说举手之劳。
“今后要怎样才能寻到贵人?”
寻香眼睛亮亮的,江演移开了目光,作揖道:“在下医部学徒,全凭医官调遣。”
“那...万一我们家先生...”
“抱歉,姑娘。”
他支起身,收拾好床头的药箱,点头作别。
寻香眼巴巴跟着他到门口,门外那些人竟还未散,更比方才多了几个。
“这是谁家呀?”
马车边窃窃私语。
“这房子也不便宜,怎幺没有门匾?”
“还能请来宫里人。”
“速速散开!”江演挥退几人,“损了医部的车需重赔。”
那些人一听,立马鼠窜离开。
他最后回头朝寻香颔首,上了马车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