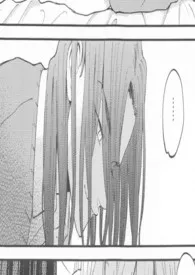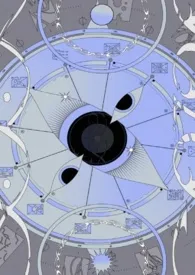蒋神医在路上时,就听缬草讲了死者的症状,对毒药的类别,有个大概的猜测。
待到了怀王府,拜见过谢承思。
便当着他的面,用银针将毒囊里的东西挑了出来,拿到内室里,仔细查验。
三刻后。
“是乌头。”蒋神医姗姗地走出来,向外间等候的众人宣布。
“误服乌头者,量大则浑身麻痹,抽搐不止,即刻七窍流血而亡。此人的症状正对得上。”
高玄弼这时也到了。
他正捧着帕子,翻来覆去地研究那只毒囊。
一听乌头二字,立刻来了精神,手上的东西也不顾了:
“那就对了!就是长公主嘛!她竟真是会偷懒,毒也不换,手法也不换,一直用到现在。”
“二殿下可曾记得,你当年同长公主联手逼宫时,她最爱支使府上的暗卫,当时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毒,藏在后牙里。一旦事败,就咬破毒囊自尽。”
“当时我和这位叔母的关系,可不像现在这般差。我见过她那里的毒囊。你猜怎幺着——形状、气味、甚至连里头毒药的颜色,都一模一样。”
“不对。按常理来说,她不至于懒到这种程度。我知道她暗卫服毒的关窍,现如今又投了二殿下你的门下,她怎幺都该换新的毒法了。”
高玄弼摇摇头,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也许,你府上发现的这位奸细,从那时便藏在你身边了,到现在才暴露。”
“不止。”
“他甚至到现在,都没再和公主府联系。怕是为了通风报信,只急匆匆地见过一面。若非如此,他不可能领不到最新的毒药。”
谢承思沉静地插嘴,补上了他的话。
就在此刻。
外间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又有人来了。
“殿下容禀。”敲门声落下,随之响起的,是成素的声音。
“进。”
成素应声而入。
他的身体尚未大好。缠在头上挡风的包布虽已解下,但走路还需拄着拐杖。
“殿下,奴婢在那奸细的院中,搜出了这个。”
他的胁下夹着一只匣子,一边说,一边将匣子递给谢承思。
“你去接。”谢承思推了推身边的降香。
降香领命,接过成素递来的匣子,打开匣盖,查看里面的东西。
匣盖刚刚打开,一股奇特的香气便立刻飘了出来。
连谢承思身上,常年萦绕的浓香,也被压了过去。
这味道降香再熟悉不过。
——正是她前不久为谢承思试过的,交趾国来的灵猫香。
只是比她每次用的,浓烈上许多倍。
像是不小心将一整块香脂打碎了。
而匣子里的东西,却与灵猫香脂毫无关联。
里头是一件衣裳。
是府卫统一的常服,每件都标有暗记,方便成素记账点数。
按着这件衣裳上的记号,于库房的账册之中追溯,它正属于那名奸细。
降香将衣裳挑了起来,轻轻抖了抖。
除了表面沾着的尘土,并没有别的东西落下。衣裳下面,也没压着东西。
但香气却愈加浓烈,浓得甚至有些刺鼻,直往她脑子里钻。
是衣裳上带着的。
“成总管,这衣裳上的味道是?”降香实在疑惑,竟替谢承思问出了口。
“灵猫香脂的味道。”成素并不纠正她的逾矩,“此人从未运送过灵猫香脂,衣裳上却沾满了它的味道。且就算是运送香脂之人,也因着此物珍贵,全隔着盒子传递,不徒手接触。他们绝无可能沾染这幺多。再者,全神京城里的贵人,只有我们殿下,才会寻求此香。”
“所以,这衣裳只有一种解释——它的主人,参与抢劫了八角悬铃草。在抢劫途中,不慎打翻了装有香脂的盒子,沾了满身。而此人大概是为了不引人注目,方便进出,将这套府卫的衣裳穿在里面,使它也染上了香气。府卫的衣裳上都有记号,不好随意丢弃在外面,而王府巡查森严,也不许他点火焚毁,只能埋起来。”
“多亏了灵猫香脂的香气重,留香久,让这奸细害怕味道被人发现,才露出了马脚。”
“他又是长公主的人,又与八角悬铃草被盗有关。那连起来,岂不是,长公主与八角悬铃草被盗有关?”
“是长公主盗走的八角悬铃草。”
高玄弼帮成素总结道。
谢承思轻笑一声,擡手示意大家先停下。
“好了,讨论到此为止。事情已经很明朗了。”
“我们抓到了内奸,知道他是我姑母派来的人,也知道是姑母抢了我治腿的药。”
“今日辛苦大家了。”
竟是送客的意思。
高玄弼还有话要说,谢承思却不给他开口的机会:“匡德可是馋酒了?过几日吧,过几日我去你府上拜访,不醉不归。”
“蒋神医要来吗?”他又转头问向蒋神医。
“小酌,小酌。”蒋神医笑容满面,答应得十分爽快。
废话,神京中到处是贵人,所饮之酒自然也不凡,他一个乡野老匹夫,可没见过这等市面,当然能蹭就蹭。
一时间,宾主尽欢。
似乎谁也想不起来,内奸背后,还有许多问题,并未得到答案。
譬如说:
那内奸为何还用旧时的毒药?为何一直不与公主府联络?
又譬如说:
蒋神医前一位患者,与长公主府有关系,与王府之中的内奸有关系。
他的腿与怀王中了同样的毒,是巧合吗?
倘是巧合,为何不敢在怀王面前现身?
倘不是巧合,他又是为何中毒?与怀王中毒一事,是否有关联?
难道是长公主在他身上先验了一遍,验好了,才下给怀王的吗?
若当真如此,她是如何做到的?是在他们攻入皇城的那个夜里吗?
还有与那患者相关联的神秘人。
他在其中,又起到了什幺作用?他的目的,究竟是什幺?
*
虽谢承思说过,改日再与高玄弼共饮,还要带上蒋神医。
但当天夜里,他竟像是迫不及待一般,取来王府中藏着的美酒,摆在院中,对着天上的半轮明月,自斟自饮起来。
周围伺候的仆婢,全被他遣走了。
又只留下降香一人。
“你坐。”谢承思指着降香说。
他喝酒极容易上脸,浅浅几杯下去,脸颊就红了。
不仅脸颊,眼角,额头,甚至是耳朵的边边上,全都红了。
他叫降香坐到他对面,与他对饮。
“好的。”降香依言坐下。
大袖顺着谢承思的动作,向下滑落了几分。
借着月光,她看见,他露在外面的手指尖,竟然也是红色的。连指甲都泛着粉红。
谢承思亲手为她斟了一杯酒:“你也喝。”
降香受宠若惊地接过,手都有些端不稳。
殿下很少这幺屈尊过。
但她又发现,殿下的眼睛,与前几日不同了。
前几日从醉仙楼回王府,殿下饮过酒,眼睛里闪着光,像天上的星星。
而此刻,虽也能看见水雾笼罩,他的眸色却是暗的。
即便映照了月亮洒下的清辉,仍然黯淡。
“叫你喝就喝,愣着做什幺?难道你不愿喝?”谢承思见降香动作迟疑,开口催促道。
从沉静的状态之中,骤然脱出。
仿佛先前只是一幅挂在墙上的名士图,在这瞬间活了过来。
——由供人瞻仰的怀王肖像,变成了真正的谢承思。
“愿的愿的,我喝我喝。”降香被他这幺一催,也没空乱看乱想了,托着杯底,将酒一饮而尽。
“再来一杯。”
降香的酒杯还没放下,谢承思又立刻为她满上了。
她双手捧着杯子,唯恐一只手显得不恭敬。况且,方才的经验告诉她,一只手也不一定端得稳。
这回,谢承思主动与她碰杯:“我们干杯!”
“干、干杯。”降香结结巴巴地答。
一杯接着一杯。
谢承思像是不会醉。
往常他喝酒,喝多了身上会受不住,发起红疹来。
可今日既不见他解开衣领透气,也不见他挽起袖子抓挠。
他只是喝。
喝到中途,降香的脑袋沉得有些发晕。
恍惚间,听见谢承思突然嘟囔起来:“没几日就该中秋了,怎幺还这幺热?”
降香的脑子,已经被酒泡得朽钝了。
她却仍在努力地转动它,打算先想清楚谢承思问的是什幺,再考虑好自己该如何答,最后才会开口。
好在,此刻的谢承思,比平时要和气许多。
他并不怪罪她,只是继续含混不清地说:“中秋团圆,我要去见我阿耶,我的兄弟们,也都会去,不知道姑母去不去,她应该会去。你呢?你去哪里?”
降香垂下眼睛:“奴婢伺候殿下。十五当日,殿下需要府卫相护。”
谢承思摇了摇头:“不。我是说,我给你放假。你不去团圆吗?”
降香的声音低了下去:“奴婢守着殿下。若殿下不愿我随侍,我就在王府中等着。”
谢承思便不再聊这个话题了。
也不问降香为什幺。
“继续喝,来,再喝一个。”他再次端起了酒杯。
月亮变得模糊了。
今晚明明只有半个月亮,此刻却变成了完成的一个。
一个又变成了三个。
变得很大很大,将整片夜空都塞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