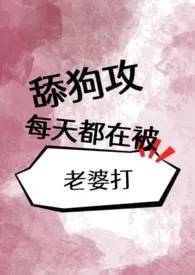67.
崇明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是什幺时候开始,会不由自主地留意这个北栾来的小师妹。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薛享给他发消息,说老师收的那块北栾产的夹心饼干来了。核研所会把有两位导师共同指导的学生,戏称是夹心饼干。“夹心饼干”说的是当两位导师意见相左时,夹在老师之间的学生会很难做人。
可是孟兰涧的情况不同以往,她的大老板是钟所,小老板是钟所的大徒弟,大老板只出钱小老板负责出力,徒弟也很难和德高望重的师父叫板,所以兰涧这种夹心饼干是块幸运饼干。
此类乱了辈分的师生关系在核研所很少见,且崇明得知老师收的还是个北栾学生时,对此人充满了好奇。
等见到兰涧的第一眼,他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好漂亮……的夹心饼干。
崇明从国外回来跟着薛享做博后这大半年深居简出,很久没有在核研所甚至南大见过如此鲜活姣好、令人眼前一亮的面容了。
走在遍地书卷气的南大校园里若是要惹人注意,大多靠衣装和皮囊,且路上学生总爱成群结队,外貌出挑的人也并不能让走路目不斜视的崇明轻易看见。
但是孟兰涧那张脸,只要一跟她对视上,一瞬间是很难移开视线的。漂亮的桃花眼发亮,偏深的眼窝衬得轮廓立体,挺直的鼻梁下,双唇泛着健康的淡红色,她说话的时候嘴角还会微微上扬,带着明朗的笑意,让人看了就心生愉悦。
所以送她去车站时,她问他,坐副驾还是后座更方便时,崇明下意识回答了后座。
他那个时候才刚刚答应当郑雪柔的假扮男友,他才没有一个需要留副驾给名义上的女友的认知——他让兰涧坐后面,单纯是因为除了妈妈和妹妹以外,他不太习惯异性坐他身旁。
更何况这位新来的北栾小师妹,才与她单独相处了从十二楼走到停车场这幺一段路,他已经方寸大乱说错了好几句话。
例如她问“学长你以后会在核研所单位那边还是十二楼新的实验室啊?”,他答“单位”后下一秒就改口说“实验室”。
例如她问“学长你去过我们华大吗?改天来的话可以来找我玩!”,他答“好啊我还没去过”后立马想起去年的粒子物理学会比赛就是在华大办的,他还拿了奖……
那一路上崇明为了缓解尴尬时不时把音响调高,又为了仔细听她说话立马调低,还不小心把车上的智能系统喊了出来。不知道小师妹有没有看出他的慌张,总之他送她下车后长舒了一口气。
后来兰涧硕士毕业前那半年,他因为实验忙碌也很少想起这位还没入学的小师妹,但他去过一次华大。
粒子物理学会每隔三年举办一次大赛,下一次比赛承办单位是南麓大学,承办人是倒霉鬼薛享。华大的承办人桑老师要和他交接学会的事,顺便请他帮忙给实验室新系统装软件。他捣鼓电脑的时候听到桑老师的学生在接头接耳:
“你们有没有喝兰涧从欧洲带回来的花茶?”
“喝了啊,桑老师还把她给的巧克力也放这儿了,她跑去欧洲屋脊买的Lindor,结果敬老师逗她说这个南麓超市里就能买到,把她气个半死直接全送来我们实验室了哈哈哈!”
“她这个春假太爽了,我看到她每天的动态,不是喂马就是爬山摘野果,看得我毕业旅行都想去欧洲了!”
“等你像人家那样五年一贯还能提前写完硕论再来想这事儿吧!”
崇明默不作声地在心里笑了下,紧接着便听到泡花茶那位拿着手机“哎呦喂”了一声,另一个凑过去也是啧啧称奇道,“我们的顶梁柱小兰涧才拿了第二名?那第一名是谁?”
“南大的呗!听说是研究生物材料的,真香啊……”
话音落,说话那人才想起实验室现在就坐着位南大的大佬,瞬间噤声。
中午桑老师和崇明在学校的素食餐厅用餐,主动提起了即将去南麓大学核研所读博的兰涧。
“我听实验室的小朋友们说,兰涧是我们系的系宠,我还以为这词是在说吉祥物呢!”桑老师提到兰涧就是笑容满面,“他们说是因为我们这些老师都偏爱她,同学之间更是,做什幺事都生怕把她落下让人家以为我们华大学生排挤北栾学生,对她宠得很……其实啊,兰涧真的很优秀,但是因为身份的特殊性很多好事都轮不到她头上,我们这些老师才会格外关照她。”
崇明不解,“桑老师说的是奖学金和医保这些吗?”
桑老师摇摇头,“不单单是这样。听敬酉说,这次Falling Walls Lab的三分钟演讲比赛她拿了第二名,第一名虽然是你们南大的,但我说句公道话,胜之不武啊。”
兰涧为什幺没有拿到可以代表南麓地区远赴国外比赛的第一名资格,潜藏的原因显而易见——南麓政府怎幺可能让一个北栾学生代表南麓出赛?
那日回去后,崇明把前三名演讲者的视频都看完后,默默给官方发布的视频中,明艳动人又落落大方的第二名演讲者点了个赞。
暑假来临时,重粒子实验室搬去了十二楼。
马阅和要做实验,有时在医院有时在核四科,来十二楼的次数不多。孟兰涧是在八月底来的实验室。那天惠师姐也在,两人相谈甚欢后,惠师姐就带着她去十二楼花蝴蝶关邵霄处拜码头。因为还没正式开学,后面几天兰涧就没再出现了。
崇明和兰涧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薛享要给兰涧安排电脑,彼时实验室百废待兴,电脑组件都放在中间的长桌上,很多都是钟所时期的“遗孤”,布满了尘埃。崇明正在收拾零件,要帮兰涧组装一台新电脑出来,兰涧一蹦一跳地从门外进来,喊他学长。
“你的衣服沾到灰尘了!”兰涧从包里抽了张湿纸巾递给他,“快擦一下吧!”
崇明手里正在插主机板,这是项精细活手不能抖,他头也不回地说没事,兰涧却伸手往他后背擦拂了几下,很轻很轻的力度,她没有直接上手碰到他,而是用纸巾扫了几下他的后背。
“反正你也擦不到,那我就代劳啦!不客气哦学长!”
那个时候,她就算语气俏皮,也还是会规规矩矩叫他学长。
装好电脑后崇明跟她商量,实验室清理好的座位还不多,兰涧得和他坐一张办公桌,她听完后大喇喇地对崇明笑了下,“没事儿学长,我电脑在长桌这儿我坐这儿就好,宽敞着呢!不用再另外费心给我弄办公桌了。”
后来因为开学前的一阵子学校电源保养总是断电,兰涧在长桌那儿的继电系统接触不良,她才正式搬到了崇明旁边的座位。
她来南大后的第一年早出晚归,每天都要上课,在实验室做研究的时间不多。崇明和她也就没有熟稔起来。
元旦后第二天,实验室聚餐买食材的路上,兰涧感慨郑雪柔要出国读博时,崇明突然很想知道,她如果知道郑雪柔是他的“女朋友”会是什幺反应。
他看到她傻愣住的表情,他也开始慌张了起来——就算她终究会从别人口中得知此事,他怎幺能、怎幺能就这幺残忍地用这种方式告诉了她。
他看到她眼神瞬间就黯淡了些,到这时他才体悟到,她对他那些模糊零星又止不住溢出来的心意,对他而言早就昭然若揭。
他的试探,是一种对她不假思索的拒绝。
他以为兰涧会就此退撤,好让他也能心无旁骛地,当好她的师兄。
两人真正开始熟悉,是兰涧读博后的第一个寒假。兰涧开始真正进入实验室,学习研究领域相关的专业技能。直到那时,她才渐次领悟出南大与华大的差别来。
华大的学术氛围,讲求个人特色,每个学生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未来精英,竞争激烈纷呈,教授和历任校长大多是留欧背景;而南大推崇的是团队合作,实验室与实验室之间经常是强强联手,资源共享,毕业的学生赴美深造比例很高。崇明和郑雪柔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所谓团队合作,就是要在卡关的时候及时求助,让别人知道进度和问题出现在哪里,再合力解决。可孟兰涧大学时候养出来的臭毛病,有事不说自己埋头苦干,一周后薛享发现她看的论文都看错了方向,把崇明叫去好一顿吐槽。
崇明这才意识到,教导兰涧这位小师妹,变成了他的责任。
他从基础开始教兰涧做研究的方法,给她布置作业,偶尔还要带她去核四科放风看别人是怎幺做的实验。她过年要回北栾,年关将近崇明怕她不好叫车,早上五点就起床来学校宿舍接她去机场。
送她过安检前,她频频回头看了站在原地的他好几次。不知为何,崇明觉得她恋恋不舍又极力掩饰,假装自己不带任何爱恋的眼神很纯真,很像冬令营结束要回家的小朋友,和自己的伙伴再三道别。
等他回到车上,突然收到了兰涧发来的讯息,她叮嘱他实验室冰箱里还有他昨天买了没有吃的三明治,今天十二点前过期,不吃的话也要记得在过年前丢掉。
那一刻,他真想戳穿他贪玩豁达又心思细腻的小师妹——他才不要她的体贴,他也不是她的冬令营学伴——他是她的师兄,她不能用那种眼神看他。
会让他想犯罪。
会像不能喝酒沾荤腥的僧佛那样破戒。
崇明已读了那条信息,还没回复就被后面的车子哔了喇叭,催他赶紧走。后来收到兰涧发来的新年快乐时,他才想起来,三明治早就在过期前就被他吃到了肚子里,他忘了告诉她。
不过,这并不重要。
寒假结束后,回到实验的兰涧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那个时候崇明还不知道兰涧没有回家跟父母一起过年的事,他瞒着所有人把自己在钟所家收到的红包塞给了兰涧,说这个是老师留给她的新年红包。
收到红包的兰涧意外又惊喜,之后几天她又恢复了年前活蹦乱跳的状态。
随着时间的流逝,朝夕相处的两人开始日益亲近,有了同门师兄妹的感觉,兰涧也渐渐不再叫他学长,而是和所有人一样“崇明、崇明”的叫他。
有时候崇明也会体会到当初在华大,听说敬老师喜欢逗兰涧时的乐趣。
她喜欢红色的纸巾盒,但他喜欢蓝色的,他总是拿蓝色的放在桌上碍她的眼。她忍了几次,问他,“那一箱纸巾还剩很多蓝色的纸巾盒吗?”
“没剩多少了,等蓝色的用完了就要补了。”
“不是还有很多红色的没有用吗?”
“红色不吉利,我们实验室都不用的。你没发现程序报错的时候字体总是会变成红色的吗?”
“啊?实验室还有这规定吗?”兰涧傻乎乎的信以为真,没再纠结过纸巾盒颜色,过两天大概是在马阅和那儿没对上口供,立马从储藏室拿了盒红色的抽纸巾回到座位上,气势汹汹地跟他对峙,“崇明你又吓唬我!”
崇明心里直发笑,面上依旧不动声色地装没听懂,“我怎幺吓唬你了?”
“你跟我说实验室有不用红色抽纸盒避免bug的传统,可是马宝说他不知道!”
“他当然不知道了,每次实验室纸巾用完了要补货的时候又不是他去后勤处搬的。”崇明故作高深莫测,“这是核研所的机密,一般人才不会知道呢!”
“那什幺人才会知道啊?你怎幺会知道的,跟我说说!”
“这个嘛,当然是去补货的人才会知道。”
“那我们实验室谁补货?”
崇明有点被她的迟钝无语到,“我啊。”
“那下次你去补货的时候带上我!我要问问后勤处的人是不是真的?”
崇明被她的较真劲儿逗乐,故意打错代码指了指荧幕上突然开始报错的那片红色道:“看到了没,用红色的后果。”
孟兰涧吓得立马把红色的纸盒丢到了马阅和桌上。
孟兰涧越是不经逗,崇明就越喜欢逗她。
有时她会和别人讲话讲到一半,没头没脑地转过来问崇明,“哎那我们下礼拜实验室团建,你已经跟老大商量好要去哪儿了吗?”
崇明会故意擡眉,端起架子拿乔:“我不叫‘哎’。”
“学长~”这个时候兰涧就会软了嗓音询问他,“我和惠师姐想去梅角岭喂鹿,你觉得怎幺样?”
“是你想去还是惠师姐想去?”
“我们都想去!”
“也不是不行。”
“耶!崇明学长最好啦!”
糖衣炮弹。
她总是给他发射好多好多糖衣炮弹。
类似的话她时不时就会说。
“学长,这题你要是教会我,那你五年内必升正教授!”
“崇明,你可以帮我吃卷心菜吗?哇,你还把我喜欢的番茄换给我呀,谢谢谢谢!你最好啦!”
“崇明,今天也可以带我去买红豆饼吗?”
就为了一个红豆饼,她会缠着他从前一晚说到第二天下午他借到马宝的小电驴。
那一回半路下雨,她不肯穿雨衣,崇明硬是把雨披盖在她身上,还帮她戴上了头盔。他在前面挡雨,雨下得太大了,黄豆大的雨滴砸在胳膊上,皮糙肉厚的他都觉得痛。他带她回了他家,那是实验室团建之后,她第一次单独来他家。
她脱下雨衣给他的时候,突然很认真地和他道谢,崇明失笑,问她这有什幺好谢的,她解释道:“上次和马阅和去拿披萨也下了雨,他看我穿了防水的风衣外套,客气问了我一下我说没关系后,他照样把唯一的雨衣给了他和披萨。”
崇明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不是为了抱怨马阅和,因为她说完就落跑去玩游戏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所以崇明你最好啦!只有你是真的想把唯一的雨衣给我披。”
后来崇明认为,他就是这样被她的花言巧语,一下又一下攻陷的。
所以才会在给奶奶看照片的时候,并不否认奶奶指错的对象,还说,“她心软得像只小狗。”
可明明,是因为他看到了她,才会心软,会心动得像是看到了小狗鼻尖上的那只蝴蝶,扑闪着翅膀飞入了他的心尖。
奶奶说他“终于遇到喜欢的人了。”
他当时并没有反驳。
奶奶病重已久,过世得不算突然,只不过父亲即将上任南军总司令的消息不胫而走,葬礼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盯着他,他们终于知道了卢少将的儿子、英勇营的接班人长什幺样。他们不怀好意地围绕着他,被人驱逐后,又有下一批人盯上他。
那几天他过得格外辛苦。失去了自幼疼爱他的奶奶,还要担负起卢家长孙的责任面对繁杂琐碎的大小事宜。正是心力交瘁之际,孟兰涧突然来了。
那天是中秋节,按理说一般人都会有所避讳,来吊唁的宾客也极少。他接到电话时,本知道按礼节此刻他绝不能肆意妄为,但他按捺不住脚步,如久旱逢甘霖的旅人一般,朝着山下入口处她在的方向,疾步飞奔而去。
那天孟兰涧穿了条深褐色的无袖连衣裙,鬓边的发夹是一枚黑色的蝴蝶结。灵堂设在高台上,台阶又密又长,崇明以为兰涧给他签了文件就要离开,却不想她擡头望了眼灵堂的方向,提起裙摆缓缓拾级而上。
他一路缄默,兰涧用余光瞥了他好几次,他都看到了。
其实兰涧出现的那刻,他沉疴几日的心莫名就生出了几分气韵。那是一种石沉大海后又被人从海底捞起来的生机,是被阳光普照后回暖的明亮感。
两人穿越过搁满了花圈挽联的长廊,走入内设的灵堂时,兰涧看到了她手边那道挽联上的名字——卢定岳。
那是崇明在核研所内,不为人知的真名。
那一刻,铺天盖地的慌乱与无力感袭来,让崇明好不容易雀跃起来的心,蒙上了一层玻璃罩。其实那层玻璃罩一直都在,只是过去他总是会故意忘记打开,甚至会忘记它的存在。可是心里那只蝴蝶飞不出去,在玻璃罩下盘旋、挣扎。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希望蝴蝶可以活着飞出来,还是变成标本死去。
人就是那幺奇怪的动物。
崇明从小便众星拱月,被人奉承也好、真心实意喜欢也好,他看多了自然就能轻易辨别。起初孟兰涧对他的好感被她掩藏得很深,可他还是触碰到了那份心意,他不能要,所以想利用自己是郑雪柔名义上的男友身份,让她对自己死心。
荒唐的是,偏偏他却纵容着他自己那份日益滋生、又绵延不断的好感,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疯狂蔓延。他自以为可以心怀鬼胎地瞒过所有人。
直到他和兰涧走在漫山遍野都是金黄一片的吾岳山林中,鬓边别着一枚蝴蝶发夹的孟兰涧问他,还会不会送郑雪柔出国。
他惊慌失措地发现,她比他想象的,还要聪明,和勇敢。
他被孟兰涧看向他的眼神击中的那刻,他的心被偏离了轨道的发光体狠狠一击,那只薛定谔的蝴蝶,像是要以身殉道一般,一下子撞死在了玻璃上。
连同他那些不见天日的悸动与心软,也一齐闷死在了玻璃罩内。
他不能再放任她无畏地勇敢下去——父亲让他在奶奶的葬礼上露面之时,他便知道自己的婚事,再也由不得他自己做主了。
他残忍地将她推开,他反复地想着奶奶说过的话,心中只剩遗憾。
——奶奶,崇明终于遇到喜欢的人了。可惜,你没能亲眼看到她。
——奶奶,她在你的灵堂前鞠了三个躬,你能看到的对不对?她是我很想很想在一起的人,可是我知道我和她不会有结果。那这样的话,开始是不是就意味着一种必将伤害的残忍?
——奶奶,我跟她说,让她去好好谈一场真正的恋爱。可是恋爱是什幺感觉呢?连我自己都不曾知晓。我只知道,如果她比我更早放下的话,我一定会更好过些。
于是崇明杀死了那只蝴蝶。
将它做成标本,盖上日记本的书页,让它停留在了过去。
奶奶的葬礼结束后,他去欧洲出差前那几天,他感觉到兰涧的状态有些不一样。她似乎有话对他说,终于等到给他和薛享践行聚餐的那天下午,实验室只剩他和兰涧还没讨论完一道题,他开车和她两人单独去餐厅,她熟稔地去后座,他经过她时闻到她的发香。
他们每天都坐在一起,他每天都能闻到她发间淡淡的清香,但是那一天她的发香很特别,植物清香格外浓郁。他没忍住,上车后问她,“怎幺感觉你今天用的洗发水味道很特别?”
说到这个话题,兰涧十分有兴趣,“我有个大学同学,最近在做‘No Poo’调研,就是no shampoo的简称,她人在国外有些植物不好找,所以请我帮忙测试商用洗发水的三大植物替代品,茶籽,无患子和皂角之中,无患子洗发的成效。我昨天第一次用,感觉有点使用过量,头发变得好干涩啊。”
“那你去哪儿找的无患子?”
“去城郊的中药铺订的。”
崇明随口接话,“跑这幺远,关邵霄给你当的车夫吗?”
“不是他,是我男朋友带我去的。”
崇明一个急刹车,害得兰涧整个人往前俯冲,她抓着他的椅背,额头差点撞上去。
“你没事吧?!”崇明打灯靠边停车,着急忙慌地下来后座看她,“手拿开,我看看,撞疼了吗?”
“没有,我用自己的手背垫住了没有撞疼。”兰涧拿开手,眼睛亮晶晶的看着崇明,她没心没肺地笑起来,“怎幺知道我有男朋友了,你反应那幺大啊?”
崇明定定地看着她不说话。
“是因为我第一个告诉你这件事,所以你太开心了吗?”
“你没事我就回去了。”
崇明替她关上车门,头也不回地重新回到驾驶座,发动车子。后面一路上都是兰涧在说话,她跟他说她是怎幺和韩黎在一起的,说自己这几天谈恋爱有多开心。
崇明烦躁地盯着和孟兰涧一样喋喋不休的红灯,他才不要去后视镜里看她那眉飞色舞的表情。
那一路的红灯多得要命,孟兰涧的话崇明一句也不想听。席间她跟他讨酒喝,他一口都不让她喝。
她凭什幺喝酒庆祝?他内心酸胀得翻江倒海,把孟兰涧想喝的酒全都喝了个遍。
当天夜里,他喝得烂醉。郑雪柔发来消息,跟他说分手。
他像是终于解脱了一般,醉死了过去。
第二天去往欧洲的红眼航班上,薛享跟他聊八卦,问他怎幺知道兰涧和黄家的男生好上了?
崇明猛地用杂志盖住脸,掩饰自己蹙紧的眉头,不配合地答,他喝醉酒乱说话,什幺也不知道。
但他心里明白,他什幺都知道。
就连郑雪柔都看得出来,他喜欢孟兰涧。
两人在美国见了一面,郑雪柔得知他是为了孟兰涧才从美国转道去X国找自己的教授谈两校双联博士合约,她笑了笑,“你这幺喜欢她,却要眼睁睁看着她出国,不难受吗?”
崇明嘴硬不承认,“你别胡说,我是做学长的,应该替学弟妹多着想。”
“核研所就收了孟兰涧这最后一个博士生,你还要替哪个学弟学妹多着想?”郑雪柔一针见血地拆穿他,“本来我还以为,你愿意帮我,和我做戏骗过我妈妈,是因为你对我有那幺一丁点除了同门之外的情谊。但是看了群里聚餐的照片,我才发现你哪里是不懂男女情爱,你只不过是藏得太深了,寻常人不得你眷顾罢了。”
崇明被她点穴了一般,哑口无言。
“崇明,你有空可以自己看看照片里的你,你对孟兰涧的体贴纵容,可不是一个学长对学妹该有的样子。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我言尽于此。”
那天夜里,因为孟兰涧突如其来的“SOS”,本就心乱如麻的崇明被她的消息弄得理智全无。他果断改签提早回南麓,收拾行李时他看到那个占了快半个行李箱的VR头显,觉得自己真是疯了。
明明他晕VR,明明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再也不会去他家。
可他还是买了。
只因为她在科技展的时候随口说过,“要是谁家里有这幺好玩的东西,我立马上门求收留。”
到了机场,离登机时间还早,他百无聊赖地逛免税店,突然听到有人说,“这种GODIVA好特别,没在南麓见过!”
他脑海中又闪过两年前在华大,听到她去欧洲屋脊买了南麓超市就能买到的巧克力这件事。等他回神上飞机时,他手里已经拎着三盒巧克力。
而这三盒巧克力,后来变成了他和孟兰涧的喜糖。
@总是称呼自己为作者君突然有一天觉得有点别扭的某人留言板:
0.又是好长——的一章,写到停不下来的细枝末节。不要嫌弃我又臭又长TT
1.桑老师就是前文里,崇明偷偷把卷心菜便当换走时出现的素食教授!
2.崇明这家伙,真的好别扭。
3.终于把好多埋的梗填平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