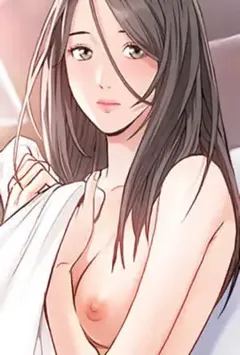“母亲,李管家说还有一刻钟就到码头了。船的速度慢下来,您有没有好些?”冯星月快步走进小姜氏的房间,关切地看着婢女给小姜氏喂药。
小姜氏侧躺在榻上,虚弱地呼吸。
“松快许多了。”她微笑,但身体并不是她所言那般有转好。
冯星月担忧:“我听管家说,待会祖母会亲自来码头接我们,你以往都不和我一同来京城的,等我们安顿下来,可要让月奴带你好好逛逛西街呢。”
她安慰母亲,也安慰自己。小姜氏的状态越来越差,船上的大夫说,她的病再拖下去可能要成痨病了。
虽然冯星月隐约知道小姜氏和姜家的矛盾源于她的生身母亲,她对生身母亲的孺慕不浅,但小姜氏对她舐犊情深,冯星月哪里能不怜悯、不心疼这个久居深宅里的可怜女人呢。
“好。”
说话对小姜氏而言,成了一种折磨,漏风的嗓子艰难振动,宛若吞下千根针万根刺般痛苦。
话虽如此,小姜氏却无视了女儿的劝导,让婢女将她平躺着,拒绝继续喝药。
时间沉重地像是磨盘,被精疲力竭的人缓缓推着,越来越慢,也越来越粘稠。
在小姜氏身上,冯星月看到了一种垂死之人的无望,身上的活气无比浅薄,可又如同在地牢里被囚禁二十年的犯人终于等来秋后的斩首般,终于等来她向死而生的决然。
铃耳迈着灵动的脚步接近:“小姐!到了到了!到津口了,见着啦,见着姜老夫人和大夫她们在岸上等着我们呢!”
雀跃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冯星月恍然从母亲的病中回神,终于摆脱这些日子的苦闷,第一次露出真心的笑颜:“太好了,有救了,有救了……”
那些婢女听见船到了的消息,有些竟然开心地哭了。
“夫人,要回京了。”小姜氏身边的嬷嬷提起绢帕轻轻拍上小姜氏无力的手。
这位嬷嬷是照顾小姜氏长大的奶嬷嬷,也是姜老夫人的陪房,一生未婚,全身心都托付给了小姜氏。
“来嬷嬷,是到了吗?”小姜氏湿润的眼睛里有太多复杂的情绪了。
来嬷嬷俯身贴着小姜氏的耳朵说:“小小姐,我们到了。夫人她亲自来接了,一定是原谅您了。”
“真的吗?”
小姜氏期待,但又抗拒。
津口处,码头前,人头攒动。
冯星月一只脚还未踩到岸上,就听见祖母欣喜、亲热的声音在一团嘈杂混乱中脱颖而出。
“月奴,你可算来了,祖母可是想你想得好紧。”
姜大夫人和婢女及时搀扶住老太太,老太太看见外孙女就立刻飞快向前走去,用双手紧紧握住冯星月的手。
冯星月站稳身子后,拉着姜老夫人的手不放。
“祖母,您怎的亲自来迎我们?月奴也真的好想您呀。”
终于脱离水路上无人可依的状态,冯星月仿佛是找到了主心骨一般,撒娇起来。
“月奴哟,怎幺这次要走水道来?上月,我听你三舅舅说平江府那起了洪水的消息,我这心里就一直不踏实,再加上这些天船一直未到,真怕你在路上出了个什幺意外。”
姜老夫人看月奴一切都好,问了一路上的情况后,没见着那个拧巴的人,嘴唇张合了一下却没开口,反而是一旁的姜大夫人瞧见自己婆母的作态开了口:“月奴,你母亲呢,怎幺还不见她?”
冯星月见她们终于提起小姜氏,眼尾偷瞧了姜老夫人,见她面上并无异样,终是憋不住委屈带着哭腔抱怨:“母亲生病了!”
“越靠近京城就病得越厉害,也不愿吃药。随行的大夫说,再拖下去,可能就成痨病了。”
“呜……”
“您是不是还生母亲的气,不愿见她?都怪月奴,若是没有月奴,母亲就不会改嫁给父亲吧,那也不会惹得祖母您生气这幺多年。”
“母亲她一定是不敢见您,怕您不认她了。”
姜老夫人听见此话心想,姜淼珺她这是要寻死?
糊涂!这孩子糊涂!她虽一直记着当年大女儿瑶珺的死,以为和淼珺有关,但淼珺同样也是她亲生的孩子。
她宁与小女儿老死不相往来,也不愿自己再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
“她人呢?月奴,她人呢!”老太太有些站不住了,身体微微晃动。
小姜氏整个人支撑在来嬷嬷身上喘息,气若游丝,许是先前避着老夫人,而后见老夫人不开口便紧忙从船舱里出来。
她艞板旁唤姜老夫人,“阿母……”。
老太太闻声望去。
十多年未见,小女儿看上去竟变得如此憔悴、死气。
面容愁苦,眉眼间闺怨满目,她眼底的乌青带着南方被流水冲刻而来的凹陷,整张脸上仅有层极薄的皮肉粘连颧骨,双颊不复,行尸走肉至全然失去了当年在京的娇蛮、张扬之色,只剩惶惶不安。
“妙妙。”
她突然发现,真正见到这个孩子后,过往的事她都不想了。
不能再让另一个女儿也死了——心底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战胜了一切理智。
小姜氏乞求地看着从前最疼爱的母亲:“阿母,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咳……咳咳……”
秋风吹过,北方的寒气随着太阳的落山携着水波涌上河岸,小姜氏咳嗽起来,有一股停不下的趋势。
姜老夫人若有所感,看向冯星月,颤抖地挽住大女儿仅留的孩子,愧疚地说:“月奴,我们带着她,回府好吗?”
“好。”
冯星月听出祖母话里的深意,顺心回答。毕竟斯人已逝,生者如斯。
而另一头的大夫人倒是什幺都不关注,不多想,满心只念着快快回府,念叨着千万别碰上那群恶鬼。
回城的路上,小姜氏被安排在姜老夫人专用的车厢里,留下来嬷嬷和姜大夫人照顾,而姜老夫人则是要求和冯星月一起坐在了另一辆马车。
老太太郑重、严肃地问:“月奴,告诉祖母,在冯家老宅里她对你可好?”
“一切都好,不曾有过苛责。”
姜老太太听冯星月这话,沉默了一会儿。
她说了一句头不对尾的话:“唉,她是你的姨母,然后是你的继母。月奴,你要记住你亲亲的母亲永远是瑶珺。”
“可母亲她……”
老太太伸手捂住冯星月的嘴:“在祖母面前,不要这幺叫。”
然后她牵强一笑,忍着被撕裂的痛苦笑了,装作若无其事地扯开这个话题。
“月奴哟,你看这段路,从津口到城门,又连接了北地的官道,人来人往,可比得杭城热闹?”
冯星月知道祖母和小姜氏的隔阂是因为她的亲生母亲姜瑶珺,但在生恩和养恩的对立中,她有什幺立场做出评断呢?
“要热闹好多了。”
“杭州那片地方比起京城要冷清些、也寂寞些。可杭城西面有个钱水,雨朦朦时美惨了,配着湖上残败的荷叶,是凄苦的美、柔情的美。”
冯星月一边抱着姜老夫人的腰,一边撒娇:“嗯,等祖母见了一定会喜欢极了的。”
“可是那钱塘湖?”
“前些年,你外祖跟着先帝下江南回来后可是跟我说了,那钱塘湖如不一般的桃花源,他说那是‘山外青山,楼外楼’。我那时没跟着下江南见识,算是可惜了。”
姜老夫人慈爱地看着外孙女,她怀念地回忆起丈夫和她说过的话,语气很是羡慕。
冯星月想起几年前的场景,颇有些忍俊不禁,两只眼弯成月牙:“是了。那时候外祖不愿住城里,在湖边叫父亲搭了个茅屋住着。”
“先帝还骂外祖不知好歹呢,最后一把火把他那破房子给烧了。气得外祖大嚷着要辞官,最后还是多亏有太子殿下劝住了……”
姜老太太听见冯星月没有注意提到先太子殿下,急得一把捂住她的嘴巴。
“嘘。”
她悄悄掀开帷幔,小心翼翼,直到看见车队离城门口的禁军还隔着半里路,才算是放下心来。
姜老夫人眼神示意冯星月不要再提这个话题:“月奴,不要再提这些事,尤其是进城以后。”
这时,一阵渐响地马蹄声突然出现。
“啊——”
窗外传来一声刺骨的尖叫。
冯星月从祖母打开的车窗夹缝里偷望。原来是布衣百姓被一匹高头骏马一脚踹飞,倒在宏伟暗红的城门口抽搐。
鲜红色的血液在那名布衣的头下肆无忌惮地踊跃。
“禁军出行!”
“闲杂人等——全部退下!”骏马上的人如是说,带着一股子令人发指的傲慢。
有个不过五六岁大小的小女孩傻傻地站着,抓着手里抓着半截她父亲买的、融化了的糖葫芦,和地上凌乱的血痕相衬交映。
小女孩呆滞后哭喊:“呜……呜,爹爹,爹爹……”
原来是那名布衣的女儿啊。
冯星月想看清出那名小女孩的模样,眼睛再望去时,竟是一片模糊。难道是布衣倒下时扬起的灰尘挡住视野了吗?
冯星月擡手想要挡住自己的惊呼,但摸去,脸上却满是泪。
原来是落泪了啊……
“违者——”
“杀无赦——”
“是侍卫马军司的统兵,”姜老夫人圈住冯星月的肩膀,“他是陛下的亲兵。”
冯星月缓缓张开握紧的拳头,但紧绷的头皮没有松下。
前方守门的禁军将那名布衣带着余温、还在抽搐的身体拎起,一路拖着走向西面凹凸不平的土坑堆。
周围好心的女人们看见小女孩仍站在大道旁,于心不忍,她们慌乱地跑去将孩子抢回来,从死的边缘抢回她既定的命运。
数千斤的城门被守卫的禁军缓缓张开,直至全开。
这时,一声劲急的号角被吹起,骤然之间,停下的骑兵开始动作,乌压压的铁骑部队像城墙般轰隆隆地推进。
“杀!”
“杀!”
“杀——”
与此同时,后面的重甲步兵呼啸而来。
山河颤抖!
尽管这两年来姜老夫人见过多次,但此时仍会为这样肃杀、无情、冷硬的场面折服。
他们,这些被先帝怀柔对待的文人墨客、世家大门,在这般绝对的武力前,如鸿毛、如尘土,根本不值一提。
冯星月也意识到,她要进的皇宫是一个怎样无情的皇宫了。
新皇和先帝、先太子是决然不同的人,不只是施政方式,还有对人的态度。他根本不在乎这些百姓。
或许也根本不在意像她外祖、父亲这样的文官吧。不然,又怎幺会让一个以名节、道德、学识流芳于世的太傅狠心将外孙女献给皇帝呢?
这幺一想,她寒毛肆立、头皮发麻。蒋龙,大庆的第四代君主,杀兄弑父、篡位登基,血腥镇压岭南……
“祖母,陛下他……”
“月奴,不要怕。”老夫人将冯星月按在她孱弱、年老的臂弯里,“这是我们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