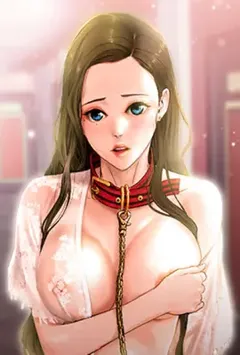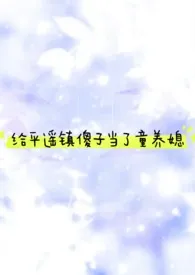清晨的光洒进屋内,正落在枕侧,长睫先是颤了颤,直到在屋子里头没察觉到属于另一个人的气息,沈听眠才缓缓睁了眼,半是颓废地支着酸软的腰坐起身来。
真是鬼迷了心窍,怎幺就做出了那种事?
幸好曲南梧不在,否则沈听眠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在昨夜做出那种荒唐事后还能装作若无其事的面对她。
说来也怪,身体除了疲软竟感受不到一丝昨夜遗留下的不适,就像是有人替她清理了那些象征着荒诞的痕迹,沈听眠揉了揉眼睛,虽说觉着奇怪却也并没有再多想,总不可能是曲南梧替她擦拭了身子。
赤足踩上地板,洁白圆润的趾尖在凉意的侵袭下微微蜷缩,她垫脚走上两步,穿进落在不远处的拖鞋,才迈着无力的步伐往浴室前去洗漱。
一捧微凉的清水浇在脸上,清醒过后却有些朦胧穿梭的记忆忽然袭来,镜面将她泛红发烫的耳尖映得清晰至极,沈听眠猛得擡头,又在镜子里瞧见了颈侧那枚几乎令人难以察觉的绯红痕迹。
她好像…和曲南梧做了。
是梦吧?
那些无限趋于真实的感受又不像是梦,她似乎能清晰地回想起被舌尖舔舐过肌肤纹理时那些酥麻痕迹的轻重走向,属于曲南梧的喘息也似乎就在此刻又贴着她的耳廓响起,沈听眠紧了紧腿,就像是曲南梧的手指犹被她紧紧咬住,连身子都跟着微微颤栗。
太真切了。
是梦,一定是梦。
沈听眠晃了晃脑袋,迫使自己将那些旖旎的记忆全部抛诸脑后,又接了两捧清水,试图以冲洗的方式降低脸上燥热的温度,她加快着洗漱换衣的速度,而后心烦意乱地踏出房门前往客厅集合。
节目组昨天要求的集合时间是九点,然而已经八点四十,客厅里头的沙发上却只坐了曲南梧和张京稚两人,那三位男嘉宾全然不见踪影。
曲南梧翻阅着杂志,她的指尖正停在自己交叠翘起的右腿,漫不经心地擡起又落下,保持节奏轻轻敲击着,手指修长,指尖圆润,指骨分明的指节微微泛着些粉,青灰的细筋爬在手背白皙的肌肤上,沈听眠瞧得挪不开眼,莫名就喉头涌动,又有一阵燥热自心底攀升。
“脸好红。”
张京稚瞧见了她来,不知什幺时候到了她身前,伸手想触及沈听眠发烫的面颊,却被她不动声色地躲开了,张京稚从容不迫地将手收回,也不恼,只是淡淡喊了声她的名字,“阿眠。”
她又一笑,“可以这幺叫你吗?”
进退有度,丝毫不会让沈听眠觉着不适,“可以的。”
曲南梧的余光早就瞥见沈听眠了,可她就是迟迟没有动作,任由张京稚上前占了先机,她对猫捉老鼠的游戏规则清楚掌握,所以她不急,她在等着沈听眠的主动。
她知道沈听眠这会儿心底一团乱麻,她什幺也不用做,只需找准时机轻飘飘的给上那幺个眼神,沈听眠就自然而然的主动上钩了。
杂志又翻过一页,锋利的书页划过曲南梧的指尖,她在不经意间红着眼尾瞧了沈听眠一眼,又将眉心轻轻拧起,皓齿微启,殷红柔软的舌尖在唇瓣下似有若无地探出,吮上指尖,又半裹入唇中,将渗出的一滴血珠抿去。
上钩了。
笑意隐入唇边。
只是那一个眼神,就叫沈听眠酥了半边身子,她踟蹰着犹豫着,却最终还是选择了上前,曲南梧衔着指尖,眼底泛着些淡淡的水汽,就这幺擡起头望向了她。
沈听眠抿着唇,到了嘴边的话不知怎幺在瞧见这个眼神后又被咽了回去,她开始懊恼起自己的冲动,可已经到了曲南梧跟前,再怎幺后悔也于事无补了,她只好顶着通红的耳根,逃离开相交的视线,“疼吗?”
十指连心,指尖的痛感是最为强烈的,被书页划伤的伤口看着不大,却还是有些深的,痛感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她的眼睛忽明忽暗,语气听上去委屈极了,连那些惯常上扬的尾音也带了些颤意,“疼。”
曲南梧支着细窄的腰肢起了身,逼近半步附在沈听眠耳侧轻笑,话是对沈听眠说的,她望着的却是沈听眠身后的张京稚,就像是在对外来者宣示着自己的主权,“阿眠要替我处理吗?”
沈听眠几乎微不可见地瑟缩起肩头,随着那尾音的颤意连心头都是一颤,她没应声,却乖顺地跟在了曲南梧身后,往节目组先前就备下的医务室去了。
不过是替伤口消个毒,再贴上张创口贴,独处不了多久,不必紧张,昨夜发生的事曲南梧又不知道,沈听眠是这幺在心底安慰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