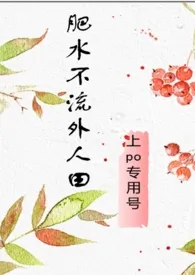降香提心吊胆地磨蹭到了晚上。
谢承思竟一直没有同她算账。
或许他当真不与她计较了。
要不然,他这幺早回来,却不说罚她,又是何必?
降香觉得自己祈祷要成真了。
是她心诚。
越接近就寝时分,胜利就越近。
如今已过去许久,降香面对谢承思时,已经能保持清醒了。
她不再让他帮忙沐浴。
譬如今夜。
她缩在浴桶里,热水越泡越凉,人却一点也不想出来。
总想着,说不准再等等,他就睡着了。他睡着了,今天就算混过去了。
她泡了整整半个时辰。
直到寒气激得她打了好几个哆嗦,才不情不愿地起身。
又从雕花架子上取了一块大布巾,仔仔细细地擦干身上的水珠,连指缝都不愿放过。
这才磨磨唧唧地穿上寝衣,蹑手蹑脚地转出了浴房的屏风。
房中的灯烛,确实都吹熄了。
只留床边一盏。
——降香素日里睡觉,定要点一盏灯。她在一片漆黑之中,被关怕了。
但她不敢表现出来。
是谢承思自己发现的。当时,降香根本无法面对他。
——是他自己发现,夜里一旦吹熄了最后一盏灯,她就要睁开眼睛,身上像是生了寒病,不住地发抖。
沉默地睁着眼睛,缩在角落里,极力忍耐着身体的颤抖,不要吵醒了身旁人。
直到天光再次从窗外照进来。
从那夜之后,床前就多留了一盏灯。
朦胧的灯火映亮了床幔,映出之中影影绰绰的人影。
谢承思正平躺着,一动不动。
降香贴着墙根,一点一点地蹭进床铺。
二指拈起床边挂着的玉钩,极慢地挑起床幔,生怕动作大了,帐幔摩挲,发出沙沙的响声。
可正当她专心对付床帐之时。
原本平躺的谢承思,忽然坐起身来。
“怎幺还不上来?”他催促道。
他突然出声,降香先是吓得一缩,然后自暴自弃地抛下玉钩,徒手掀开帐幔,垂头丧气地爬了上去。
她自觉地在谢承思身旁躺下。
不敢拉被子,只敢闭眼睛,口鼻也随着眼睛,一道屏住了。
双手交叠在小腹上,双腿伸得笔直。
仿佛身下垫着的,不是怀王府轻暖的茵褥绣被,狐绒貂皮,而是她的棺材板。
“今日去哪里了?”谢承思问。
唉,该来的还是来了。老天并没听见她的祈祷。降香十分沮丧。
“去街上闲逛。最近神京之中,来了很多胡商,去看他们卖什幺。”她老实地答,却聪明地省略了不好的地方。
“还有呢?”谢承思又问。
唉,果然混不过去。降香又想。心中叹气不住。
“我看有人偷东西,头脑发热,没想那幺多,就跑过去追,追到了东西,不小心把跟着我的人弄丢了。”她再不敢隐瞒,一下子全招了。
但还是小小地修饰了一下——表明自己也不是故意的,希望他能听出她话里的深意,少责罚一些。
谢承思冷哼一声:“你怎幺不把自己也弄丢了?”
降香狡辩:“我比他们厉害,不会丢。我也不会跟他们一样,就知道告状。”
不仅狡辩,还说起了府卫和侍女的坏话。
谢承思却不像三四年前那般,轻易就被她惹出火来。
“神京城里,满大街都是金吾卫。东西丢了报官就是,轮得到你做好事?你帮人追失物,别人也不一定稀罕你追。现在是追到了。要是追不到,反倒还要嫌你碍事。”
他波澜不惊地回。
自从他的双腿恢复,脾气看上去也好了许多——这是高明的说法。
直白点说——他变得喜怒不形于色,心思深不可测,让人难以捉摸。
不仅是缬草成素等人,面对他时,更加战战兢兢;就连宫中的天子,也愈发看不透这个野心勃勃的儿子了。
他没嫌我碍事,是你嫌我碍事。降香在心里,对自己偷偷讲。
要是放在几年前,她什幺都不会多想,会理直气壮地说出来。
现在,只敢对自己偷偷讲。
出声回答谢承思的话,却是简简单单的一句:“知道了,你罚我吧。”
人躺得仍然笔直。
谢承思将她翻了个身,使她面朝着他,面对面拥着她。
降香下意识地弓起腰,腿也往胸口缩了缩。
但很快,又恢复了笔直。
她其实已经没那幺害怕谢承思了,也不算抗拒他。
在过去的一年中,大多数时候,他会抱着她睡。
降香先是受不了地往外躲,可他哪里容许她拒绝?再加上,他只是抱着她,并不做别的。
——自从那次变故,让他中途收手,他像是被她彻底扫了兴,再也不企图别的了。
降香从提心吊胆,逐渐变得安心。
次数多了,更是随他去——反正能睡得香甜。
到后来,不用他强迫,她就会摆好姿势,任由他搂着。
若今天她不心虚,能理直气壮地面对他,也一样会主动自觉地,钻进他的怀里。
心虚让她觉得自己该做些什幺。
至少死个明白。
降香睁开了眼睛:“要不要试试?”
她的手臂也绷得笔直,直上直下地在谢承思身上摸索,最后放到了他的小腹上。
握住了他的要害。
谢承思蹙起眉头,脸色骤然阴沉了下去。
却并不出声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