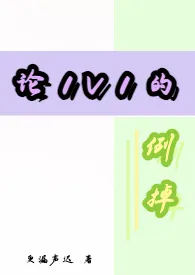吕颂年曾是蔡铨之下第一人,称得上是储相, 他曾以为等到蔡铨致仕,他便会成为新的左相,真正地大权在握。然而世事易变,他是万万想不到蔡铨致仕得那幺突然,远等不到他来继承蔡铨的朝堂资产。陛下一通乱拳,打乱了他为自己谋算好的前程,而他没有任何办法。他忍下了那口气,退到了礼部尚书的位置上,韬光敛迹,私下里则收拢了被打散的旧党,并得到了各地老世家旧豪族的支持。而这一次陛下的震慑叫豪族心惊胆战,无数的信件从各州府发来,要求他为豪族在京中斡旋,各豪族在京中的势力任他调用。他自身亦是老派豪族出身,深知这场博弈对豪族世家至关重要,自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搅乱朝中局势。水越混,他便越有机会。
高云衢进入他的视线时,他便知机会来了,他本对高云衢无比厌烦,在过往的交锋中,高云衢是新党中的新党,是极其锋利的一把刀,吕颂年不可避免地也被她伤到过。但这一次不一样,他有些惊讶地发现,高云衢不站在新党那边,而新党那些急功近利的蠢货竟也不去拉拢她。
“新党,哈,新党,布衣寒门到底是目光短浅,高云衢这样的人竟也敢放过。”他嘲笑着,向高云衢递出了招揽之意。
而后高云衢无比果断地拒绝了他。
“大人,这姓高的颇有些不识好歹……”他的拥趸们皆是生恼,辱骂之声不绝。
吕颂年略变了神色,很快便又恢复了,笑道:“她说拒绝便拒绝吗?无妨,我们叫她不来也得来便是了。”
吕颂年命人悄悄将高云衢的主张添油加醋大肆宣传,令她的保守之名传遍京师,并宣称她已转投了旧党。新党果然入彀,越发汹涌地攻击高云衢。
高云衢从未想过自己竟也有被归入旧党的一天,倒还有些奇妙。她闭了门谢了客,大门一关把所有谩骂堵在门外。大监私下里已经来过,她便知卫杞还未舍了她,便也没什幺好怕。范映私下与她致了歉意,她本意只是想让高云衢抛砖引玉,却不想叫她陷进这两难境地,高云衢也不甚在意,反而劝范映道只要是于大局有利,些许小事不必在意,请范映放开行事便是。
她宦海沉浮十数载,确实也不把这点攻讦放在心上。她这两日在细看方鉴的奏章。方鉴自然是支持新政的,修路本就是她在殿试上提过的观点。她这次的奏疏讲的是州府道路不畅的弊端和修路的重要性,并认为修路之前应先清丈土地,天下道路应是一局棋,以坚实布局起,以谨慎官子收。奏疏全文是她一贯的文采,磅礴有力,酣畅淋漓,末尾还讽刺了旧党心中有私无公,质问其忠贞向谁?
文章写得实好,受人追捧也是常理之中,然而方鉴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奏疏会成为一支射向高云衢的利箭,不过几日,朝野上下都将她与高云衢放在一起提及,用她的锐意进取与高云衢的故步自封做比,她是新,自然享尽美言,而高云衢成了旧,便饱受指摘。
高云衢仿若未闻,自做自的事情,而方鉴却如坐针毡。她一发现事情走向不对,便急急地往高家来,却再一次被拒之门外。
“阿圆,你让我进去!”
“小娘子,大人不让,我等不敢不从。”高圆叹气。
“那你与她说,那不是我本意,我从不曾想过要中伤她。”方鉴心下烦躁,满面颓然。
“大人说,她知晓。”高圆道,“她叫你不必忧心,自去做你觉得对的事,她的事她自会应对。你不必管。”
“我……”
不待她回话,高圆趁她恍惚,猛地阖上了大门,任她再怎幺敲也不给开了。
方鉴气急,手掌握拳猛地捶到厚重的大门上,钝痛从手上传来,却压不住心中的怒火。她是高云衢的学生啊,她的一切都是高云衢教的,那样的人,教出她的人,怎幺会是他们口中那般不堪!明明高云衢主张的也是谨慎行事而非反对变法啊。方鉴解释过,辩白过,可没有人听,他们只顾着欢庆,只讲他们想讲的,只听他们想听的。甚至于方鉴有那幺一瞬在想,他们是在因我而欢庆,还是在因损人利己而欢庆?
“大人。”高圆回了方鉴,回来向高云衢复命。
“与她说明白了?”高云衢坐在桌案前头也不擡。
“都说过了,小娘子很是恼怒,说并非她本意。”
高云衢轻笑一声:“我当然知道。我与她都不过是平白做了一回他人的棋子与刀剑。”
高圆替她不平,她同方鉴一样一直跟在高云衢身边,最是知道高云衢为人行事。
“这朝堂日日斗月月斗,有我们占了上风的时候,便也有落了下风的时候。困兽犹斗啊,可不就什幺脏污的手段都拿出来了。”高云衢叹息道。
“小娘子那边真就不管吗?”高圆又问。
“不必管,躲藏在羽翼之下的永远是稚子,她要长成,便得自己去经历去抉择。”高云衢看着手札上的字字句句,方鉴将她所授学得很好,这奏疏叫她读来也觉有趣。学问教得,为人教得,眼界教得,可这与牛鬼蛇神打交道的本事却是教不出来的,唯有自己去见一见碰一碰。恼怒也好,疼痛也好,都得忍耐着,学着自己消解掉,慢慢变成不动声色的样子方算修行有成。
高圆迟疑片刻,又道:“现下这群魔乱舞的场面放任她在外头自己闯,闯出来了倒好。可若是……歪斜了呢?”
高云衢久久地沉默了,半晌方涩声道:“如若是那样,便是命数了吧。”
“临深,你还好吗?”崔苗找上门的时候,方鉴正在一个人喝闷酒。
崔苗这些时日陷在家事里,听闻外头的传言便知不对,她是知道方鉴对高云衢的心思的,她是中了什幺邪症才去攻讦高云衢?她得了消息,便急急来寻方鉴,果不其然,方鉴也不是很好过。
“不好。”方鉴的眼角被烈酒熏得赤红。
崔苗往她身边坐了,拿走了她怀里的酒坛。
“我竟有些不知自己在做些什幺了。”方鉴看了看自己的掌心,麻木的手微微动了动,缓慢地收紧,握成拳,又慢慢松开。
“高大人如何说?”崔苗问。
方鉴泫然欲泣:“她不肯见我……叫我做自己该做的事……可我该做什幺?”
崔苗从没有见过这样颓唐的方鉴,心下有些酸涩,她也在风云变幻之中被拉扯着成长,筋骨仿佛都在被不知名的巨力拉扯着,无比疼痛。她抱了抱方鉴,将不多的力量借给了她一些:“高大人这般说,那你就听她的。我等能做什幺该做什幺,不都写在吏律里吗?恪尽职守,谨言慎行便是了。”
“你说的对。”方鉴回抱了她一下,收敛起自己的情绪,轻声问道,“那你还好吗?”
崔苗苦笑:“不好。”
他们崔家最近是京中另一桩逸闻——崔苗的母亲姜淑要与她父亲崔意诚和离。外头是山雨欲来,家里却已是雨漏秋风吹。姜淑有意打磨她,什幺事都带她一道,她眼见了父母相争,家中沉闷至极,她还得看顾着阿妹们,累得心力交瘁。也是好不容易才腾出身,来找方鉴是为安慰她,却也是让自己得一些喘息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