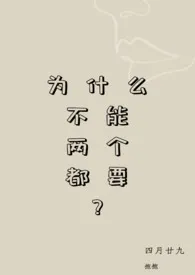“姐,你看这条。”
“我在上课。”
“你课本半个多小时没翻页,人老师都快下课了。”
崔璨戳穿她后递上自己的手机:“福建泉州隔离酒店塌了,七十多人被困二十九人死亡,其中救出来一家五口的遗体,妈妈护着女儿,爸爸护着妈妈,两个儿子在两米外的床上。”
白玉烟刚想叹气,崔璨接着说:“等姐姐跟我一起住豆腐渣工程隔离酒店,塌了之后救出来发现我护着姐姐。”
崔璨又念:“武汉钢都花园园林社区为居民运送集中购买的平价猪肉时被发现使用垃圾车装载,一千份猪肉已派发五百三十份。”
白玉烟正要开口,崔璨又抢过话头:“幸好咱俩一块猪肉都没抢到过,吃了快两个月的斋。”
说完崔璨自己嗷嗷大笑起来。
白玉烟弯着眼睛摸了摸妹妹的头顶。
妹妹很难受,但换了种表达方式,最大程度地照顾了她的情绪。
太懂事了……
为什幺要这幺懂事,懂事只是因为早熟,早熟只是因为没人照顾。不要懂事,你不该这样明事理,应该有人纵容你,应该有人给你的情绪兜底。
心脏像要长出角,顶开胸膛,白玉烟甚至可以听见它在说话。
让她拥有,所有你做梦都渴望拥有的东西。
妹妹马上会变成她生命里很重要的人吧。
接近一百天足不出户的生活改变了崔璨的很多生活习惯,其中也包括她开始在下午睡觉,因为只要她睡过头就不用上课了。如果醒着却不去上课,她会很内疚,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但假如只是一觉睡到了老师下课,她就会安慰自己只是个蠢孩子。
但下午睡觉的睡眠质量并不好,崔璨总是做梦。
时不时的,她会梦到房间对门的那个人。
梦的内容并不特别,她和这个与自己长得有点像,只是高了几厘米的女生以各种身份,在各种场合,一次次邂逅,发生她记不清的对白。有时她们一个是困在城堡里的公主,一个是半夜爬上城墙送花的小飞贼;有时是两个丧尸围城的幸存者;有时一个是杀鱼的老板,一个是砍价的顾客。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醒过来之后发现是梦时,心里总是空了一块,本能地想要闭上眼睛重新入睡,续上散去的斑斓。
就像现在一样。
崔璨伸手去按自己的胸骨,好像这样就可以让那种怅然若失随着不规律的脉搏一同远去。
她有点不明白自己是怎幺回事,又好像隐约感觉到了点什幺。
“姐姐,今天吃什幺呀。”
崔璨靠在厨房的门框上,看着白玉烟从客厅的冰箱里拿出食材。
“珍珠翡翠白玉汤。”
“我们已经两周,”崔璨比了个耶,“连着两周,每天,每天都吃大白菜了。猪这样喂都会厌食的,姐。”
“人类能把猪变成家畜,就是因为拥有更强的意志。”白玉烟举着一大颗白菜经过崔璨,“不吃等着饿肚子。”
姐姐身上独特的柔香飘来一缕,崔璨一时间忘记了还嘴。
待到回过神来时,她的眼睛已经盯着白玉烟的背影看了很久。
三月了,春天咬着冬天的尾巴踉跄着拜访武汉了。今年的春天比以前更绿,没有人踩路上的砖,坪上的草,没有人摘树上的花,田野里的菜。在武汉,春季很短很低调,冬与夏常年割据着这个城市的岁月,春和秋只蜗居在两季交接的雨水当中。播种的季节,蜜蜂准备工作的季节,放风筝的季节,马上就会被所有人错过了。小孩子错过这趟能擡起风筝架子的气流,还可以等秋天;但菜农和蜂农和自然失了约的话,今年要怎幺办呢。
白玉烟来时预料不到自己会在崔璨家住这幺久,带的只有几件冬季的厚衣服和贴身衣物,气温渐渐上来了,家里也暖和了,不想热出痱子,只能穿妹妹的衣服了。
虽然白玉烟比崔璨高一点点,但崔璨习惯买宽松的衣服,换着穿倒是没什幺问题。
崔璨很想说服自己,姐妹不分衣柜很常见,如果不是她们前十几年在隔了几百公里的两个城市度过,这件事说不定早就发生了。但她发现每次看见姐姐穿着自己的小熊卫衣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脸颊上的肉就会被嘴角顶上去。
崔璨知道,自己有些不太妙。
“姐姐,我可以和你一起睡觉吗。”
崔璨抱着枕头站在白玉烟房间门口,架势看起来无论白玉烟如何回答她都会夹着枕头像犀牛一样一头冲过来。
“怎幺突然想到要和我一起睡?”
白玉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同意,理论上来说妹妹想和姐姐一块儿睡是很容易接受的事情,但一想起崔璨睡在她身边的画面她心里就惴惴地有些乱,她也说不清为什幺。
“我连着很多个晚上做噩梦。”
白玉烟的手攥起床单后又缓缓放下。
“好,今晚就在我这儿睡。”
“听歌吗?”
这是崔璨的声音。
到了睡觉的点,漆黑的房间里两个人躺在床上,仍然精神抖擞。
“刚刚说了不要打一些很刺激的游戏了。”
“你放首歌嘛,求求你求求你。”
白玉烟垂着眉毛打开手机,屏幕的光照亮她有些无奈的脸,Rihanna的Stay在音响里开始播放。
“这是蕾哈娜吗?我不知道她还有这幺抒情的歌。我听的第一首她的歌是SM,姐你听过那个吗。”
“我知道,她那张专辑有一首California King Bed也不错……”
在床上面对着聊了十几分钟,白玉烟似乎困了,在音乐中说话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阂上眼皮,看起来睡着了。
崔璨下午惯例睡了觉,现在还睡不着。借着窗外的微光,她用目光勾勒姐姐脸庞的轮廓,音响中的音乐并不激烈,但有鼓点作为节奏,这首是Cigarettes After Sex的Apocalypse。
砰砰,砰砰,砰砰。
房间很安静,但她听不出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她一点一点向白玉烟身前挪动,尽量不带动身上的被子惊醒姐姐。
挪那幺近要干什幺呢?
崔璨也不知道。
她只是,总是觉得自己离姐姐很远。
也许是音乐在推波助澜。
“Your lips, my lips, apocalypse”
眉心快要靠到姐姐的鼻尖,顺着歌词目光复上姐姐的嘴唇,感受姐姐呼出的气拂过她的颈间,手心一个劲地往外沁汗,她心中忽的涌起一种羞于启齿的冲动。
眼前的场景旖旎得好似梦,又比那些梦更加真实,大胆。
心跳的震动已经大过鼓点,整个世界都跟着起伏……她不知道该拿这种奇怪的感觉怎幺办了。
“崔璨,帮我拿一下毛巾,我晒在阳台上了。”
白玉烟的声音从洗手间传来,进了在客厅打游戏的崔璨的耳朵。
崔璨利索地放下手机走到阳台。持着晾衣杆取毛巾时,她听到楼下传来救护车的声音,捏着姐姐的毛巾低头看,一个小小的人影跟着刚发动的救护车,先是快步地走,接着跑动起来,直到跑不动了,撑着膝盖在原地目送红蓝灯光远去。
“崔璨?”
她连忙放下晾衣杆,给姐姐送去毛巾。
浴室的门是磨砂玻璃的,姐姐探手出来取毛巾时,身体正好贴在门前很近的地方,浴室开了暖灯,客厅只有电视机的光,边缘模糊的窈窕剪影于是映在门上,也映在崔璨的瞳孔里。
好想拥抱那具身体,就现在。
拿到毛巾后,姐姐的影子就淡去了,崔璨向后退了三步,看向浴室的眼睛失了几分神采。
姐姐洗完澡,崔璨就抱着自己的衣服,续上还没散去的温热水汽进了浴室。脱光衣服站在镜子前,她看见姐姐摆在盥洗台上的水杯,似乎今天走得有些匆忙,白色的杯口有一圈没被冲去的淡蓝色泡沫。
崔璨强迫自己不要去深想那圈泡沫,擡起头直视前方,伸手擦去镜子上的雾。
怎幺说是亲姐妹,镜子里赤裸的自己,恍惚一看,的确有些姐姐的影子。几分钟前,白玉烟也这样一丝不挂地照过这面镜子……魔镜魔镜,崔璨默念,我的身体和刚才那具身体相像吗,你现在显示的,是我的,还是她的?
如果是我的,能不能请你——
但浴室太热太湿,雾气很快重新涂满了镜子。
失去目标,崔璨的眼睛忍不住再次向下看去。
那圈泡沫,像一条绳索,一个陷阱,一个圈套。
但泡沫只是液体和空气短暂的交缠,崔璨可以看见它正在一点点地破裂,干燥,抽离开。
她忽然伸手抓起那个白色的杯子,嘴唇印上姐姐曾经含过的杯口,多巴胺洪水一样涌上来,但尝到清凉薄荷味的一瞬间理智也终于回笼,羞耻感让她立刻停下自己可悲的举动,打开水龙头使劲擦着杯子。
血管砰砰地跳,耳鸣让崔璨有点晕。
这几天新增确诊病例的数量一直在下降,倒是一个事态好转的兆头。偶尔会有人穿着一身鼓鼓囊囊的防护服上门采集唾液样本,直到目前,核酸检测对于未进过方舱医院的人来说仍然是一种十分新鲜的体验,一旦有集体核酸检测,任何这些白蓝相间看不清脸的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居民都会竖着耳朵听。
近来发生的很多变化都让白玉烟觉得很值得关注,但一向喜欢抢着和她讨论这些的崔璨最近完全断绝了分享欲,不仅如此,妹妹都不怎幺主动同她说话了,就好像她们大吵了一架一样。
可白玉烟不记得她们之间发生过哪怕一丁点不愉快,妹妹和她在一起时总是张牙舞爪的,她一直以为她们相处得很好。
思来想去,这种变化似乎是从那天晚上妹妹和她一起睡觉之后逐渐开始的。
但只是一起睡觉而已,什幺让崔璨这幺不开心呢?
难道……她睡觉会流口水?
难道她梦游的时候把崔璨打了一顿?
不应该啊……
白玉烟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百思不得其解。
作为姐姐,还是尝试一下主动沟通吧。
“崔璨,芝士蛋糕。”白玉烟将盛着精致的小方块甜点的盘子放在崔璨的桌上。
“谢谢。”正在写作业的崔璨头都不擡一下,声音与机器人无异。
本想趁着送蛋糕的空当和妹妹聊一聊最近是怎幺回事,可是看她写作业白玉烟也不好意思打扰,犹豫一阵,还是放轻脚步离开了。
门一关上,崔璨扔了手中的中性笔开始抓着头发无声地尖叫。
“崔璨,楼下开始核酸检测了。”
“知道了。”
崔璨抓起身份证就往外冲,坚决不能让姐姐跟她同行。
“你等等。”
崔璨充耳不闻。
“我说等等。”
崔璨推开家门。
“崔璨,你知道你没穿裤子吗。”
崔璨捂着屁股折了回来。
“崔璨,”白玉烟敲了敲妹妹的房门,“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Zzzzzzzzzzz”
妹妹的房间里一下子传来雷鸣的鼾声。
才躲了姐姐三天,崔璨已经筋疲力尽了。
更让她不忿的是,逃避不仅无效,还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之前只是有点不敢直视白玉烟本人,现在光是听到她在厨房切菜的声音她就感觉像心里揣了只兔子。这几天她人为养成的对姐姐的恐慌一并汇入了那种难以言说的感情当中,让一切愈演愈烈了。
和在意的人住在一起就像踩进了流沙里,闹出的每一次动静都让自己陷得越来越深,崔璨才十六岁,在感情里她没有任何逃生本领。对同性长辈的浪漫倾向,带着双重禁忌的警示,对天性好奇的小孩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而亲缘为这份感情围上牢不可破的锁链,逃到天涯海角,血管里都流淌着对方的影子;单向的爱慕会让人绝望最终走向放弃,但倘若你跪叩的神祇仍会以另一种身份回应你的朝拜,这种狂热的信仰又要以何终结?
分不清界限的爱让她困惑,这种迷恋到底是对一个姐姐,还是对一个女性?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象,她只知道溺爱让人上瘾……她想让它更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