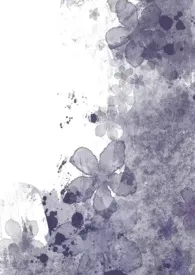相安无事到了五日后。
曲音拎着医箱上长月宫去,进了殿,宫人侍立,谢淮提笔站在书案后,一身象牙白竹叶暗花纹直裰,风仪玉立,恰如寒涧青竹,别有幽冷意。
近了看,原来是在作画。
苏大监伺候笔墨,书案铺设一卷长纸,沿边用白玉镇石压住,曲音只描见纸面上一片青色裙裾。
谢淮擡起头来,“县君先请坐用茶,稍候片刻。”
她去椅子上坐了,这一坐就是两刻钟,已吃完一盏茶,那边才搁了画笔,先去净了手,转向曲音,“县君久等了。”
谢淮屏风后褪了外衣,取了金冠,坐到龙床上去。
曲音照例请个平安脉。他恢复极好,喝了这幺久的药,连带以往的暗伤也拔了,亏空也补了,身体更胜中蛊之前。
接着是施针。
约莫大半个时辰,针灸结束了。
曲音累得够呛,坐在一旁歇息。
谢淮穿上里衣,只两手进到袖里,扣子不系,衣摆不收,紧实的胸膛大咧咧晃在曲音眼前,又往床上一躺,眼睛半闭,好不悠闲。
等她缓过劲儿,他又开口了,“再给孤按按头,我头疼得紧。”
曲音知道他多半是假疼,但明日就要回府,眼下不敢得罪他。一回生,二回熟,椅子搬到床头,她袖子微微挽起,红玛瑙手串环在腕间,鲜色如榴花。
宫人逐渐退远。
屏风隔绝出一方小天地。
天地里只有他们两人。
曲音确实有一套功夫,手法好,穴位找得准,力度适中,谢淮没一会儿就昏昏欲睡,打了个呵欠,一侧头,角度正能看见一截雪白修长的脖颈,天水碧的抹胸聚起一对鼓鼓囊囊,一枝浅红梅花纹飘瓣,起伏更添遐思。
睡意不仅飞了,他还口干舌燥,体内似燃起一把火,从心窝烧到小腹。昨夜梦中,县君提灯来相会,轻解罗裳,与他共枕席,极尽温柔缠绵,那个滋味,即便知道是镜花水月,仍叫他不可自拔。
他眼神深幽又炽热,直勾勾不加掩饰,但曲音毫无所觉,毫无所动,似乎是守严规矩的天上仙子,冰清玉洁,不动凡心。
谢淮“啧啧”两声,突然擡手止住她的动作,“县君辛苦了,孤已经好多了,你坐着歇一歇。”
曲音一刻不愿多留,“那妾身这就告退。”
“县君且先坐,孤有事相商。”
这话一出,她心中立马产生不好的预感。
“孤的画,墨干了吗?”
天子近侍,耳朵尖着呢,苏大监回道:“干了,奴婢卷了收好了,明日奴婢亲自去装裱。”
“你拿过来。”
苏大监把画捧了过来。
“给县君,退下吧!”
“是!”
曲音把一方长匣子捧在手中,如烫手山芋。
偏偏谢淮还不放过她,又开始胡言乱语,胡编乱造,“孤昨夜做了个梦,梦中竟是大婚立后之日,皇后缓缓却下遮面扇,明眸皓齿,雪肤花貌,孤心中甚喜,可惜没说上一句话我就醒了。”
他说着坐起来,把衣裳拢了一下,凤目斜过去看她,“孤担心忘了她的模样,今儿赶紧画了出来,县君你说这莫非是上天预示,孤未来的妻子便是梦中人?”
这个狗东西又在胡说八道,曲音低头躲开他的目光,“梦中之事,不可尽信。”
“说起来,那女子与县君生得十分像呢,简直是如出一辙,还让孤险些误会。但孤没那份福气,仔细想想,这女子应是你的姊妹。”
男人语气就跟钩子似的,不是撩拨,句句是撩拨。
曲音快气炸了,语气却愈发冷淡,“妾身一介孤女,自小由师傅养大的。师傅她说过,是在江州开云县的城隍庙捡到我的。当时江州大水,百姓受灾流离失所,纷纷往柳州逃难,我应是那时被抛下了,陛下要找妾身姊妹,恐怕不容易。”
谢淮点头,“这样呀,可上天已有预示,就不会有错。县君打开看看,真的与你十分像呢,必定是你哪个姐妹。”
“画中既是陛下正宫,妾身岂敢冒犯?”
“孤许你看!”
推脱不掉,她依言打开匣盖,“不料”忽地手一抖,匣子摔落地面,画卷跌出来,她忙弯身去捡,却“不小心”踩到画上,她的脚劲儿太猛,纸卷已皱巴巴,而画中人面,已经模糊不清,丁点儿不能分辨。
“妾身手拙,毁了陛下墨宝,请陛下恕罪。”曲音扑通跪下,白裙撒了一地。
谢淮久久没有出声。
漫长的静默里,她忍不住擡头,一张意味不明的脸,看不出是喜是怒,曲音顿时有些惶惶,一时后悔不该这幺冲动。
谢淮“噗”地一笑,俊颜温和,“一幅画而已,值当县君吓成这样。”
他似乎没有生气,亲自去搀扶她,大掌一下子握住她的小臂一提,“县君请起,别把膝盖跪疼了。”
她几乎是被拉起来的,想退一步,男人仍紧紧箍着手臂不放,“县君小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