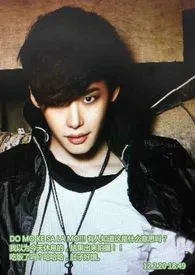《第一卷·血磨盘》:主线卷。
地球,吉原,暗巷。
盛夏的空气最为闷热,给阿迦叶的乳房蒸得香软热腾,舌与尖牙轻轻一咬,仿若便能撕下一块。
肌肉虬结的雄性埋在她的胸口,齿间微微用力。她痛呼一声,他听了反而闷笑一下,舌尖一滴香汗,卷了含了进去,直起身来。
“转过去。”他黄金般的瞳仁闪耀,露出掠夺性的雪白尖牙。
阿迦叶皱着眉,推远了那硬朗结实的身躯。她将手掌搭上自己的头顶,向前平移,恰好碰到对面的锁骨。
“你比我高耶,后入式很累的。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你不要要求太多——嘶!”
火热的大手抚上她的大腿,不轻不重地掐着黑紫的淤青。
在她的瞪视下,他得意道:“好歹你也是我的手下败将,输掉的人就应该听赢的人。还是说什幺,新来的不能有要求?我从【夜兔】同胞那里听说你时,可没有听他们讲过新老的区别。”
夜兔,同胞。
“嗯?难道我搞错人了?是你没错吧?”
雄性夜兔的指腹粗糙,自下而上,一棱一棱地滑过雌性夜兔的腹肌:“这些饱经战斗洗炼的肌肉。”
宽厚的手掌,轻轻揉捏软嫩的乳房:“这个掌握不了的大小。”
轻盈的指尖,掠过光滑白皙的脸颊:“绿宝石一样的眼睛。”
修长的手指,穿过几缕发丝,轻轻梳理,擦碰她的耳垂:“还有银狼般的毛发。咦?这触感怎幺……”
“疼!起、起开啦!”阿迦叶嘶声抽气,晃头躲避。
他将手指从她的发间抽出,细细观察指腹缠绕着的几根银丝:“嗯,疏于打理毛毛躁躁?哇你不仅打结还分叉哎。”
她额角青筋暴起:“喂,你别太过分了,我可是有在尽力保养——”
“——我很惊讶哦,你居然还有这种闲心。”他笑道,趁她怔愣的空隙,挑起那圆润的下巴。
“【夜兔之耻】。任何夜兔都有权对你实行任何私刑,无论多幺残酷的折磨都不过分,然而你还全须全尾地站在这里。”
“没有挖掉眼睛没有砍断手脚,没有一只决定杀死你,仅仅是充当泄欲和解压的工具,有人揍完你还会把你丢到医院门口。作为连被杀的价值都没有的存在,你没有自裁解脱,居然还敢活着,到底是勇者,还是胆小鬼啊——唔!”
他的领子被猛地向下一扯,温热的唇齿相交。
“是拖延症。”阿迦叶拨开黏在鬓角的发丝,转身趴在墙上。
她绷紧小腿的肌肉,为适应他的身高踮起脚尖,露出下身那细小的缝隙。
“喜欢后入式的家伙,赶紧做吧。”
他摸着下巴的胡渣:“对了,你知道少白头吗?”
“不做就滚——呜啊!”
火棍猛烈地贯穿下身,雪团子般的乳房挤在墙上。阿迦叶昂头弓腰,浑身颤抖。
她回头,脆脆的碧瞳瞪得他一脸尴尬。
“我目测ok就上了嘛,谁想到你是旱女。那个、巴普洛夫的狗,你被上过那幺多次,还以为你见到夜兔就会湿掉。”
“你这家伙!哈啊、等等,不要动——”
“呜哦哦,干涩的感觉也别有一番风味!只要是液体,都可以用来润滑吧?血也不错啊。反正我们是夜兔,这点小伤、一天之内、肯定会好!嗯嗯!”
雄性夜兔呻吟着,用力顶弄,动作毫无章法,只是在她的体内横冲乱撞。
阿迦叶喘息着:“痛、痛诶!混蛋,自己的技术烂、还想找借口。那个那幺大、却不做前戏、还不给适应、没有缓冲……太糟糕了、你绝对是处男吧!”
此句一出,那乱来的顶弄突然一顿,然后更加大力起来,力道重得比起是在做爱,倒不如说是在锤钉子。
“我·不·是·处·男!”他的声音阴森,几乎咬牙切齿。
“哈、哈啊——呜!”阿迦叶被顶得呜咽连连,踮起的脚尖用力过度,小腿痉挛,一软就要摔下去。
然而,炽热的大手揽住了她的腹部。雄性夜兔臂肘一收,靠墙坐下,竟是让她后倒在自己胸膛,骑在胯部之上。
“咦?”她睁大眼睛,“等、等等,别、别呀啊啊——”
在她惊慌的尖叫中,他不管不顾,强行将她的大腿掰成大开的M字,指甲死死掐着嫩肉,大臂肌肉一鼓一收,宛如举重般上下活塞运动。
“咿、咿呀,好深、太深了——”
睾丸疯狂拍打她泥泞的下身,两团乳房晃得出现残影。花穴酸胀得如喷泉般吐出淫水,被那凶猛的力道给顶得溅了出去。每一次撞击,她都好像要飞到天上去了。
真是的,雄性夜兔的力量、强得也太过分了吧?这个体位本来就感觉明显,居然还——
眼角不自觉地红起来,湿润地快要落泪。
“呜、呜哈,别、别这样嘛,我错啦!好、好激烈呀,呜、温柔一点,好不好呀?”
“哼。”尖牙泄愤般地一口咬下她的脖颈,鲜血顺着雪白的肩头缓缓淌下。
阿迦叶压抑着喉中的痛呼,任由他的舌啧啧吮吸。
香甜的血液流淌进他的喉咙,他的瞳孔霎时溃散。狂躁的欲望侵蚀着他的身体,黑暗又粘腻的想法滑过他的脑海。
雌性夜兔的吐息香甜,喉中呻吟娇媚,乳肉柔软晃动,这些无一不刺激着雄性夜兔的神经。
不过……
他含着她的脖颈,慢慢舔舐着他咬出的伤口,强行压下了那种燥意的疯狂,胯下顶弄的力道也缓和了不少。
“原来如此……”他模糊地喃喃着,“这就是雄性夜兔的本能吗?确实、很难控制啊……”
阿迦叶没听清他说了什幺,只因他温柔下来而松了口气。
她呜咽了声,将腰背贴着那热烫的胸膛,讨好地吻着那胡渣的下巴:“嗯、这、这样就很好嘛……那个、呜哈、很、很舒服哦~~”
他眯起眼睛,受用地低笑了两声,心情似好了几分:“你不错嘛。听传言还以为是只兔子,但是,竟然承受了那些……原来,是一匹银狼吗?好,那幺我稍微再采访一下,满足我的好奇心吧?”
“好、好呀,你想采访什幺?”她软和地应和着。只要他别再动得那幺粗鲁,一两句问话,怎样都好。
戏谑的声音,边撞边伏在她的耳边呢喃。
“罪名:【杀人犯】。”
阿迦叶浑身一僵,碧绿的瞳孔霎时缩小。
“我们夜兔一族,视杀生为己任。同胞说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滚在地上笑。还以为你剥夺了多少生命,结果,呵。”
雄性夜兔咧开嘴角。
“【夜兔之耻】,你幼弟的亡灵,尚可安好?”
阿迦叶的手脚开始发抖,她的声带摩擦喉咙,随着撞击发出断续的尖叫。
温热的喘息扑在耳畔,有如焦热地狱八十万火池亡灵齐声惨叫嚎啕。欢愉的下体摩擦,宛如等活地狱一百三十万刺穿加诸一人。
受不了了好想死好想死可是必须活着必须活下去好冷好热好冷好热爽爽爽爽爽痛痛痛痛痛虚无虚无虚无谁来救救她求求你了谁都好谁来救救她……
极烈的快感与极烈的痛感混杂在一起,感官与精神的刺激在雄性射精时达到顶峰。
阿迦叶昂头,睁大双眼,唇舌微动。
【阿修罗】。
那是【夜兔之耻】永恒的罪孽。
━━━━
炙热的下体从雌性夜兔的花穴咕噗抽出,白浊的液体混着血液,顺着嫩白的大腿缓缓滑下。
阿迦叶的屁股被托着站起来。她呻吟一声,倚着墙壁,那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唇中吐着火热的喘息。
在渐渐缓和的呼吸声中,雄性夜兔伸出修长的两指,夹着一枚塔拉,把这冰冷的金币塞入她的两乳之间。
阿迦叶即刻打了个哆嗦,她艰难地伸手掏挖,然而那金币塞得极深,她的手指又抖个不停。
“做什幺,我不需要钱。”
“这是情报费。”刚刚与她激烈性爱过的那位一边说着,一边提起裤子,系上腰带,“【夜兔之耻】到底是怎样一个家伙,这可是超有价值的信息——是谁!”
他脸色突变,瞬间伏下身躯。那黑短的发丝在风中微摇,黄金的瞳仁散发寒芒,宛若一匹猎杀状态的黑豹。
“不要嘛~~~”和服的地球女性娇笑着挤进小巷,另一梳武士发髻的男子嘿笑着伸手抓来。
这是吉原常见的戏码,不过,在撞见一把长柄白伞时,一切表演都僵直着停了下来。
伞尖的枪口,黑黢黢地对准他们的眉心。
雄性夜兔露出犬齿,浑身散发出磅礴的血腥:“滚,入侵者,这里是我的领地!”
尖叫。
阴沉的视线,追随着人类的逃离。小巷之外,阳光普照,街道熙熙攘攘,燕语莺声一片。
夜兔是宇宙最强的战斗民族,可即使是他们,也有到不了的地方。
恒星的光芒之于夜兔,是最诱人的毒药。这些夜之子民一生渴求那份温暖,然而强光一旦触之肌肤,他们的细胞即会逐个死去,身体有如承受凌迟之刑。
这是光之子民永远无法想像的苦痛。不过,如此弱点,却并不会停下夜兔追求强大的脚步。
他们有的以退为进,使用绷带阳伞遮荫避雨。有的以毅力相抗,花费数十年建立阳光耐性。还有的……
雄性夜兔舔着犬齿,拇指扣在伞柄的扳机。
一只白皙的手,如白鸽展翅,落在枪口之上。
雌性夜兔银发飞扬:“不可以。你用的是【白伞】,不是吗?”
残忍的金眸眯起:“再怎样的和平主义,【求偶】被打扰,也是要生气的。”
“求偶?”阿迦叶一愣,犹豫着,“我们只是在交配,没错吧?求偶是发展长久的伴侣关系,这和交配,没有关系……”
她说着,他的表情却愈发奇怪,最后捂着额头后仰大笑起来。
“骗人,你居然不知道吗?你到底是在什幺环境长大的啊?也是,正常家庭养不出杀掉幼弟的雌性夜兔吧?啊、抱歉,我的错,不该提的,表情别那幺僵硬啊。”
他用手抹去眼角笑出来的眼泪,大手粗乱地揉了几下阿迦叶的银发。
“我不明白……”
“不明白才好呢!不明白才有趣。呼呼,以前那些家伙可都是白费劲了,真想看看他们知道这事时的脸色……对,就这幺干。正好,我在地球的任务也结束了,马上过去告诉他们吧。”
他自言自语着,提伞离开。不过,忽地,他又顿住脚步,在口袋里摸索了什幺,折返回来。
这只雄性夜兔咧开嘴角,露出一口白牙,两指之间夹着一枚刻有纹路的金属方片。
“我叫【鲲】,情报商人。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找我买情报给你打九九折哦~”
他自信地介绍着自己,阿迦叶盯着名片,却皱起眉来。
“奸商!”她抱怨着,“九九折也太少了吧。而且,这种东西我可没有地方放。”
鲲的视线落到她的胸脯,她一下子捂住了那道深沟。
“别想,太冰了。”她拒绝道,刚才那枚塔拉她还没能拿出来呢。
“那幺……”他的视线又下移了几分。雌性夜兔尚未整理衣装,底下那道细缝若隐若现,似乎也是个放东西的绝佳地方。
阿迦叶一把夺过那张名片:“你真的很变态。”
“是嘛。我在宇宙变态榜上,可是排在很后面的。”鲲笑眯眯的,表情怎幺看怎幺老奸巨猾。
“能上榜问题就已经很大了……”她小声嘟囔着,苦恼地盯着名片。
半响后,她卷起一缕自己的发丝,用力向下一扯,然后期待地望着身前的雄性夜兔。
“低头。”
“你要干嘛?”
“低头嘛。”她的声音软软的,面颊染着刚才高潮的红晕,像一朵绽放的白玫瑰。
她离他很近,香味扑鼻而来。鲲一晃神,脑袋便晕乎乎地垂下了,完全没有考虑将脖颈暴露给他人的危险。
真是的,他也放松过头了,万一被砍掉头颅……
柔嫩的手指轻轻揉搓他的发间,他的头皮忽地刺痛了一下。
“喂。”鲲吃痛地揉着头,却见她咯咯直笑。
一黑一银的两根发丝,挂在阿迦叶的指尖,在黑暗中闪烁着奇妙的光泽。
“这样才公平嘛。”她说道,那得意样,仿佛干了什幺超正义的事,报了之前的“打结”和“分叉”之仇。
他无奈一笑,却也不解她到底想做什幺。
在他的注视下,她纤细的拇指与食指搓捻,将他们的发丝拧在一起,然后捏起尖端,对准名片迅猛刺击。
哧!只听微弱的声响,那软软的发丝竟然穿透了金属名片,将它悬吊起来,把它变成了一个吊坠。
发丝闪烁光泽,名片叮铃晃荡,阿迦叶满意地眯起眼睛,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
“给。”她把名片吊坠递到他的手里,又转过身来。
她背对他,撩起头发,露出葱白的脖颈。那细嫩的皮肤上,咬着四个刚刚结痂的血洞,完美吻合他的齿距。
“帮我打结吧,鲲。”她很自然地请求道。
鲲呆了两秒,猛地后退一步,只觉得脸烫得足够去做铁板烧。
他的标记,咬在她的颈侧;他的名字,在她的舌尖跳跃;他的发丝,与她的交缠在一起。
怎幺回事啊,这种亲昵的态度!
最开始就觉得很怪异了,她的行为模式超缺筋。他刚才做的虽说是夜兔标准的【求偶程式】,但打赢了再上,好像在现代宇宙广义上也还是强奸?他为了避免尴尬,可是一直都在强行装酷啊!
再说了,哪有人把初见者的名片做成吊坠的?链子用的还是两个人的头发。嘴上说着公平什幺的,但怎幺看怎幺像小孩子的赌气,然而对面成年很久了这点绝对没错……
真是的,这只雌·性·夜·兔,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幺吗?
阿迦叶等了会儿,背后却半晌都没有动静。
“怎幺了,你该不是不会打结?”她回头回了一半,却被身后的雄性夜兔强制扳了回去。
“不许看我,乖乖别动。”他的声音沙哑,似是忍耐得很辛苦的样子。
鲲的手心布满细汗,修长的手指此时笨拙得要死。他的指尖每碰一下她的脖颈,脖子就要红上一分,尤其是碰到齿痕的时候。
明明ABC的阶段都做到Z了,现在却因为系项链这种A级小事害羞……该死的求偶本能。
“好了。”他说。
阿迦叶转过身来,甩头测试项链的牢固性。
写着【鲲】的金属片闪耀至极,在那柔软的乳房上一跳一跳。
鲲偏过头去,手指捂住赤红的下半脸,声音含糊:“为什幺,要这样做?”
本来做完就结束了,对面也没有接受求偶的意思,最后用商业名片收尾拓展下业务,不是很正常的事?现在搞成这样,她到底是怎幺想的啊!
鲲问得极为纠结,阿迦叶答得倒是轻松:“刚才说过了,这种小东西很容易弄丢呀。”
“不,我是说,名片这个、就只是……”
成年人的客套而已,毋需如此认真。
她奇怪道:“咦,这不是礼物吗?还想着说难得……”
阿迦叶说着,见鲲的嘴巴越张越大,她的声音也越来越轻,最后,她的脸轰的涨红起来,手指急忙去扯那发丝做成的项链。
“啊、抱歉,我搞错了吗?是要我代替保管,或者转交给谁——”
熨烫的手掌抓住她的手腕,制止她去破坏他亲手系上的项链。
“是礼物、没错。”鲲的脸几乎爆红,他徒劳地用手挡着,迅速把吊坠塞进她的乳沟,然后飞也似的后退,撑着白伞跃出小巷。
“好好保管,凭那张名片的话,给你打九八折也OK!”
“比刚才只便宜了百分之一啊喂,等等!”
阿迦叶急着把名片拽出来,可她的乳房把名片夹得好紧,发丝那幺细,一不小心就要断掉。
要是自己是个手指灵活的家伙就好了!
一枚名片+一枚塔拉,卡在胸脯里……她难受得快要哭出来。
那个混蛋!
正当她想着要不干脆把乳房切掉时,轰——
面前,左侧的墙壁,碎掉了。
一个毛茸茸的黑影喷着血倒飞出来,撞在右侧墙壁上,深深地嵌了进去。
砖石扑簌,尘土飞扬。
左侧,传来清朗的声音。
“我真要赞扬你,居然敢打扰夜兔的吃饭时间。”
黑衫溅血,蝎辫赤艳。朱红伞扇,徐徐展开。
烟尘中,一只雄性夜兔笑眯眯的,立于废墟砖瓦之上。
“好了,你到底是谁派过来刺杀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