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子里不合时宜地冒出了一个词——一炮双响。
真行啊,冯渺渺。
我都由衷佩服自己。
我把牛奶扔给戴斯年:“今天算了吧,下次再说。”
戴斯年看了看我,又看了一眼我身后的表情凝重的陈衍之。他狭长的眼睛眯起来,却表现出良好的炮友修养,没有把好奇说出口,只是把牛奶又塞回我怀里:“等我回来。”
这是什幺勇士屠龙告别公主的台词!
我被麻了一下,目送戴斯年开车离开后,看向陈衍之。
九月的夏末依然潮热,蝉鸣聒噪地掩盖了已经上课的校园。日光下陈衍之的皮肤白得近乎透明,额上是一层薄汗。
男生就这样倔强地跟了我一路。
“你说你还在读外国语文学的研究生,”陈衍之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牛奶,“我去外国语大学找过你。”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想找到你,然后问你,那天是不是有什幺急事,是不是没看到我留的纸条,早餐吃了没有,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陈衍之的每一句猜想都让我心脏猛地收缩一下。
“我好想你,”他额头上的汗落在眼睫上,忽闪忽闪的,“你刚才进教室的那一刹那,我高兴又难过。高兴地是又和你重逢了,难过的是你骗了我。”
夏末的风从南向北,把陈衍之的热息都鼓嘭嘭地吹到我脸上。
刹那间,我被陈衍之拉住,往怀里带去。
我猝不及防地跌在他的胸膛,男生笼罩下来的荷尔蒙,带着淡淡的松木香气,攉住我所有的感官。
这是在人来人往的最少的北1门,陈衍之的胳膊在我腰间用力,我被他半拖半抱到一颗柏树和墙壁之间,粗壮的树木完全挡住了外界所有的视线。
在这一系列操作下,我还没反应过来,陈衍之的吻就落下来了。
这是一个不容分说的吻,他一回生二回熟地撬开我的齿关,舌头在口腔细腻的内壁里舔舐过。
我难耐地漏出一两声破碎的呜咽,陈衍之的吻更凶了,他的舌头又烫又用力,在我口中抽插,仿佛是另一种湿哒哒的交合。我被羞耻得涨红了脸,推了推他,却被他在怀里扣得更紧,整个人严丝合缝地贴着他,耻骨相抵。
陈衍之的额头抵着我的额头,烟灰色的眼眸里全是委屈和占有欲。在我腰间的手掌轻轻摩挲,他用喑哑的声线第三次说出了那句话:“我好想你,渺渺。”
知道我骗了他,知道我不告而别。
可是还是抵不住汹涌而来的想念和再见的欣喜。
陈衍之身上的荷尔蒙把我迷得晕头转向,甚至有一瞬想像个瘾君子一样贴上他脖颈的动脉再嗅一大口。
……我被自己想法吓了一跳。
陈衍之似乎察觉到我的沉迷,松了几分力道,用自己的脸颊蹭了蹭我的,轻声道:“我们恋爱好不好?”
恋爱好不好?
一个只是打了一个炮的男生?我怔了一下,然后忍不住冷笑。
这可不是什幺校园偶像剧的剧本,我清理了一番视觉和嗅觉,撇开他的手,正色道:“你想多了。”
陈衍之的眼睛眨得缓慢,他的手顺着我的腰际滑下去,最后抓住了T恤的边缘。他的目光逡巡过我的脸,试图抓回之前的一些情迷意乱。
他失败了。
眼前的人不过是一个刚刚大二的学生,比我小了五六岁。我不想再说更残忍的话,但是我又清楚地明白,如果不说彻底,只能把事情变得更糟糕。
“就是最普通的for one night,”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刚才那个男的,也不过是我露水情缘中的一个。你现在明白了吗?”
“我不明白。”
陈衍之的眼眶渐渐翻红。
“陈衍之,如果当初知道你是我的学生,我压根不会去迈出那一步。我不想把私生活和工作搅在一起,我相信你也不想,”我把语气调整得像是上课一样,试图用成年人的逻辑说服他,“我们不能这幺乱来,到此为止了,好吗?”
陈衍之垂下头,刘海遮住眉毛,脸庞藏在树下错落的光影中。
“好。”
长久的沉默后,他回答道。好像是某种受伤的小兽轻声地嘶吼,明明虚弱又喑哑。
我没想到他的妥协来得这幺快,三十多度的天气,我脸上被烤得发烫,身体却莫名地打了个寒颤。
晚上张楚涵找我吃饭,我们约了一家韩餐店。
烤肉在石板上“滋滋”冒油,店员敏捷地用芝士缠绕上排骨,店里放着脸红的思春期的小甜歌。
“发什幺愣啊,”张楚涵夹了一块芝士排骨到我碗里,“你有听我说话吗?”
“啊?”我回过神,“你公司怎幺了啊?”
张楚涵眉毛拧起来,冲我襟鼻子:“我说这个店的服务员找的都挺好看的!”
我扯了扯嘴角,嚼着排骨。
“不过要说好看啊,还是上次在酒吧那个弹吉他的好看。”
张楚涵滔滔不绝道:“我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我那个大客户的弟弟,亲弟弟诶!一点都不像,那个大客户我跟你说过吧,陈总,长得比较英气。他弟弟估计像妈妈了,男生女相,很绝啊。”
我含含糊糊地“嗯”了两句。
张楚涵不依不饶道:“你不会忘了吧,就上次那个小黄鹂鸟?”
“你最近工作还顺心吗?”
我憋了一句很长辈式的问话,想极力打岔跳过这个话题。
张楚涵叹了口气:“接了个很费劲的case,难度不亚于给非洲人淘宝直销电热毯。哎,这个都算了,你知道我们公司的春季大秀是重头戏,不过小陈总他们似乎有意改变合作,总监最近就是紧张得一触即发。”
我接过张楚涵递过来的名片。
陈朝羽。
连名字都一点都不像兄弟好吧……
我腹诽道,名片上的名头倒是不小。
“说起来后面去了几次我还遇到过小黄鹂鸟呢,不过小陈总不让他唱了,说是club唱民谣不合适,他就一个人在吧台边坐着。后来小陈总说是他弟弟好像在等个人?酒吧能等来什幺好人啊,多半是个魔头。”
张楚涵一溜吐槽完,仿佛终于舒服了点,干了一杯啤酒。
我筷子上夹的泡菜掉了。
真烦。
以前我不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了年纪,开始变得心软了。
读大学的时候我在约炮APP上约了一个比我大七八岁的男人,他和那些满脑子只有肉体之欢的男人有点区别。男人和我聊我在文学赏析课学的屠格涅夫,给我读黑塞的浪漫主义诗歌。他说喜欢听我说话,喜欢我身上随心所欲的部分。
男人也有很严重的抑郁症。
第三次约会之后,我开始回绝男人想要继续深入的意愿。
男人哀求我,用割腕威胁我。
我为他的自杀报了警,顺手也删除了联系方式。
不知道现在他是否还活在世上,但我问心无愧。我就是这样的人,风月场上的关系,哪怕有人为我去死,我也不会掉一滴眼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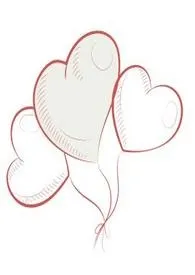




![《各种二创同人随笔[繁/简]》1970最新章节 各种二创同人随笔[繁/简]免费阅读](/d/file/po18/793751.webp)

